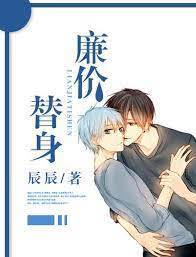《陳年烈茍》 第102章
那句潘小卓沒聽清, 陶淮南自己也屏蔽了的話,是一句迷茫遲疑的:“小卓,我好像……聽不見了。”
過分寂靜的世界像一場噩夢, 等到遲騁坐在他旁邊他的頭, 陶淮南才像是突然從某個可怕的夢魘里醒了過來。
聲音還在, 世界還在,遲騁著他的頭問他怎麼了,陶淮南搖了搖頭,他自己也不知道, 記憶和思維像是都錯了,一切都顯得不真實。
陶淮南從小失明, 他最依賴的一直是他的耳朵。那一上午短暫關掉的聲音, 陶淮南很快就忘記了。可他卻記得曉東那條語音,曉東語氣里的無奈和惆悵刻在陶淮南腦子里,他每次一想起來都覺得渾發麻。
暴瘦、剃頭、沒時間了。
這讓陶淮南接下來的每一天, 意識世界里都是黑暗的。漫無邊際的黑暗幾乎吞噬了他,他抱著哥哥,不知道能做些什麼阻止這一切。
陶淮南不記得在那個上午他曾經短暫地跟這個世界斷過聯系,所以第一次他在有意識的狀態下失去聲音時,最初的迷茫失措之后, 陶淮南坐在教室椅子上,上不停地冒著冷汗。
盡管只有半節課的時間, 陶淮南的冷汗卻把襯衫的后背都浸了。
他臉白得像紙,不停著自己的耳朵。
普通人失去聽力還有眼睛, 盲人失去聽力,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陶淮南在浸絕對封閉的那二十分鐘里,像被扔進了漆黑的海底。他在徹骨的冰冷中緩緩下沉, 沉進了另一個黑暗的異世界。
眨眼看不見,側耳聽不到聲音。時間被拉得很長很長,那二十分鐘對陶淮南來說難捱得像過了幾個小時。
好在只有二十分鐘。
Advertisement
下課時同學問他是不是不舒服,陶淮南說“沒事兒”。
那天中午陶淮南只吃了幾口飯就吃不下了,遲騁沒說他,還縱著他說:“吃不下就別吃了。”
午飯后他跟遲騁回教室趴了會兒,蓋著遲騁的校服外套,遲騁隔著外套拍了拍他的后背。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失聰之后,陶淮南很小聲地了聲潘小卓。
潘小卓當時正在翻書,隨口答應著:“啊?”
陶淮南慢慢地問:“下午你能陪我去一趟醫院嗎?”
潘小卓馬上問:“你怎麼了?”
陶淮南鼻尖上還帶著剛才的冷汗,眼睛對不上焦,向潘小卓的方向微微側頭,輕聲說:“我有時候聽不見聲音了。”
潘小卓嚇得撲棱一下在椅子上坐直了,眼睛瞪得溜圓,瞪著陶淮南:“什麼意思?什麼聽不見?耳鳴?聽不清??”
陶淮南了耳朵,手指都還在抖:“不是聽不清,是聽不見……什麼都聽不到。”
潘小卓瞪著陶淮南,有半分鐘的時間沒說出話來。
兩個都是乖學生,潘小卓還是班里的學習委員,他倆從來沒惹過事沒闖過禍,下午一請假老師就給了。
潘小卓說陶淮南不舒服,想陪他去打針。老師痛快地給了假,讓他們去校醫院,還讓潘小卓照顧好陶淮南。
兩人沒去校醫院,跑了出去。
查了一下午,能做的檢查全做了,陶淮南上不揣錢,錢都是潘小卓給墊的。幾種聽功能全測了,聲導抗做了,耳蝸電圖也做了,可這一下午卻什麼都沒查出來,沒有質病變,耳朵好好的。
潘小卓哆哆嗦嗦地問醫生:“那是為、為什麼啊?”
醫生是個年長的教授,戴著厚厚的眼鏡,說可能是神的,不要太擔心,又問家長呢。
Advertisement
潘小卓說:“先不想讓家里擔心。”
醫生又說了遍“沒大事兒”,問:“高幾了?”
潘小卓說“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們倆,話說得溫和,說好治,還是要跟家里大人講,別害怕。
醫生還是見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訴他們別擔心,只是重復了好幾次要跟家里講,還說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來他這兒看看。兩個小孩都不笨,知道醫生只是沒想加重他們的心理力,真沒事兒的話就不用反復強調讓大人來了。
老教授把話說得那麼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個詞。
“這個癔癥聾呢,它不是說你就真聾了,畢竟咱們功能都好好的,是不?還是你神方面的影響,力太大啊,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麼刺激都沒有,做了個害怕的夢,醒來就突然聽不見了,所以沒關系,別擔心,能治。”
潘小卓擰著眉問:“那得怎麼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們,才慢慢地說:“這得去神科,如果是質有病變可以在我們這兒,但咱們沒真病,去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力沒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復了,都不是絕對的。”
一個可能是“癔癥聾”砸下來,這四個字怎麼看怎麼聽它都不帶個好樣。
大夫的話乍一聽像是寬心,畢竟耳朵沒壞。
兩個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學校,在車上潘小卓問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說嗎?”
陶淮南“嗯”了聲,知道耳朵沒壞多多寬了點心,低聲道:“考完再說吧。”
潘小卓很擔心,卻又安他:“沒事兒的,你別害怕。”
陶淮南點頭,說:“我不害怕。”
那時候陶淮南的確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沒壞就行。
Advertisement
可事分兩面,耳朵沒壞還聽不見,一旦治不好就一點辦法都沒了,連戴助聽的機會都沒有。耳鳴、聲音小、聽不清,這些過渡都沒有,直接就是徹底切斷了。
從那天開始,陶淮南開始了跟寂靜之間沉默的抗爭,恐懼安靜,卻也在堅強地和它做抵抗。
他開始依賴聲音,只有聽著聲音才覺得安穩。他需要一直戴著耳機,這樣他一旦聽不見了就能第一時間發現。耳機還能做他的偽裝,給他的聽不見提供了個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沒課的時候,一對小同桌又著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幫他約了次治療,帶著醫院的診斷和那些檢查結果和報告,去了家心理醫院。這次的醫生很年輕,說需要長期治療。他同樣沒把話說得很嚴重,可是在那他們到了個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這個病,聾了三年了,到現在沒有丁點好轉的跡象,徹底徹底聽不見了。
那是一段很艱難的日子,每一分鐘都很煎熬。
陶淮南擔心哥哥,也擔心自己。他得復習準備高考,最難的是還要在聽不見的時候不被哥哥們發現。遲騁不好騙,他對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到骨子里的。
陶淮南只能一直捂著耳機,無論聽不聽得見的時候都說話,回應。讓他的遲鈍和不耐煩變一段時間里的常態,這樣才不會在某些時刻顯得突兀和怪異。
可哥哥們他,陶淮南反常地發脾氣和他那些煩躁的語氣他們都縱著他。某一次遲騁摔了他的耳機,陶淮南知道他或許是生氣了。陶淮南最不想騙他,他對遲騁撒的每一句謊,每一句裝出來的憤怒和不耐煩,都是割在自己上的刀。
隨著聽不見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陶淮南開始變得恐懼。
Advertisement
他每天都在手機上查著資料,查癔癥耳聾,查過往病例。盲人模式沒那麼好用,有些件完善得好,可網頁不行,上面字和鏈接都很多,經常會點錯。陶淮南在麻麻的文字中尋找著能夠安自己的容,在它們上找寄托。
治不好的那麼多,他們都抱著能治愈的心態,徹底邁進了失聰人群。
黑暗和寂靜是所有負面緒的溫床。
在聽不見的時間里,陶淮南最大的就是孤獨。那是一種絕對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孤獨。孤獨之下產生絕、恐懼,和強烈的窒息憋悶。
每一次聽不見的時候,他都會捂著耳朵,想起那年見過的那個盲聾小孩。他活得像個小,在自己的世界里封閉地滿足著。說他永遠停在了嬰兒時期,那樣也未必不好。
陶淮南也想起了小時候盲校的那個薩克斯吹得很好的男孩,他得到過,聽見過,所以回不去嬰兒的狀態了。從十二樓跳下去的時候,一定也是害怕的。
陶淮南比起那個薩克斯小男孩,他得到過更多,牽絆也更多。
他有哥哥。曉東現在有湯哥了,可遲騁什麼都沒有,遲騁只有他。陶淮南和遲騁是綁在一起的一個整,遲騁永遠不會放開他。
陶淮南每一次都會想,如果他也變了一個盲聾人,他會不會選擇像那個盲聾小孩一樣活著,靠手去辨認簡單的來大概得知些信息,自己沉進深海里,靠著每天被遲騁和哥照顧著的吃喝拉撒,來繼續和這個世界的唯一聯系。
陶淮南那麼聽遲騁的心跳,在他能聽見的時候,他不止一次地想把自己裝進遲騁的心臟里關起來。被遲騁的心跳包圍著讓他覺得踏實,只有那樣才踏實。
陶淮南已經越來越狼狽了,他漸漸出了更多端倪,但是哥哥們都忍著他,不愿意在高考前惹他。
陶淮南焦灼地希這一切快點結束,也在每一次恢復聽力的時候希這是最后一次。
遲騁親他的時候陶淮南總是深深地吻他,小哥真的變了很多,不那麼發脾氣了,生氣之后只要陶淮南變乖了他就還能縱容地抱著,小哥變了。
陶淮南特別、特別他。
到高考前夕,陶淮南的失聰已經嚴重到以天為周期,早上睜眼就聽不見,一整天都恢復不過來。
希漸漸被磨得沒有了,那種只能通過氣流的輕微變化和邊料被子的才能知道有人來了的覺,讓人不過氣。陶淮南不知道是真的有人來了還是他太敏導致的幻覺,只能在每一次覺到的時候,無論真假,都皺著眉說一句“我現在不想說話”。
如果真有人來了會被他刺這一句,如果沒有人來,那他就像個對著空氣說話的神障礙患者。
高考最后一天下午,陶淮南完全是在無聲中考完的試。偽裝了那麼多天的沉默,裝了那麼多天的心理問題,他倚著椅背裝太累睡著了。
回去之后他把自己鎖進了房間里。
整整兩天,陶淮南沒聽到過一點聲音,他每一天都在重復著刺傷別人和看起來像個瘋子的過程。
那兩天長得像十年那麼長。
沒有時間概念,沒有白天黑夜,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黑,和沒有盡頭的孤獨。
猜你喜歡
-
連載27 章
性愛天堂『總攻』
總攻。內含各種誘惑而羞恥、恥辱的play,還有性愛調教 口嫌體正直,肉汁四濺的董事長已完結。含野外調教,羞恥性教育 高冷乖巧,不停被調教的男神影帝已完結。含繩束縛,女裝,道具 情色的皇帝篇完結。含吸奶,灌子宮,恥辱調教 最後結局篇是黑暗命運的皇帝作為總攻的cp。有以往的悲慘性虐也有在一起之後的恩愛做愛,皇上的人妻誘惑。 壁尻,被性愛俘獲的總督,包括總攻的假期系列其餘都是特別篇,play跟花樣多
14.1萬字8 25448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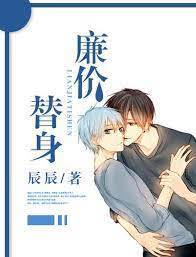
廉價替身
童笙十三歲那年認識了雷瑾言,便發誓一定要得到這個男人。 他費勁心機,甚至不惜將自己送上他的床,他以為男人對他總有那麼點感情。 卻不想他竟親自己將自己關進了監獄。 他不甘,“這麼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麼?我哪里不如他。” 男人諷刺著道:“你跟他比?在我看來,你哪里都不如他,至少他不會賤的隨便給人睡。” 當他站在鐵窗前淚流滿面的時候,他終于明白, 原來,自始至終,他都不過是個陪睡的廉價替身罷了! 同系列司洋篇【壓你上了癮】已完結,有興趣的親可以去看看!
51.1萬字8 9389 -
完結176 章

穿成重生男主前男友
宋暄和穿進了一本叫做《總裁和他的七個男友》的書裡,變成了總裁的砲灰前男友宋暄和。 書裡的宋暄和:身高一米八,顏值碾壓一眾一線明星,祖上三代經商,妥妥的富三代。 任誰穿到這樣一個人身上都不虧,然而,這是一本重生文。 書裡的宋暄和作為虐了男主八百遍,並且間接害死男主的兇手,面對重生後直接黑化的男主, 最後的結局可想而知——不但名聲掃地,而且還死無全屍。 現在,他成了這個注定要死無全屍的砲灰前男友。- 系統: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男主有點奇怪?像是在暗中計劃什麼。 宋暄和:計劃著怎麼殺我? 總裁:不,計劃怎麼吃你。 躺在床上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宋暄和將系統罵了八百遍——說好的男主是總受呢!
60萬字8 11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