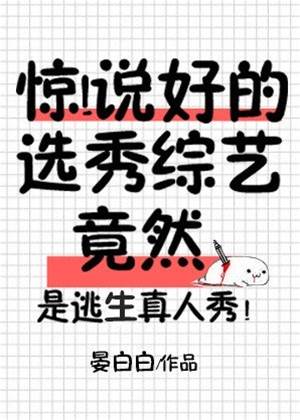《限時占有(ABO)》 第三十六章
酒店的房門咣當一聲被關上,涂言跟著抖了一下。他用余暼顧沉白的神,看到他眉頭鎖,角抿一條直線,似是強忍著怒火。
涂言自知理虧,小聲地嘟囔了一句:“我又沒傷。”
顧沉白竟然沒搭理他,略過他徑直往臥房走。
涂言沒見過顧沉白對他生氣的樣子,一時慌張起來,無措地跟上去,把口袋里的錄音筆拿給顧沉白看,為自己辯解:“我不是要去跟他打架,我就是想從他里套話,留作證據用,而且、而且我也沒有真手,就是嚇唬他,推了他兩把。”
顧沉白了西裝外套,放在床尾,然后松了松領帶,轉對涂言說:“這不是你能懷著孕和人打架的理由。”
涂言語滯,張了張卻說不出話來,他知道顧沉白是真的生氣了。
可顧沉白憑什麼生氣?涂言是為了他才打的架。許家桉用那麼難聽的話辱顧沉白,涂言怎麼可以忍?他沒把他打死都是好的。
他為了顧沉白出頭,顧沉白卻嫌他沖莽撞。
涂言一陣委屈,看著顧沉白冷冽的側臉,怨怨地想:顧沉白現在滿心滿眼都只有小兔崽,只擔心小兔崽的安全,也不問問他有沒有傷。果然,有了小兔崽之后,他就不是顧沉白最的人了。
“一個月前你剛跟人了手,在酒吧那種地方打掉了抑制,撞出來的淤青才消下去,你又跑去跟人打架,”顧沉白眼睛里全是無奈,對涂言無計可施,“你是不是想要我的命?”
“別說的冠冕堂皇,你不就是怕我傷害到你的寶貝嗎?你放心好了,底下這幾個月我一定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敬心敬職地把他生下來給你,可以嗎?夠嗎?”涂言紅著眼,朝顧沉白吼道。
Advertisement
顧沉白被吼得直愣神,還沒等他反應過來,涂言就沖進衛生間,咣當一下把門摔上。
小家伙的脾氣真是一天比一天見長。
顧沉白哪里會真的和涂言生氣,不過是為了讓他長長記,現在效果達到,便見好就收,拄著手杖走到衛生間,敲了敲門,喊他“兔寶”。
涂言在里面喊:“你走,我不想看見你!”
“我走去哪兒啊?”顧沉白輕笑。
“跟我沒關系!”涂言的聲音里摻著哭腔,他把蓮蓬頭打開,企圖用水聲掩蓋。
顧沉白許久沒有再開口,他站在衛生間門口,等了幾分鐘,然后握住銅制門把,作極輕地打開了門。
涂言正背著門站在盥洗臺前,他低著頭,沒有注意到顧沉白的到來。
顧沉白走近了一些,便聽到涂言委屈的自言自語。
“……小兔崽,你出生之后不要跟我搶顧沉白好不好?不要讓他更喜歡你……”涂言半天才想好措辭,惡狠狠地著肚子說:“不然我一定把你扔掉。”
顧沉白的心都要融化了,他走上去從后面環住涂言的腰,把他攬進懷里。涂言被嚇得差點,連掙扎都忘了掙扎,一抬頭就看到顧沉白笑意晏晏的眼。
“誰準你謀害我的小兔崽?”
涂言眼圈更紅了,他覺得自己一遇到顧沉白,就變一個沒法控制緒的大麻煩,他總是哭,其實他一點都不喜歡哭。
齊瀾把他丟下一個人出國、涂飛宏為了一個項目把他的生日忘的一干二凈時,他都沒有哭。可他在顧沉白面前不就哭,一點出息都沒有。
“你是不是因為我懷孕了,才和我復婚的?”
顧沉白失笑,“這話又是哪兒來的?”
涂言捂著臉哭,半天才把真心話說出來:“那你為什麼都不問問我有沒有傷,疼不疼?”
Advertisement
這是涂言第一次對顧沉白示弱,放下自我防備的保護殼,沒有再說刺傷人的話,哭得像個要糖吃的小朋友。
顧沉白把他轉過來摟進懷里,哄道:“是我錯了,我不好,可是兔寶,事到如今,你還質疑我對你的嗎?”
顧沉白只簡單問了涂言一句,涂言就停止泣,可憐兮兮地盯著顧沉白,半晌又低下頭,把糊了一臉的眼淚全蹭在顧沉白的口。
這個問題是不需要回答的。
“兔寶有沒有傷?”顧沉白握住他的手,舉到眼前,一邊檢查一邊問:“他有沒有打到你?”
涂言搖頭,悶悶道:“我不會讓他打到我的。”
“這麼厲害?”
“因為、因為我是媽媽了。”
顧沉白怔了怔,然后把涂言的臉從懷里撈出來,住他的下和他對視,笑道:“你再說一遍?”
涂言抿,誓死不從。
顧沉白把手進涂言的邊,進飽滿的,準確地找到,他低頭在涂言的耳邊說:“兔寶,我有的是辦法讓你開口。”
涂言被顧沉白拎到盥洗臺上,子了一半堆在小上,背后是碩大冰涼的鏡子,顧沉白揭開抑制,alpha的信息素瞬間在衛生間里擴散開來,涂言逃也逃不掉,像被泡進糖水里,又漲又,手腳都沒有力氣,只能抬起屁敞著,任顧沉白的手指進出。
顧沉白的手指修長有力,從口捅進去,在涂言的腸壁上反復輾轉,不多時又加進一,三只手指同時搗進去的時候,涂言已經徹底沒有力氣了,半個子倒在鏡面上,腰不停地發,口里不斷涌出水來,把每一寸干都潤鋪平。
顧沉白把旁邊的蓮蓬頭關了,衛生間里突然安靜下來,只剩他指間的噗嗤水聲,還有涂言小小的聲。
Advertisement
“嗯……嗯……不要了……”
涂言上只剩一件僅能蔽的上,還被扯得只剩一粒紐扣負隅頑抗。反觀顧沉白,襯衫西整整齊齊,毫不,涂言氣惱不過,要去踹顧沉白,卻不想惹得顧沉白直接按上了他的敏點,輕慢捻,涂言一僵,然后就不能自控地尖出聲,下一秒,他就了出來,一半沾在顧沉白的襯衫上。
顧沉白笑了笑,取了旁邊的紙巾了下手,然后胳膊一攬,把涂言抱下來,又哄著神志不清的他:“兔寶,去床上。”
涂言剛爬上床,還沒來得及躺下,就被顧沉白托起屁頂了進去。
“顧沉白!”
被罵的人毫無悔意,仗著自己不好,整個人都在涂言上,也頂到最深,顧沉白了腰,和涂言的生腔打了個招呼。
涂言登時睜大了眼,他知道顧沉白不會進去,況且孕期的生腔也不會開啟,可他還是本能地到驚慌,抓了被子,哭著求顧沉白,“不行,不行……”
“怎麼辦?”顧沉白低頭咬了咬涂言的耳朵,“我想見見我的小兔崽。”
“不行,求你了,不能進,”涂言腦袋全空了,完全忘了生理課老師教的基本常識,在顧沉白趁人之危的胡謅下連聲哀求,“不能進的……嗚嗚求你了。”
“這樣求可不行啊。”顧沉白抹掉涂言臉上的眼淚,親了親他的,“那你告訴我,你什麼?”
涂言眼淚汪汪地答:“兔寶。”
“兔寶是誰?”
涂言不肯說,顧沉白就把出來一半,然后猛地頂進去,涂言覺自己被頂得就要撞上床頭了,他連忙喊:“顧沉白,顧沉白的老婆。”
顧沉白笑意漸深,明知故問道:“兔寶,你的初是誰啊?”
Advertisement
涂言的被顧沉白折起來著,他覺得自己像蒸籠里五花大綁的螃蟹,沒有半點活路,他了鼻子,小聲說:“是你。”
“真的沒有喜歡過別人麼?”
“沒有。”
顧沉白抱起他,含住他的,放棄克制和忍,發了瘋似的吻他,他抵在涂言的生腔腔口一次一次地,涂言就跟著他抖戰栗,頸相擁。
顧沉白做了幾次,涂言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自己最后什麼都不出來了,連尿都尿不出來,著子站在馬桶邊,扶著自己的小兄弟哭無淚。
顧沉白披了件浴袍,慢悠悠走過來,一臉無辜地摟住他,“兔寶這是怎麼了?”
涂言扭著腰想掙開他。
顧沉白笑著說:“我幫你,乖,我幫你。”
他用右手握住涂言的小,掌心的繭蹭著,惹得涂言瞬間輕哼出聲,顧沉白一下一下幫他擼著,正要萌生出些許尿意時,顧沉白又從后面頂了進來。
涂言跪在馬桶圈上,兩手撐著瓷磚墻,虛弱道:“顧沉白,你等著。”
顧沉白很誠懇地道了歉,然后頂得更兇。
最后涂言被顧沉白洗干凈子,拉上床蓋好被子,摟進懷里的時候,他的靈魂已經完全和離了,腦海里只有一個疑問:他和顧沉白到底哪個是殘疾人。
猜你喜歡
-
完結58 章

離婚
關鍵字:弱受,生子,狗血,惡俗,古早味,一時爽,不換攻,HE。 一個不那麼渣看起來卻很氣人的攻和一個弱弱的嬌妻小美人受 發揚傳統美德,看文先看文案,雷點都在上面。 一時興起寫的,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什麼都不保證。 原文案: 結婚快四年,Alpha收到了小嬌妻連續半個月的離婚協議書。
7.7萬字8 9015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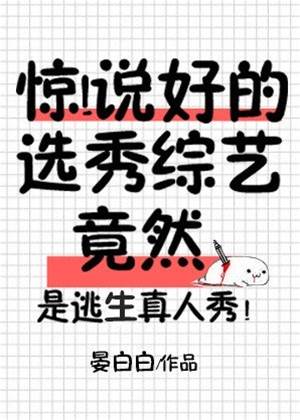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
完結149 章

美貌廢物被迫登基後
《美貌廢物被迫登基後》作者:謝滄浪【完結】 文案 李氏王朝末年,朝局風雲詭譎。 新任平南王雲殷,狠戾果決,與當朝太子相交甚篤。 一朝宮變,天子崩、太子被毒殺於宮中。雲殷帶兵平叛,親手將弒父殺弟的大皇子斬殺於階前。 自此,帝位空懸。 就在世人皆猜測,這位雷霆手段的異姓王將要擁兵自立之時,雲殷入了宮。
21.3萬字8 5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