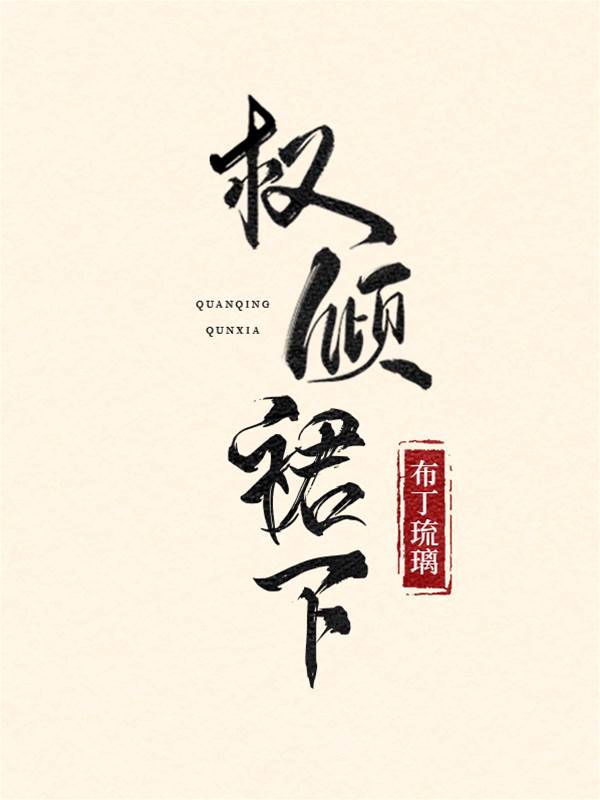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側妃上位記》 第73章 問罪
周韞和傅昀趕到綏合院時,綏合院一團。
莊宜穗比他們早到一些,此時臉上刻著怒意,室孟安攸的哭喊聲不停,毫不留地斥著劉氏:“孟氏有孕在,你有何委屈,不能找本妃或王爺作主,非要和起爭執?”
話音剛落,就見提花簾子被掀起,傅昀和周韞一起踏進來,頓了頓,視線在周韞微凸起的小腹上一掃而過。
周韞注意到這抹視線,不著痕跡地擰了擰眉,側頭覷了一眼邊人的臉。
傅昀稍沉著臉,旁人看不出他心如何。
一片行禮聲中,周韞稍退了一步,斂眸朝室中間看去。
劉氏跪在地上,低垂著頭,人看不清臉上的神。
周韞被扶著朝位置上走去,一手輕耳畔,似嫌棄吵鬧,蹙著細眉,不耐道:“夠了,都吵嚷什麼?孟良娣現在況如何了?”
不聲地,引過了話題,眾人視線不再停留在劉氏上。
劉氏聽見的聲音,繃的子才些許放松。
出聲后,室都微微有些寂靜,畢竟,這副模樣,過于理所當然了些,王妃還在上方呢,這副架勢,倒比莊宜穗更像正妃。
周韞對此視而不見,自從爺走后,們聯手宮后,周韞就沒打算日后再給莊宜穗留臉面。
即使這般張揚,只要這王府真正的主子默許了,莊宜穗能耐何?
傅昀無聲地看了一眼,倏地響起那日清醒后,仰在他懷中,涼涼地說“我不會放過們的”的景。
他上前坐在主位上,重復了的話:
“孟良娣況如何?”
似無聲地默許了的行為。
在場的眾人臉稍變,悄悄看了一眼莊宜穗的臉,卻見莊宜穗臉毫不變,只低低輕嘆了一聲,臉上皆是擔憂:“太醫還在里面,只聽孟妹妹的慘聲,妾心中有些擔憂。”
Advertisement
這番話,傅昀多看了一眼,似有些驚詫。
仿若他去一趟郭城,回來后,這府中后院的子皆有些變化。
周韞自不必說。
王妃仿若也比往日更大度溫和了些,若是之前還有些浮于表面,現在,卻似多了些真心實意。
周韞坐在位置上,假裝沒看見傅昀的驚詫,若無其事地著帕子遮了遮角。
若出了這麼大的變故,莊宜穗還沒有一點改變,那才會驚訝呢,驚訝于莊府費盡心思究竟怎麼會教出這麼個嫡出來。
秋時坐在周韞對面,眸稍變了變,好似自貴妃一事后,府中有些事,就出乎了的意料。
覷了眼莊宜穗后的氿雅,之前氿雅待態度和善,如今卻對避之不及。
秋時有些想不明白。
莊宜穗究竟怎麼了?
頓了頓,才搖了搖頭,說:“劉妹妹,如今孟妹妹子重,你怎得會和起了沖突?”
一句話,又將重點拉回劉氏上。
周韞輕挑眉,徐徐看向秋時,不待劉氏說話,就反問了一句:“本妃聽說,側妃當時也在場?”
言下之意,你都在場了,當時不阻攔,現在還問什麼問?
秋時也的確能忍,被這般嘲諷,臉都沒有一變化,只咬,看了傅昀一眼,似有些委屈:“妾的確在場,卻是趕去晚了些。”
話音模糊,說得也不盡然,的凝景苑離后花園甚近,趕到時,事態還可控,不過,為何要攔?
一方有孕,一方是周韞的人,鬧起來就鬧起來,攔下有何好?
周韞對是什麼樣的人,心知肚明,聽了這話,只嘲諷地笑了笑,沒再接話。
也沒幫劉氏說什麼。
畢竟兩人爭執,導致孟安攸摔倒是事實,劉氏不做出解釋,本不可行。
Advertisement
傅昀一直沒說話,等二人爭執停下來后,才沉眉劉氏,稍擰眉。
對于劉氏,他素來是放心的。
不管是在周韞等人進府前,還是進府后,不得不說,行事都甚為妥當,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都分得清楚。
如今居然會和孟安攸在大庭廣眾之下起爭執,完全不像是的作風。
若說,是周韞,倒還做得出來。
想到這里,傅昀擰了擰眉,沉聲道:
“說吧,究竟怎麼回事?”
話音甫落,室就有幾人不著痕跡地變了變眸,聽爺這語氣,似也沒有多大怒意。
究竟是過于不在意孟良娣,還是說,爺就這般信任劉氏?
劉氏在王府待了四年有余,對傅昀也有幾分了解,抬起頭,往日的臉上皆是苦,半晌才勉強出一句話:“是妾的錯,求爺降罪。”
周韞立即擰起眉,這什麼都不說,直接認罪是什麼病?
傅昀也抬起頭看了一眼,他沒先問旁人,而是讓說,就是給解釋的機會。
他臉沉了下來,劉氏邊的秋寒見此,忙拉住劉氏的手臂,急得快哭出來:“不是這樣的!王爺,您聽奴婢解釋!”
“是孟良娣!是孟良娣先諷刺我們主子,說、說——說我家主子是不會下蛋的、的……”
后面連個字,終究是說不出口。
劉氏眼淚倏地掉了下來,堪堪側頭,抹了一把眼淚,攔住秋寒,皮子都在:“是妾的錯,進府多年,沒能給爺誕下一子半,是妾沒福氣,怨不得孟妹、姐姐這般說……”
頓了一下,生生地改了。
這番稱呼上的變化,不難讓人猜出兩人究竟為何鬧出矛盾。
屋中站著的人,有好些人都變了臉,連莊宜穗都稍稍變了神。
Advertisement
劉氏沒能有孕,被罵這般,可這滿府,有孕的不過孟安攸和周側妃二人罷了,這句話,豈不是把們皆罵了進去?
傅昀臉立即沉下來,孟良娣罵的這一句,不亞于把他也罵了進去。
他擰眉冷聲斥了句:
“你比先進府,這番沒規矩的話,別本王再聽見。”
說的是稱呼一事,劉氏堪堪咬,說不出話來。
秋寒卻抹著眼淚,還沒有停:
“王爺,若只如此,我家主子看在孟良娣有孕份上,本想退一步,相安無事,可是孟良娣卻說……”
回頭看了一眼周韞,這一眼,周韞臉變了變。
怎得?
這二人牽扯,還嘲諷到了不?
秋寒說:“孟良娣說我家主子,日日往錦和苑跑,小心染到側妃娘娘,側妃娘娘——”
一聲脆響,打斷了秋寒的話。
周韞冷寒著臉,手邊的杯盞被摔在地上,碎了一地。
秋寒嚇得立即噤聲。
傅昀臉也甚是難堪,他沉著臉,甚至對秋寒都有些遷怒:“不知所謂!”
秋寒未盡之言,并不難猜,不過是一些類似“側妃娘娘也如我家主子一般”這種的話罷了。
看似好意替周韞擔憂。
偏生周韞如今有著孕,這般言辭,不亞于詛咒。
綏合院的奴才嚇得跪了一地,孟安攸伺候的萩榮似想辯解什麼,可周韞就在此時涼涼出聲:“一個良娣,敢如何大放厥詞,看來是真的仗著腹中有塊免死金牌,旁人奈何不得了?”
一句輕諷,旁人說來倒也不如何。
但一說,秋時沒忍住朝看了一眼,怎得好意思說出這話的?
如今貴妃去世,即使爺寵周韞,可若腹中沒有子嗣,敢在府中還如此張揚?
Advertisement
莊宜穗打斷周韞的話,擰起眉:
“即使孟良娣有錯在先,但你也不該直接和起爭執。”
周韞聽得好笑,不顧份尊卑,直接側頭,嘲諷發問:“怎麼?莫非還要等著繼續蹬鼻子上臉?”
莊宜穗被噎住,視線轉向周韞,出一句:
“可來找本妃或王爺作主。”
“作主?那王妃姐姐是要打,還是罰?”周韞一句諷問,不待莊宜穗回答,又說:“姐姐大度,恐怕頂多不過訓斥幾句,就放過了此事。”
“可有一就有二,不敬上位,言論有失,本是該罰,不長記,日后豈不是還要再犯?”
眾人皆一驚,傅昀也有些頭疼,本是劉氏和孟氏之間的問題,如今發展這般,倒了王妃和側妃之間的擂臺。
莊宜穗冷眸看向周韞,周韞抬眸,毫不怵地回去,莊宜穗眸稍暗,說:“何事比得過腹中的子嗣?”
周韞方才的話有一句沒錯,孟安攸懷著孕,在這王府中,就的的確確是持著一枚免死金牌。
你再不滿,又能如何?
周韞心知這個道理,佯裝不耐地說:
“兩人不過起了爭執,不慎摔倒,也不一定是劉氏所致。”
看向旁人:“你們誰看見劉良娣推了孟良娣了?”
眾人皆啞聲,且不說們當時不在場,就算在場,當時場景混,誰也不能說,就一定是劉良娣推了孟良娣了。
無人回答,周韞輕揚眉梢,看向莊宜穗:
“王妃姐姐可看見了,既不是劉氏的錯,還是先起來吧。”
“明明了委屈,還要被責罰,這般下來,恐要旁的妹妹心涼了。”
莊宜穗簡直要被這番無賴的模樣氣笑了。
后院中皆這般,誰傷,誰就是害者,另一人自然就有罪。
到了周韞口中,倒了孟安攸自作自了?
莊宜穗卻沒和爭執,只輕嘆一聲,搖了搖頭:“本妃說不過妹妹,還是待太醫出來,知曉況后,再說吧。”
現在說再多,皆無用。
若孟安攸無事,周韞那番話,恐還可以當理由替劉氏罪。
可若反之,即使劉氏再多委屈,也逃不過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0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2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392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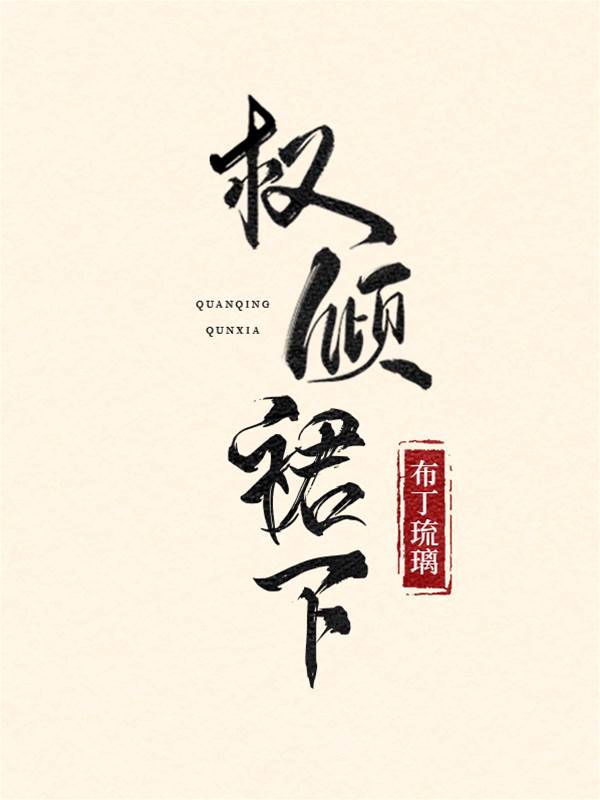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7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