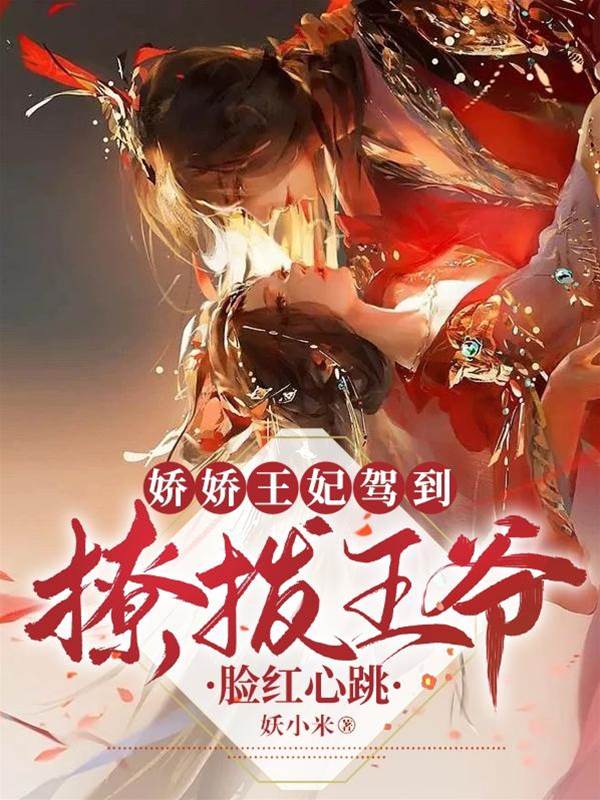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別枝》 第32章
給主子們遞個信兒原也不是大事,然這丫鬟神有異,加之信封外又未有署名,這才人心有存疑。
可這個方向,是去洗春苑的。
從遮月手中接過信,付茗頌好奇的看了那丫鬟一眼,隨即才將目放在信紙上。
【亥時二刻,留門。】
姑娘夾著信紙的指尖不由一頓,這個時辰,這幾個字,任誰都會想岔吧。
下意識屏住呼吸,發覺信封里還裝有重,拿出來一瞧,已是摔斷了的玉簪。
可即便摔斷了,也一眼便能認出,這簪子是云姨娘的,還是尤為喜的一件首飾,曾連著好幾日都戴著。
一件私,一封信,一句留門。
怎麼看,都盡顯曖昧。
可信紙上這字雖獷有力,是男子的字跡,但付茗頌見過付嚴栢的字,端莊工整,絕非這般。
何況,以對付嚴栢的了解,他也不是個懂趣的人,更做不來這等事。
稍一思索,便有了答案。
但難免心驚,老太太這般重面之人,云姨娘竟然敢在付家的宅院會男人?
將信紙折起收進信封,低頭道:“你——”
“奴婢什麼都不知,奴婢今夜,也未曾給誰遞過信,也未曾見過五姑娘!”丫鬟將頭磕在地上,渾抖的像篩子,生怕這事兒連累到自個兒。
付茗頌一頓,輕聲道:“你回吧。”
丫鬟連連應是,踉蹌爬起,一下便跑的沒了蹤影。
—
付宅正中的園子有一水榭亭臺,能將整個付宅的格局盡收眼底。
自然,也能瞧見洗春苑的里。
許是天已晚,洗春苑中連個走的丫鬟都沒有,空寂的院落,幾間屋子皆是門窗閉,連簇也瞧不見。
在這個時辰,也是正常的。
Advertisement
夏夜風涼,付茗頌抬手了手臂,在這兒了一刻鐘,眼看過了亥時二刻,莫不是想錯了?
遮月悄悄打了個呵欠,“姑娘,會不會弄錯了,云姨娘怎可能如此大膽,何況對老爺——”
驀地,遮月睜大眼睛,瞧見個穿灰棕長袍的男子從后邊的林子里匆匆至洗春苑門前,回頭四下打量一眼,方才推門進去。
說巧不巧,正好往主屋的方向去,只見他在窗子旁停了一瞬,隨后那屋門,便從里頭拉開了。
遮月全然懵了,饒是眼神再不好,也能瞧出這人定不可能是老爺啊。
高,量,哪哪都不像。
這個時辰,一個外男進了姨娘房中,鬼鬼祟祟,除了-,還真想不出別的緣由了!
震驚過后,遮月一改困意,整個人神煥發,肅起臉道,“姑娘,這事若是傳出去,按照規矩,云姨娘可是要沉塘的。從前咱們小娘子的事就是從里傳出來,生怕外人不知寬容大方,如今干出這般齷鹺事兒,咱可不能放過!”
付茗頌緩緩收回目,偏頭瞧遮月,見拳頭都握了,忍不住笑問,“那你說如何?”
“自然是讓眾人皆知,從前如何對姑娘的,就也嘗嘗這滋味兒。”
月下的姑娘角輕斂,方才瞧見這一幕時,一氣涌上頭頂,恨不得將云姨娘的骯臟事廣而告之,再將從前的那些污言穢語,一并還回去。
如此一來,付姝妍便要到曾經與一般的待遇,甚至更為凄慘。
生母私通外男,是這項罪名扣下來,將來就連的婚事都得到牽連。
正如老太太曾經敲打時說的,就算是一般人家,都瞧不上。
Advertisement
而那個向來注重面的父親,怕是要告假三日,無見人了。
—
清晨,姜氏梳洗過后,早膳還來得及用便匆匆踏出屋門,見茗頌著一青綠站在廊下,忙迎了上去。
“五丫頭今日怎過來了?昨個兒我讓吳媽媽將嫁妝記了冊子,你可瞧過了?”姜氏說話恭敬小心,將請進屋里。
“瞧過了,母親心細,都妥當。”笑笑,將信紙連帶摔斷的玉簪擱在桌上,推給姜氏,“昨個兒,瞧見云姨娘屋里進了人,也不知是誰,茗兒思來想去,這事還是告知母親的好。”
說罷,小姑娘捧起杯盞抿了口茶,到底還是有些張。
姜氏聽的一愣,遲疑的打開信紙一瞧,再聯系這丫頭的話,臉一變。
抬頭屏退了丫鬟婆子,又將信收到了匣子里,“可有外人知曉?”
見搖頭,姜氏臉一松,長長舒了口氣。
若是一般事兒,自然樂得云姨娘栽跟頭,可這事若是鬧大了,只糟踐付姝妍的婚事也就罷了,若是還牽連的云兒,那便不值了。
思此,姜氏又是一怔。能考慮這些,可五丫頭全然不必,立后大典定下,左右也跑不了。
姜氏心下微,起看向,“五丫頭,這事我記心上了,你的婚事是皇家大事兒,一應時宜都有務府和禮部的人持,說到底我幫不上忙,但你放心,該付家做的,我定仔仔細細,半點不落。”
說罷,不等茗頌回話,姜氏接著又說,“我知你在云小娘那兒了不委屈,這事雖不好聲張,但該置的定置。”
茗頌角輕輕彎了彎,說話依舊小聲:“謝過母親。”
姜氏哪里敢擔一聲謝,搖了搖頭又道:“不過…你尚在閨中,這證據,便不說是你遞的,可好?”
Advertisement
姜氏話說到這個份上,茗頌微微訝然,還以為要廢一番口舌。
如此,算是最周全了。
—
五月十九,繡娘最后來量一回材,便要將禮服的尺寸的給定下。
誰知這麼接連一月來,反而瘦了,本就掌大的腰肢更不堪一握,這腰圍又得再改改。
姜氏也在這日將的嫁妝定下,是瞧名冊上記的件,好似要將付家給掏空似的。
而最最要的,是一莊子。
地京南,好地段。
這莊子雖算不得姜氏私庫,但卻是一直由打理,算是能拿出的最好的一了。
連遮月都不由驚呼,“姑娘,這樣好的莊子,夫人竟舍得。”
付茗頌合上冊子,倒也不覺驚訝。
姜氏做了幾十年的大夫人,最顧面。如今記在姜氏名下,便是的兒,是嫡,嫁的還是那可不可攀的九五至尊,就是咬著牙,也得全了這尊貴。
可茗頌想想這緣由,小臉并未有多喜。
天稍沉,姑娘了眼睛,已是有些困意,正遮月給拆發髻時,徐媽媽腳不大利索的走來,珠簾一陣輕響。
“姑娘,姜氏將人捆了,了牙婆子來,契都收了,吳媽媽特地來知會老奴一聲,說是老爺與老太太都知曉了。”
聞言,茗頌揚起頭,“是要發賣了?”
安媽媽低聲道:“原該沉塘的,但此事不宜做大,夫人便想了這麼個法子,屆時便對外人道是回鄉養病了,老太太和老爺未吭聲,允了。”
可依姜氏對云姨娘多年厭惡,找的牙婆子怕也不是個好的。
一朝發賣,云姨娘可是完了。
茗頌抿了抿,腦袋輕輕點了下,說不上來什麼滋味兒。
須臾,又問:“二姐姐呢?”
Advertisement
“在老爺跟前哭呢。”
聞言,付茗頌徹底收回目,低頭應了聲。
還能在付嚴栢面前哭,已是好的了。
夜幕降臨,萬家燈火滅,京城籠罩在一片漆黑中。
皇宮東面,景宮還燃著微。
元祿一邊燃了火折子去點龍涎香,一邊回道,“五姑娘沒聲張,這事友付夫人辦了,說是要發賣了,老奴倒覺得此舉尤妥,既未放過惡人,也周全了該周全的。”
聞恕神淡淡,向來都很聰明。裝傻充愣是的本事,賣巧做乖也是的本事,膽小怯懦,不出頭,不拔尖,恨不能將自己一小只,誰也看不到才好。
不管置于何地,總有應對的法子。
可這一點,真人高興不起來。
男人手中翻著繡娘記下的數字,眼看幾日下來,腰圍越來越小,雖他看不見,可是想想那腰,怕是一折就斷,握都握不得。
男人眉目一蹙,還不如在永福宮養著。
元祿見他瞧著那幾個字,臉難看,一下便猜到他在想甚,是以輕言道,“素心捎信道,五姑娘幾日來無甚胃口,甚至還連夜噩夢,許是要大婚,張了。”
這話,不如不說。
男人臉涼涼的撇開冊子,也是,怕他怕的都不敢拿正眼瞧他,現下嚇到吃不好睡不著,也不反常。
指不定夢中,他還是個索命的鬼魅。
作者有話要說:
還真是。
以后睡在聞恕床上,付慫慫夜夜噩夢==(我把玩車推過來給你們了,自行腦補
下一章能婚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709 章

攝政冷王悄醫妃
特工軍醫穿越為相府嫡女,受父親與庶母迫害,嫁與攝政王,憑著一身的醫術,她在鬥爭中遊刃有餘,誅太子,救梁王,除瘟疫,從一個畏畏縮縮的相府小姐蛻變成可以與他並肩 ...
255.2萬字8.18 63160 -
完結449 章

郡主囂張:誤惹腹黑世子
一場精心謀劃的空難,顧曦穿越成了安平公主府里人人欺賤的癡傻嫡女。親娘早死,渣爹色迷心竅,與妾室母女狼狽為奸,企圖謀奪公主府的一切。前世的顧清惜,以為裝瘋賣傻,隱忍退讓便能茍活,卻仍被姨娘,庶妹奸計毒害。今生,顧曦決心將忍字訣丟一邊!專注斗姨…
120.8萬字8.09 87940 -
完結691 章

公府貴媳
晏長風嫁給病秧子裴二少,是奔著滅他全家去的。后來,她眼睜睜看著這病秧子幫她滅了全家,又一手將她捧成了天下第一皇商。……晏長風的大姐莫名其妙的瘋了,瘋言瘋語地說著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她說爹爹將死,母親殉情,家產被姨娘霸占,而她們姐妹倆會被趕出家門。她說她未來的世子夫君是個渣,搶奪嫁妝,寵妾殺妻,連親骨肉也不放過。晏長風難以置信,卻也做足了準備。后來證明,爹爹確實身處險境,姨娘確實狼子野心,她為了不讓后面的悲劇發生,代替姐姐嫁入國公府。然后,她嫁給了國公府最不起眼的一個病秧子。當她要大開殺戒時,那病...
110.4萬字8 25343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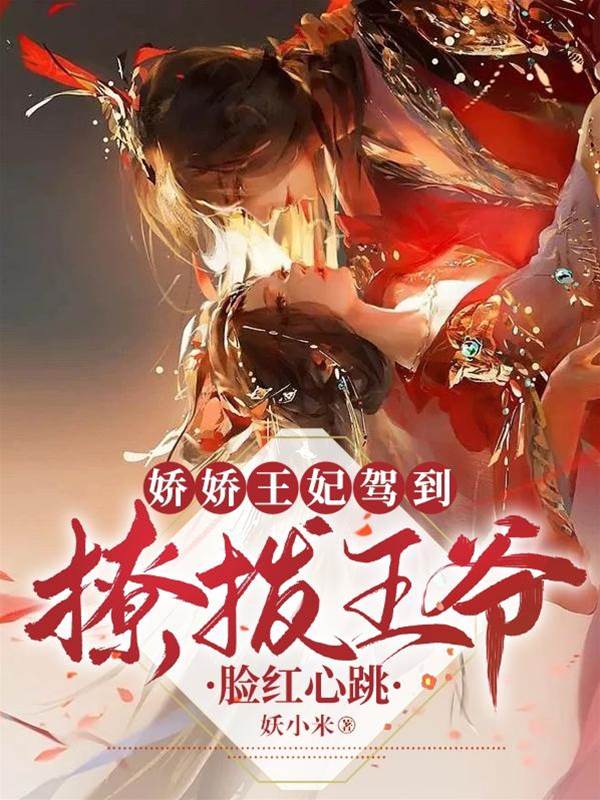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236 章
選秀當天被爆孕吐,冤種王爺喜當爹
【女強+萌寶+醫妃+偽綠帽】 一朝穿越,神醫沈木綰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四小姐,第一天就被人「吃干抹凈! 被狗咬了一口就罷了,竟然在選妃當場害喜! 還沒進宮就給皇帝戴綠帽?! 沈木綰:完了! 芭比Q了! 瑾北王表示莫慌:我,大冤種。 人在家中坐,綠帽天上來。 御賜綠帽,眾人皆諷。 催眠術,神醫術,沈木綰生了娃打腫他們的碧蓮! 不要臉的瑾北王每天拿著鋪蓋送上門:「媳婦兒,孩子生下來吧,我跟他姓」
42.6萬字7.93 138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