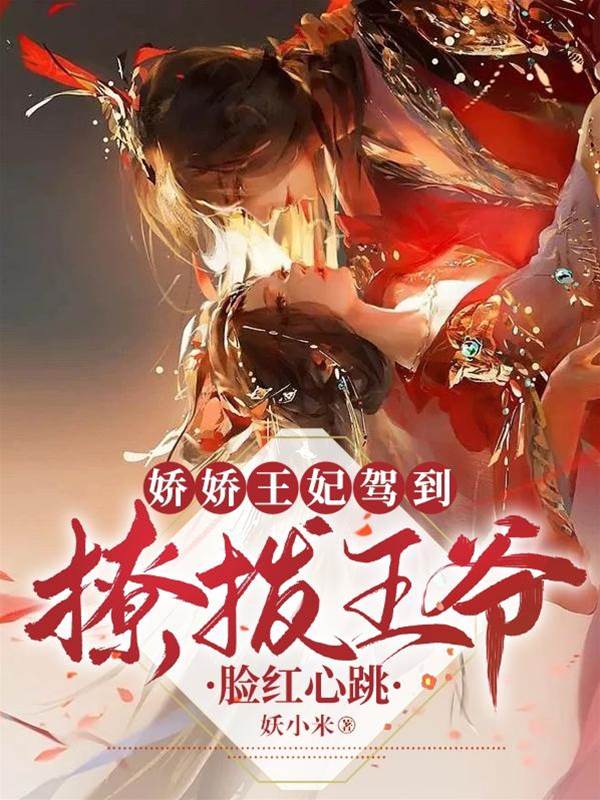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被廢后成了鄰國皇帝的獨寵》 第29章 修羅 兩個男人對上了視線
宋寒時沒有言語, 眸越過面前的夏倚照落在了后被忽略的慶忠公公上。
慶忠公公似乎領會了他眼中的深意,微微垂眸,轉離開。
夏倚照并不在意旁人, 只直直進了面前男人的雙眸,“我需要你下一道圣旨, 宋寒時, 我要出宮。”
宋寒時的視線重新向, 眉眼微, 卻只是平緩道:“這不可能。”
夏倚照知道事的進展不會很順利,但是聽到他毫不猶豫的拒絕還是有些惱火,“宋寒時,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上前一步,腰間的佩劍撞上他的書案,方才被白紙掩蓋的畫卷猝不及防地闖的視線——
那是一張畫紙, 上面赫然是一個青靈的, 眉眼婉約人,乍一看跟幾乎是同一人。
只是有春兒在, 夏倚照認為自己不該太過自信。
“阿照……”宋寒時注意到的視線,順著目凝視的方向看過去, 眉頭微微蹙了起來,隨即染上一點笑意,“這張畫了很久,一直想著你十年前的樣子, 現在你回來了, 才發現有很多要改的地方。”
這十年他一點都不敢停歇,將一個搖搖墜的國度治理如今的模樣并不容易,他的父皇將宋國變得千瘡百孔, 風雨飄搖,那個時候的宋國甚至只能依靠他們的皇后去鄰國做人質才能得來一點息的空間——
思及此,男人的眸緩緩沉淡下來。
如若不是那臨危命的責任,他們之間不必有這十年的間隙。
他甚至連閉眼的時間都計算得確,不敢有毫的懈怠,唯一可以放松的事就是偶爾在書房描繪的樣子。
這是他唯一給自己休息的理由。
Advertisement
夏倚照沒有言語,拂開腰間的佩劍,轉過子面對書案將上面的畫卷拿了起來。
知道宋寒時畫技不俗,他生喜靜,從小的時候便習慣一個人待在書房中,一待就是一整天,誰都喊不出去。
紙上文墨的事他最是擅長,這幅畫在夏倚照的眼中看來就是栩栩如生,大師水平。
勾了一下角,卻是帶著諷刺的弧度,“有什麼需要改的地方?”
宋寒時已然走到后,聽到這般問輕笑一聲,想從后抱著,“自然是需要修改一些細節的地方,你離開十年,也有了些變化。”
他的手才放在腰間,夏倚照便徑直躲開他,側將手中的畫卷扔了回去,“是麼?”
男人落了個空,倒也沒有惱,角依然噙著一抹笑意,只是有些無奈,“阿照。”
他哄小孩一般的語氣聽得夏倚照心中莫名嫌惡,閉了閉眼,冷呵一聲,“興許你畫的人是春兒,所以才跟我有些差異,不必修改什麼,因為你畫的本來就是。”
話畢,指了指那張畫卷的背景。
即便只是個背景,也看出來那個涼亭是在離開這里的那十年重新修建的,畫面中的那個與酷似的人只能是春兒,不是。
宋寒時的臉終于有了變化,似乎想辯駁,最后卻無話可說。
他眼中的緒明明滅滅,最終都歸于平靜,只剩下最為濃稠的黑,“你到底還要生氣多久?”
“我不是在生氣,我們之間結束了。”
夏倚照深吸一口氣,“給我圣旨,我要出宮。”
宋寒時沒辦法聽說這麼絕的話,他跪過了、解釋過了、他只需要再等他一次。
最后一次。
“不可能。”他冷聲拒絕了,忽而扣住了的手腕,“你別想離開我的視線。”
Advertisement
夏倚照用力甩開他,“宋寒時!你不要欺人太甚!”
眼中被制了千百回的怒火又被他輕易挑起,“我知道你作為帝王三宮六院很正常,但是你從前在父親面前立過誓言只會有我一個人,如今你背信棄義,我不曾與你計較,只想要帶著阿回躲一個清靜也不可以嗎?”
“我沒有別人。”宋寒時幾乎是下意識口而出,越發用力握了的手腕,“那日與你說的話是真的,我從未過春兒。”
夏倚照眼中閃過一驚詫,隨即蹙了眉頭,“你什麼意思?”
宋寒時上前一步,略帶薄繭的指腹在細膩的手背上輕輕挲,緩聲道:“阿照,我跟之間……什麼都沒有。”
書房只有他們兩人,靜謐得有些過分。
冬季似乎很快就要過去,窗外的皚皚白雪快要融化,屋檐上的雨水一點一滴往下掉,間或落在地上,有的似乎只能看到在空中的弧線,永遠聽不到落地的聲音。
夏倚照定定地看著面前的男人,清澈淺淡的眼眸翻涌著晦的緒。
的眉頭微微蹙起,一煙青便服顯得材拔秀麗,發尾高高豎起,不同于那些冗雜服飾的清爽干練,是一貫喜歡的裝束。
只猶豫了一會,便用力出自己的手,“可懷孕了。”
宋寒時沉默片刻后,又重復了一遍,“我沒過。”
,濃稠的鮮染紅了裾。
春兒臉慘白地看著自己上斑駁的跡,又有些震驚地著面前的宋回,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反應,“你……我的孩子……”
宋回啞然后退一步,雙手輕,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我沒有推你、我沒有……”
他的確是想在臨走前給一個教訓,讓他母親那般傷心難過,他咽不下那口氣!
Advertisement
即便是在蕭國時,他們需要提防小心,可夏倚照還是教會了他一個道理:那便是有債必償。
春兒分明就是說了謊,既然宋寒時不愿意為夏倚照討回公道,那麼便由他來!
但是他真的沒想過讓小產……他從未想過要推。
宋回不知道該如何,他頭一次遇見這樣的場面,他記得自己并未推過,只是看著春兒倒在泊中的模樣,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
他甚至都有一瞬間的恍惚,不記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出手推了。
他害怕了……
宋回呆呆看著自己的雙手,春兒往上爬了幾步,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下意識地去扶,自己的雙手也沾滿了鮮,“你……”
他有些張,說不出話來,皮子哆哆嗦嗦,“你沒事吧?”
耳旁忽而傳來一陣遒勁的風,宋回還未回過神,就聽到后帶著一慍怒的聲音,“宋回,你在做什麼!”
他甫一回頭,便看到匆匆而來的宋寒時、以及他后的夏倚照。
——他們方才在書房聽到這個消息便匆匆趕了過來,醫已經在路上,只是看著春兒下那一攤濃稠的,似乎……
夏倚照閉了閉眼睛,心中無比雜。
方才宋寒時告訴他從未過春兒,可他似乎又言又止,還有些話不肯告訴,轉眼便發生了這樣的事。
看到宋寒時那般焦急的模樣,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去相信他的話。
若春兒肚中孩兒不是他的,他何至于這般張?
況且,若真如宋寒時所說,難道他一個帝王,會允許一個春兒私通,還這般寶貝地放在邊?
只一瞬間的腦海中轉過無數個想法,在看到宋寒時完全忽略了一手鮮的宋回,只大步走到春兒前將抱懷中時輕聲細語地哄著時,所有的想法都不重要了。
Advertisement
閉上眼睛下心中的思緒,快步走到宋回邊蹲了下來,“阿回,你傷了嗎?”
宋回呆呆地搖了搖頭,雙手污有些目驚心。
夏倚照見他沒有傷,這才松了口氣,“……發生何事?”
一雙眼睛看著他,似乎不允許他有任何的謊言,宋回眼睫都在輕,子也在抖,只搖了搖頭。
他看了宋寒時一眼,見他只張地看著懷中的人,越發害怕地握了拳頭,對著夏倚照又搖了搖頭,“對不起母親……”
“我……我……”
宋回倔強著不讓眼淚掉下來,眼眶通紅,淚水在打轉,“對不起……”
宋回的事鬧得沸沸揚揚。
誰都知道那個剛歸國的小太子將貴妃娘娘推得差點小產,如今大人孩子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此事引起軒然輿論,按理說后宮事務跟前朝沒什麼關系,只是此事事關到他們的儲君,宋回畢竟年,行事略有沖與魯莽,那日與貴妃之間的沖突被宮人們描繪得繪聲繪,無非就是——
貴妃娘娘如何忍大度,不愿爭執;太子殿下如何咄咄人,不依不饒。
朝中那些人本就忌憚夏倚照,是皇后,后宮中本就沒什麼人,唯一的子嗣所出,手中還握有兵權,這幾年陸續都有聲音強諫宋寒時充盈后宮開枝散葉,好不容易有了一個春兒,也好不容易肚子有了靜,卻落得這樣一個下場。
如今關于太子殿下橫向霸道、皇后娘娘狠毒善妒的流言甚囂塵上,那些大臣們也以“故意害死皇嗣”希宋寒時嚴懲宋回。
其中以丞相周之余的意見最甚:“太子殿下目空無人,橫向霸道,雖年紀尚,卻依然可看出德行有虧,不足以擔當儲君之位。”
此言一出,便獲得了不人的附和。
“丞相大人所言極是……”
“故意謀害皇嗣實乃罪大惡極,太子殿下年紀輕輕就如此不法祖德,不遵訓誡,恣行乖戾,日后恐災禍……”
“……”
宋回聽著那些對他明嘲暗諷的話,幾乎將他打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殘忍殺害自己手足的魔鬼,臉一片慘白。
只是他依然直了脊背,即便子都在輕,也握著拳頭并未怯場。
宋寒時居于龍椅之上,目沉沉向宋回,眸中似有千萬種思緒閃,眸漆黑,讓人看不清楚他真實的想法。
所有人都在等著他的回答,只有夏倚照不了宋回被審視的場面,忽而起至大堂之上,在天子面前跪了下來,“皇上,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懲罰,末將愿意代他過。”
用“末將”自稱,一時之間全場嘩然。
宋寒時瞳孔猛地放大,握在龍椅上的手緩緩收,手背上浮現青筋,幾乎用了極大的自制力才抑住自己的緒。
“皇后,慎言。”
夏倚照抬頭看向他,無比倔強,“皇上,以末將上的戰功、這些年為大宋的付出,可否抵去阿回所犯下的罪過?”
寥寥幾句話,已經表明了的立場。
跟宋回不會占著這個位置,除去的夏家軍之外,可以什麼都不要。
后那些大臣開始竊竊私語,宋寒時陡然沉了臉,“阿照,不要胡鬧。”
他看向一旁的人,“把皇后帶下去。”
話音落下,夏倚照已經手握上了腰間的佩劍,“皇上三思!末將這些年為大宋殫竭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末將只求阿回安然無恙!”
丞相卻上前一步道:“皇后娘娘是太子生母,不該如此溺教養,為皇子品德人格何其重要?皇后娘娘只求太子殿下安穩,殊不知是害了太子殿下!”
話畢,他又直直看向夏倚照道:“且功過不能相抵,即便可以,又豈能用皇后娘娘的功,去抵太子殿下的過?”
“他不過才十歲,你讓他何去立功!”
周之余一聲哼笑,“皇上最近為收復鹿城的事頭疼不已,若是太子殿下能解決此事,為大宋解除一大心患,功過相抵又有何不可?”
他明知這是不可能完的任務,鹿城已被魯國強占那麼多年,就連宋寒時都束手無策,又怎可能讓宋回一個不過十歲的孩解決?
他分明就是在挑釁!
夏倚照被他激起了熊熊的斗志,風眸淬著火焰,“本將若是讓阿回將那城邦收了回來,你該當如何?”
周之余輕蔑地指了指頭頂的烏紗帽,還未來得及言語,便聽到掌印太監忽而鳴鞭三響,隨即高聲道:“蕭國使者到!”
殿中頃刻間恢復寂靜,似乎都才記起來有這麼一件事。
自從十年前夏倚照去了蕭國說是建實則做人質換來蕭國的幫助之后,兩國一直維持著表面上的友好往來。
蕭國使者過了金水橋,又至道等候,之后等到掌印太監一聲高呼,這才緩緩殿,行禮。
使者一行三人,皆是容貌上乘,尤其最左邊一個男子尤為突出,只微微一瞥便人心中驚艷,難以忘懷。
他們恭敬上前,呈上他們帶來的見面禮。
往年都是一些珍奇異寶,今年卻是一紙文書,慶忠公公上前接過,當面清點,在看到上面的容時一時怔住了——
“如何?”宋寒時看向他,眉頭微蹙,下意識看向使者最左那人,見夏倚照也一瞬不瞬看著那人,似乎看直了眼睛,心中微沉。
慶忠公公吐了一口氣,看了看皇帝,又看了看丞相,才緩緩道:“回、回皇上,蕭國送了一座城池給太子殿下。”
“……”
“……正是鹿城。”
他話音落下,整個大殿寂靜無聲。
周之余更是白了一張臉,似乎還未回過神來。
片刻之后,又聽他們使者其一道:“鹿城是宋國邊關要塞,離蕭國甚遠,故而獻給太子殿下作為禮的一點心意。”
一旁的宋回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氣,“蕭兄這也……”
太闊綽了。
他忍不住去看旁的夏倚照,卻見自己母后一直著某個方向出神,也順著的視線看了過去,在看到那最左側的使者時登時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地張大——
那不是……?
男人似乎意識到幾道強烈的視線,朝他看了過來,對他微微勾了勾角。
隨即又恢復了面無表的模樣,跟龍椅上的宋寒時對上視線。
猜你喜歡
-
完結1709 章

攝政冷王悄醫妃
特工軍醫穿越為相府嫡女,受父親與庶母迫害,嫁與攝政王,憑著一身的醫術,她在鬥爭中遊刃有餘,誅太子,救梁王,除瘟疫,從一個畏畏縮縮的相府小姐蛻變成可以與他並肩 ...
255.2萬字8.18 63160 -
完結449 章

郡主囂張:誤惹腹黑世子
一場精心謀劃的空難,顧曦穿越成了安平公主府里人人欺賤的癡傻嫡女。親娘早死,渣爹色迷心竅,與妾室母女狼狽為奸,企圖謀奪公主府的一切。前世的顧清惜,以為裝瘋賣傻,隱忍退讓便能茍活,卻仍被姨娘,庶妹奸計毒害。今生,顧曦決心將忍字訣丟一邊!專注斗姨…
120.8萬字8.09 87940 -
完結691 章

公府貴媳
晏長風嫁給病秧子裴二少,是奔著滅他全家去的。后來,她眼睜睜看著這病秧子幫她滅了全家,又一手將她捧成了天下第一皇商。……晏長風的大姐莫名其妙的瘋了,瘋言瘋語地說著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她說爹爹將死,母親殉情,家產被姨娘霸占,而她們姐妹倆會被趕出家門。她說她未來的世子夫君是個渣,搶奪嫁妝,寵妾殺妻,連親骨肉也不放過。晏長風難以置信,卻也做足了準備。后來證明,爹爹確實身處險境,姨娘確實狼子野心,她為了不讓后面的悲劇發生,代替姐姐嫁入國公府。然后,她嫁給了國公府最不起眼的一個病秧子。當她要大開殺戒時,那病...
110.4萬字8 25343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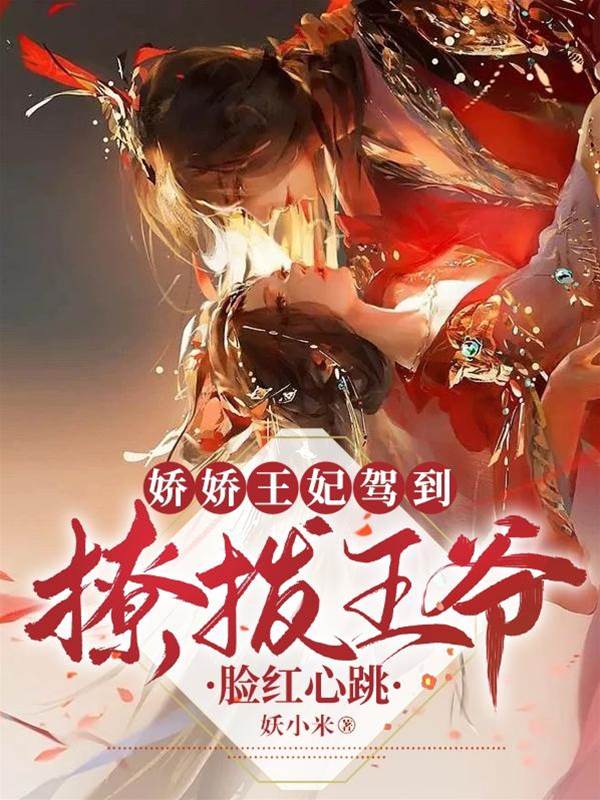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236 章
選秀當天被爆孕吐,冤種王爺喜當爹
【女強+萌寶+醫妃+偽綠帽】 一朝穿越,神醫沈木綰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四小姐,第一天就被人「吃干抹凈! 被狗咬了一口就罷了,竟然在選妃當場害喜! 還沒進宮就給皇帝戴綠帽?! 沈木綰:完了! 芭比Q了! 瑾北王表示莫慌:我,大冤種。 人在家中坐,綠帽天上來。 御賜綠帽,眾人皆諷。 催眠術,神醫術,沈木綰生了娃打腫他們的碧蓮! 不要臉的瑾北王每天拿著鋪蓋送上門:「媳婦兒,孩子生下來吧,我跟他姓」
42.6萬字7.93 138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