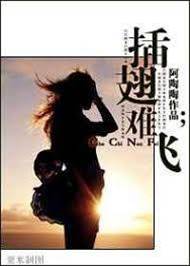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寵壞》 第18章
氣氛正逐漸變得迤邐甜,沈夏時忽然一陣小腹酸痛,下涌出一暖熱的。
僵住。
算算日子,生理期也就這兩天了。
沐則在上,手掌正要往下探去,沈夏時慌忙抓住他的手,因為尷尬和害,聲音不同往日那般冷靜:“不要!”
沐則清醒了幾分,以為真的害怕,輕拍著背脊安:“我不你,你別怕。”
“我…”沈夏時僵的從他懷里起:“你快出去。”
沐則蹙了蹙眉:“怎麼了?”
“你…你快出去!”因為說話說得急,下腹又涌出一,沈夏時臉上燒紅。縱然如這般沒臉沒皮的人,也不可能神無常的告訴沐則,我跟你親熱的時候來了大姨媽。
而且沒有帶衛生巾,流如柱,頗有滔滔不絕之勢,只能祈禱這個浴室放著孩子的私人用品。
沐則見神窘迫,蹙著眉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試探問道:“是不是生氣我親你?”
“…不是。”
“那是氣我了你?”
沈夏時咬牙:“這個以后再算賬…總之你先出去!”
沐則反倒不說話了,沉默的盯著看了半天,視線掃過渾上下,沈夏時慢慢后退,把屁湊在墻上擋著。
他起,語氣難掩失落:“好吧。”
臨走前,沈夏時囑咐他:“麻煩你幫我一下姜昕,就說我找有急事。”
沐則淡淡點頭,他出去后沈夏時才松了一口氣,間又涌出暖熱來,無奈的閉了閉眼睛,站進浴缸里把臟掉的子下來。
白皙的雙上流下幾滴鮮,一紅一白對比鮮明,沈夏時上半穿著寬大的襯,長度剛好遮住私的地方,艷紅的柱流向小,如果忽略地上那條沾上的子,現在的風景實在有些詭異的。
Advertisement
浴室的門突然被人打開,沐則的聲音傳來:“夏夏,你…”
沈夏時“……”
沐則:“……”
他剛走沒多久,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本想回來問問沈夏時是不是不舒服,走的時候忘記鎖門,也沒想到沈夏時在里頭服。
于是,沐則有些呆怔的看著沈夏時的下半,沈夏時臉赤紅的瞪著突然出現的人。
好在長久以來培養的冷靜和事不驚讓沈夏時沒有破口大罵,僵的蹲下坐在浴缸里,下半被遮住,兩只手搭在浴缸邊緣看著沐則。
他的耳尖浮起一抹可疑的紅暈,上前兩步又趕停下來:“夏…夏夏,你流了。”
“……”
我謝謝你告訴我!
沈夏時勉強扯出一笑:“你去幫我姜昕,快出去吧。”
沐則轉要出去,見坐在浴缸里,又回過頭從柜子里拿過幾片浴巾放在手能夠到的地方:“浴缸里冰,用浴巾裹著。”
他路過客廳時兄弟們正在吃早飯,姜昕和楊謹也在其中,沐則讓姜昕去浴室后,拿上車鑰匙準備出門,臨走前囑咐大家:“二樓的浴室不準進去,玩鬧的聲音小一些。”
說完頭也不回的出去,步伐還有些急。
二四給兄弟們丟去一個眼神:“哎,你們有沒有發覺頭兒臉有些紅?”
“你可拉倒吧!頭兒還會臉紅?”
二四下,他不可能看錯啊。
沐則開車到商場后徑直朝專區而去,跟著導購的引導,他站在一片衛生巾區域,看著種類多樣的衛生巾…一言不發。
導購阿姨笑笑:“給朋友買?”
“嗯。”
淡淡應了一聲,沐則怕沈夏時等太久,并不想與旁人過多寒暄,但是他是個大男人,對衛生巾這東西并沒有什麼研究,也不知道沈夏時平日習慣用什麼,又擔心買回去不喜歡。
Advertisement
躊躇了一會兒,沐則挑貴的指了指:“這個,這個,這個,還有這個,都給我包起來。”
導購阿姨蹙起眉:“買這麼多,留著過年呢?”
“……”
沐則涼涼的看一眼,導購阿姨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忙把沐則看中的衛生巾包起來遞給他。
足足兩個購口袋的衛生巾,沐則所到之都吸引了路人的側目,他形高大修長,英的臉上面無表,把購袋放在結賬柜臺后懶洋洋的側靠在柜臺上。
收銀員小姑娘盯著他看了幾眼,怯怯問道:“先生,有積分卡嗎?”
沐則有些不耐煩,兩手指夾著黑卡扔過去:“刷卡,快點。”
后排隊的人竊竊私語,一邊往沐則側臉瞟去,一邊捂笑,沐則掀起長睫看去,一雙黑沉的眼眸,眼底化不開的冰涼,目放在幾人臉上淡淡一瞥,那幾人臉紅的低下頭。
后傳來收銀員怯生生的聲音:“先生,好了。”
沐則接過卡正要離開,那姑娘小心翼翼的看他一眼:“先生可以辦一張積分卡,打折很劃算,可以…可以…”
越說越小聲,怯弱的模樣像只小白兔,別人興許會憐香惜玉,可遇上沐則,他不辣手摧了花都算好的。
男人沒心思再耽擱下去,兩條長快速的朝停車的方向走去,一路走過去的時候他忍不住想起沈夏時,從認識到現在,他見識過的聰明,膽識,嫵,當然也有耍和冰冷無。
這樣的人擺在面前,其他的就顯得索然無味了。
沐則打開車門,后突然傳來杯子砸碎在地的聲音,這條街一向熱鬧,平時打架鬧事的也多,倒沒有吸引沐則的主意,可等他坐上車后,對方又破口大罵起來:“沈夏時那個臭娘們兒!老子遲早辦了!”
Advertisement
丁乘舟輸了司心很不好,作為青云律師事務所的常勝將軍,與沈夏時這一戰簡直讓他面掃地,他心里氣不過,約著三兩好友出門買醉。
幾個人喝得酒氣沖天,走起路竄來倒去,從酒吧出來時手里還提著酒,慕璨禹作為丁乘舟的好友也在這一行列,他已經聽丁乘舟罵了一下午的沈夏時。
起初還會幫沈夏時說幾句話,后來聽得多了,丁乘舟也本不聽勸,他也就懶得管了,跟著眾人喝了許多的酒,醉得糊里糊涂。
幾個西裝革履的大男人在大街上耍酒瘋,狼狽的幾乎站不穩,丁乘舟扶著墻冷笑:“沈夏時那個賤…”
話沒說完,肩膀被一突然的力道擰過去,丁乘舟還沒有看清是誰,肚子上就挨了狠狠一拳,扎扎實實的疼痛,胃部一陣劇烈的痙攣讓他彎著腰捂著肚子干嘔起來。
下一秒,他的臉被一記拳頭打得撞在了墻上,喝醉酒的人像一攤爛泥,順著墻就倒了下去,沐則走過去一下一下的猛踹。
其余人后知后覺的拎起酒瓶:“你…你是誰!”
結果被人家瞥一眼后,哆嗦著打了個寒,慫里慫氣的把酒瓶子砸過去,沐則抬踢飛,輕而易舉把這幾個人放倒后,徑直朝慕璨禹走去,沐則沒忘記這個人至今都還惦記著他的人。
慕璨禹愣愣的看著近過來的人:“你…你是誰?”
沐則歪過頭,角斜挑起一抹冷冷的笑意:“沈夏時是我的人,以后離遠點兒。”
提起沈夏時,慕璨禹也說不清心里是什麼覺,起初當然是喜歡的,為了追求,他也做過不努力。可是沈夏時全都視若無睹,不僅把他的真心按在地上,還十分不待見他,時間長了,慕璨禹也分不清自己對究竟是喜歡還是固執。
Advertisement
可是現在,他在沐則眼里看到強烈的占有和保護,男人的自尊心讓慕璨禹不甘心認輸,他回了一句:“我認為,我們應該公平競爭。”
“公平競爭?”沐則嗤笑,戴著皮手套的手吊兒郎當的抬起,朝他勾了一勾:“就按你說的,公平競爭。”
平時的慕璨禹行事謹慎,是絕對不會逞一時之氣的,但今天喝多了酒,正所謂酒壯慫人膽,他兩只胳膊抬起,手掌握拳,打架的架勢倒是足的很。
冬日里冷風吹得人神抖擻,慕璨禹一鼓作氣沖過去,沐則惡劣的勾起角,一記左勾拳毫不留的揮過去,慕璨禹干脆利落的躺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沐則看著地上的人:“這麼不經打?”
對手太過弱小。
他覺有些無趣。
心里記掛著沈夏時的,沐則也沒有停留太久,恨恨的踹了一腳慕璨禹后迅速開車離開。
路過一家甜品店,他想討沈夏時歡心,于是又進去買了個蛋糕拎著出來。
別墅里安靜,兄弟們記者沐則的吩咐,絕對不敢吵到沈夏時休息,只是瞧著老大風風火火的從外頭進來,手里還拎著倆購袋和蛋糕,他們雖然已經有些習慣沐則的變化,但看他這副模樣,還是忍不住讓人嘆,使人盲目!
眾多目追隨沐則上了樓,見他急急忙忙的朝沈夏時的房間里走去,二四嘿嘿一笑:“你們猜,咱頭兒多久能拿下沈夏時?”
“老子猜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太久了,我猜就今晚。”
二四看向兄弟幾個:“敢堵嗎?”
“賭就賭,你他媽以為老子怕你?”兄弟們興致的掏出了隨的銀行卡在桌上。
樓下熱絡的說著話,沈夏時的房間倒是十分安靜,門窗關的不風,整個人在被子里,被子的邊角出一些細碎的亮。
沐則關上門,走過去掀開被子,沈夏時卷在被窩里看電影,懷里抱著個暖手袋,小臉揚起看他一眼后又別開目:“你去哪里了?”
“怕你著急用,去給你買這個。”沐則拿出衛生巾遞給,沈夏時略有些不自在:“謝謝你,姜昕帶著一些,可以應急。”
“你不喜歡?”他蹙起了眉頭,手里拿著一包衛生巾,臉深沉的審視著它。
沈夏時尷尬的將他手中的購袋接過來抱進懷里,點點頭:“我很喜歡,謝謝你。”
瞧著這副窘迫還拼命裝大不了的模樣,沐則覺得有趣,上半靠過去,手指輕輕的臉:“吃飯了嗎?”
“吃了。”沈夏時模樣很乖。
沐則心的一塌糊涂,把人摟進了懷里:“家里好幾個廚子,喜歡吃什麼就讓他們給你做,平時不會打擾你。”
沈夏時沉默了一陣,然后說:“我想回家。”
“就住這兒,把這兒當你家。”
下聲音同他商量:“縱然你喜歡我,但是我們還沒有往,我住在你也不是事兒,你說是吧。”
沐則盯著沒說話,沈夏時繼續說:“再說我家里還有我好多上班要用的資料,在你這兒不方便。”
“我明天就給你搬過來。”
“我不。”
沈夏時的態度也強起來:“我想回家住。”
空氣凝結了一刻,沈夏時毫不肯讓步,沐則拿過剛買的蛋糕遞到面前:“吃嗎?”
沈夏時險些繃不住,這男人還會轉移話題。
別過臉去,沐則低聲哄著:“你再住幾天,過兩天我送你回去,行不行?”
高燒剛退,部長念在勝了一個大案子,給了三天的休息時間,本打算在家睡大覺,現在看是不可能了。
沈夏時也知道這是沐則最大的讓步,也不再犟著,接過沐則手里的蛋糕輕輕一笑:“好吧。”
沐則問:“你這麼想回去,是因為那間公寓是你母親留給你的吧?”
先是一怔,繼而撇撇:“還有什麼瞞得住你沐大爺呢。”
那個家的確是母親留的。
沈夏時說得隨意,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太習慣用這副模樣來掩飾自己的心,但是沐則一眼就可以看,他忽然很不喜歡這樣。
人活在這世上開心就笑,難過就哭其實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沈夏時反其道而行,不管是開心還是難過,笑得那一個無所謂。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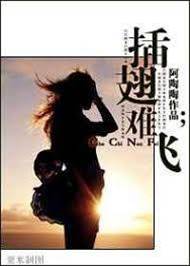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658 章

名門寵婚之老公太放肆
他和她的關係可以這樣來形容,她之於他,是他最愛做的事。 而他之於她,是她最不愛做的事。 ……安城有兩樣鎮城之寶,御家的勢,連家的富。 名門權貴聯姻,艷羨多少世人。 連憶晨從沒想過,有天她會跟安城第一美男攀上關係。 「為什麼是我?」 她知道,他可以選擇的對象很多。 男人想了想,瀲灧唇角勾起的笑迷人,「第一眼看到你就想睡,第二眼就想一起生兒子」 她誤以為,他總會有一句真話。 ……一夕巨變,她痛失所有。 曾經許諾天長地久的男人,留給她的,只有轟動全城的滅頂醜聞。 她身上藏匿的那個秘密,牽連到幾大家族。 當她在另一個男人手心裏綻放,完美逆襲贏回傲視所有的資本。 ……如果所有的相遇都是別後重逢,那麼他能對她做的,只有不還手,不放手! 他說:「她就是我心尖上那塊肉,若是有人動了她,那我也活不了」 什麼是愛?他能給她的愛,有好的也有壞的,卻都是全部完整的他。
106.3萬字8 71276 -
完結235 章

追妻漫漫行長的心尖寵
【京城大佬 美女畫家】【雙潔】【追妻火葬場】 陸洛晚如凝脂般的肌膚,五官精致絕倫,眉如彎月,細長而濃密,微微上挑的眼角帶著幾分嫵媚,一雙眼眸猶如清澈的秋水,深邃而靈動。 但這樣的美人卻是陸家不為人知的養女,在她的大學畢業後,陸父經常帶著她參加各種商業聚會。 …… 在一年後的一次生日派對上,原本沒有交集的兩人,被硬生生地捆綁在了一起,三年漫長的婚姻生活中一點一點地消磨點了陸洛晚滿腔的熱情,深知他不愛她,甚至厭惡她,逐漸心灰意冷。 一係列的變故中,隨著陸父的去世,陸洛晚毫不猶豫地拿出離婚協議,離了婚……從此遠離了京城,遠離沈以謙。 後來,命運的齒輪讓他們再次相遇,隻不過陸洛晚早已心如止水。 而沈以謙看著她身邊層出不窮的追求者,則不淡定了,瞬間紅了眼。 在某日喝的酩酊爛醉的沈以謙,將她按在懷中,祈求著說:“晚晚,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 都說沈以謙風光霽月,聖潔不可高攀。 在兩人獨處時陸洛晚才發現,他要多壞有多壞,要多瘋就有多瘋。 他道德高尚,也斯文敗類。他是沈以謙,更是裙下臣
46萬字8 15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