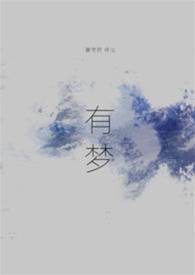《別給她鏡頭》 2.你乖一點
站了大半天屬實累人,哪怕好好泡過澡,小的酸脹猶在。
錢難賺,屎難吃。
孟槐煙吹著頭髮深刻領悟了這句話。
吹頭髮喜歡全乾,發量長度又都不,因而總在這上頭花不時間。等吹風機的嗚嗚聲終於慢慢悠悠停下來,門鈴聲才有機會傳到耳邊,也不知響了多久。
孟槐煙將睡攏些過去,沒先急著開門。
湊近,貓眼裡影影綽綽映出個廓。
比預想的來得快了些。
孟槐煙最後一困意也散了,心頗好地倒了杯紅酒,倚在沙發上悠哉聽門外靜。
響半分鍾一次,不疾不徐,耐極好。
約莫有了十來聲,孟槐煙似是滿意了,扯松了領口往門口去。
江戍將門鈴按到第二十一次,才從閉的門裡出來,從一條線慢慢暈一片暖黃的亮。
主人像是對任何人都沒什麼戒心似的,真的睡隻堪堪掛在上,垂很好,於是頂出兩曖昧的凸點,前的出一大片,暗曲線綿延著沒領裡。
可整個人被薄薄的一層水氣籠著,平添了幾分和。
江戍掃了一眼,緒算不得多好。
他不說話,孟槐煙也不說話,一時間靜默得厲害。
到底夜深了,樓道裡的冷風破開略顯沉悶的空氣,鑽了空子灌進來。
江戍抬腳向前邁一小步,子順勢調了個位,說了今天見以來的第一句話:
“你要我來,我在這裡了。”
孟槐煙任由他犯進自己的安全距離,畢竟他這麼一擋著實暖和了些,明知故問道:“我什麼時候要你來了?”
江戍也不辯,從容拿出手機播放那條簡短的語音。
Advertisement
——“有什麼話,自己來跟我說。”
見孟槐煙沒反應,再放一遍。
眼見他手指要落下到第三遍,孟槐煙急急抓住他的手臂。
當眾聽自己的語音是什麼尷尬的刑罰?
江戍垂眸,視線鎖住那隻抓著自己的手,孟槐煙立時像了什麼燙手山芋一樣松開。
“有什麼話,進來說吧。”說完便沒有要搭理他的意思,轉進去了。
登堂室的覺尤其好,江戍背手將夏夜裡的悶和涼意一齊關在門外,視線卻隨著孟槐煙一路走著,懶懶倚沙發裡,爾後同著酒杯的那兩瓣一道,裹一口甘醇的紅酒。
江戍斂神,低頭換了雙居家的男士拖鞋,線更深幾分。
孟槐煙不聲把一切瞧在眼裡,心明朗。
“坐吧。”
江戍在腳那頭的單人沙發落座,眼見換了個更愜意的姿勢。
是,這主人放肆極了,有客人在也隻圖自己爽快,了鞋著腳屈在沙發上,右手撐著腦袋,左手拿著酒杯,領向一側落去,松松垮垮,幾乎要出整隻白的。
偏偏那半明半昧的玉正對著江戍。
孟槐煙恍若未覺,極優雅地小口啜飲,可左手一抬,服的左下擺也跟著向上,了泰半,線也開始若若現,分不清是裡頭沒穿還是穿了什麼特別款式。
早該知道這是場鴻門宴。
孟槐煙勾了個痛快,大發慈悲給江戍拋出話頭:“是什麼話,值得江導半夜跑來我這裡?”
“該提醒的,工作人員已經提過了,”江戍子前傾,手肘支在膝上,“你要我當面說,也還是那些話。”
Advertisement
孟槐煙挑眉:“我記不好,忘得差不多了,江導再說一遍?”
江戍有求必應:“合同的條例,孟小姐好好遵守,希收錄製時,孟小姐依舊站在臺上。”
像是聽到什麼好笑的事,孟槐煙的笑意漾開在角,酒杯裡的深紅不安分地波起來,前綿的那團也跟著生生幾下。
“知道。知道。”孟槐煙笑說。
江戍並不在意的不屑,亦不願意把話強調得再明白些:不要同臺上異多流,不要吸引他們注意,對他們笑。
說多了總顯得自己在意。
孟槐煙見他不再開口,又想著他多說一些:“還有別的話嗎,江導。”
江戍沉沉看,看服穿得不規不矩,躺著的姿態也不規不矩。微啟,說些什麼,可轉念自己又算是什麼人,便什麼教好好穿裳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就這樣,孟小姐好好休息。”
沒坐下兩分鍾,江戍起。
孟槐煙那點說不上來真假的笑去了,凝著那道疏朗的背影時隔多年又離自己遠去。
“等等。”
江戍停了,沒回頭。
他聽到酒杯與茶幾的,人的理與皮質沙發的挲,相比之下那點腳步聲就顯得溫和極了,像是沒一點危險,離自己愈來愈近。
角忽地被人拉扯住,接著一綿的熱度挨著手臂傳上來。
而後他聽見說。
“欸,你還沒負責。”
江戍轉過來,作幅度很小,沒把的手甩開,只是作間手臂似是挨到了什麼的一小顆。
江戍低頭,眸深沉:“負責什麼?”
孟槐煙神很是無辜,松開手,食指微垂,指指自己的。
Advertisement
“錄你的節目好累,站了那麼久,到現在都酸得厲害。”
江戍視線隨手指的方向下移,那雙白玉一樣的足就這麼直接踏在地板上,大約有些涼,小巧的趾頭微微瑟著。
下一秒孟槐煙就被打橫抱起來,驚出一聲輕呼。江戍闊步將放回沙發上,視線相接,兩人皆是一頓。
他們在不足兩厘米的距離裡換鼻息,氣氛突然變得熱且曖昧。
江戍手掌下一是膩的彎,一是飽滿的側。
他恨得厲害,得厲害。當下手裡不自覺加了力氣。
孟槐煙“唔”一聲,並不覺得疼,反倒希他再用力些,好喂飽自己這些日子裡的綺念。
江戍在進一步失態的邊緣收回手,於旁坐下,默不作聲撈起的兩條擱在自己上,掌心覆上去,竟是給孟槐煙按起來。
這手帶著灼人的熱度,得孟槐煙隨他作浮浮沉沉。
江戍找準了位,摁下去的一瞬響起孟槐煙的痛呼。
“疼……你輕一點呀……”
這雙,到這個人,乃至講話時的語調,尾音,都著一子溫。
江戍聽到這話,是想再用力些,出更多討饒的話的,只是一瞧那可憐樣,心就了,心一,手下的作也不覺和緩下來。
孟槐煙舒舒服服地接服侍,開始心猿意馬。
江戍給按了一會兒,就察覺到某人不安分的作。
一點一點往裡挪,每挪一步就靠近他腹部一分。江戍默然,便得寸進尺,磨磨蹭蹭終於挨到他的下腹,小肚約到一,孟槐煙一愣。
這下是真得意暢快地笑起來。
Advertisement
明明是始作俑者,卻還故作天真問道:“江導,這的,是什麼啊?”
江戍手上作隻停了一瞬,便繼續按,渾若什麼也沒聽見。
孟槐煙見他不理,也不惱,用極磨人的速度緩緩屈起左,將腳心搭在那。
江戍被迫中斷了這場荒唐的所謂“負責”,被拉更為荒唐的無邊風月裡。
人是多的生,尤其孟槐煙這樣的人,江戍早便領教過。
此時此刻,被弱無骨的足隔著綿綿纏纏裹住,全被膩人的視線封膠。
江戍是半點彈不得了。
“你乖一點。”
一開口,嗓音啞得不像話。
孟槐煙極他陷裡的聲音,得教人耳熱。
索坐起來,手支好,微一抬,借著輕巧的角度稍往前移,便正巧落他的懷抱裡。
從一見到他,淨想著抱他。
孟槐煙勾著江戍的脖子,拿鼻尖去蹭他的。
“我乖怎樣,不乖,又怎樣?”
——
加更一章,人節快樂。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老婆寫真
王斌無意中從別人那裡看到了自己老婆裸露的照片,本想回家興師問罪,可老婆蘇欣怡三言兩語就將事情打發了過去……
63.4萬字7.62 80167 -
完結230 章
金鱗豈是池中物
薛諾還在盡心盡力的服侍著男人,雖然侯龍濤的肉棒不是巨大無比,但對于一個十六歲少女的櫻桃小口來說,還是過于粗長了,她最多只能含入一半多一點。每一次圓大的龜頭頂到她喉頭的粘膜,跪在地上的小美人都有要嘔吐的感覺,但她還是堅持繼續咗著硬挺的雞巴,一出一進的半根肉棒上涂滿了女孩的唾液,在車燈的照耀下,閃著淫猥的光芒。多余的口水還來不及吞下,就被陰莖撞了出來,流的她一身都是。
127.1萬字6.92 249813 -
完結101 章
歡喜債
夜色瀰漫,客棧裡一片沉寂,走廊兩側客房中,飄出來的男人鼾聲,輕重不一。 唐歡悄無聲息往前走,如夜行的貓,最後停在走廊盡頭那間客房前。 黃昏在大堂裡見到的那個男人,就住在裡面。 那人有一雙清冷的眼,進店後直奔櫃檯,問房付錢,而後朝樓梯走去,並未看周圍一眼。他穿著淺灰色的長衫,腳步不輕不重,每次落在黃木梯板上,皆發出相同的聲音。兩側衫擺隨著他的動作錯開,露出裡面修長雙腿,交替擡起。白色中褲套進黑靴,簡單幹練,有種說不出來的味道。他上了樓,她目光不由往上移,卻只瞧見他側臉,尚未細品,他一個眼神掃過來,冷寂如冰。唐歡心動了,她想要這個男人。師父說,女人初夜多少都有點意義,還是找個看上眼的人破了吧。唐歡舔了舔嘴脣,沒想到一下山就遇到個絕品。 食指指腹從舌尖掃過,輕輕貼在窗紙上,等那處溼了,細細竹管插-進去,沒有半點聲響。 太冷的男人都不好對付,還是用點手段吧。 半刻鐘後,唐歡撥開門,悄悄閃了進去,直奔牀頭。 窗子開著,皎潔的月光斜灑進來,因男人沒有放下牀幃,他平躺的身影一覽無餘。 唐歡歪坐在一旁,滿意地打量這個男人,看著看著,她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白皙清俊的臉。連睡覺的樣子都是冷的,身上會不會熱一些? 可就在她指尖距離男人俊臉不過幾寸距離時,男人眉心微動,唐歡暗道不妙,正要閃身退開,眼前寒冽清光閃過,脖下一涼,待她反應過來,便是一道無法言喻的劇痛。她捂住脖子。溫熱的血如杯中滿溢的茶水,從她指縫滲出。
50.1萬字8 29001 -
完結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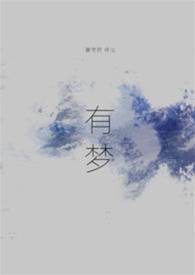
有夢
作品簡介: 她總說他偏執。 是了,他真的很偏執,所以他不會放開她的。 無論是夢裡,還是夢外。 * 1v1 餘皎x鐘霈 超級超級普通的女生x偏執狂社會精英 練筆,短篇:) 【HE】 其他作品:無
5.9萬字8 55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