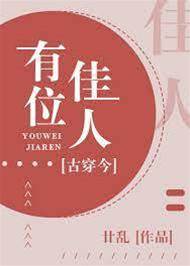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朕懷了前世叛將的崽》 101
不好!
悚然一驚, 幾乎是立時沖了過去,一腳踹開房門, 便看見了廂房相擁的兩個人。
李元憫眸一, 放開了眼前之人。
倪英重重息著,看了看這個, 又看了看那個, 眉頭蹙起, 最終將目落在了猊烈臉上,然而猊烈沒有什麼表,只如往常那般一概淡淡的。
倪英咬了咬牙,正拔劍, 李元憫冷聲喝道:“阿英!”
他頓了頓, 雪白的耳廓上微微發紅。
“我讓他來的。”
倪英明顯不信,護衛還昏睡外頭,若是自請他進來, 又何須放倒他們。
可看著他們二人方才相擁的模樣, 不似勉強, 倪英心間又突突突地跳起來, 不敢細想,生怕自己無端的揣測再度落空,白歡喜一場。
只能可憐又無措地站在那里。
李元憫嘆了一口氣,上前幾步, 將手上的劍推回劍鞘中,聲道:“回去收拾收拾,準備出發了。”
倪英看著他,似乎想從他的臉上找到什麼,然而那張臉上只有那給予的憐惜與溫,別無其他。
的阿兄站在他后,看著他們。
倪英咽了咽口水,一點兒也不敢打破眼前這個夢境。
***
啟程的第二日,因著晨起的一場暴雨,大隊人馬耽擱了不行程,在落日之前無法按著既定的路線趕到兗縣,猊烈干脆下令就地扎營。
因著子有狀況,李元憫一向深居簡出,如今有倪英代為安排駐扎事宜,他干脆懶待在歇憩的營帳翻閱些風土志。
Advertisement
夕西斜,外頭細碎的腳步聲來來往往,有著一令人發懶的氣息。
李元憫神倦怠地又翻了一頁,腦海無端端閃過一雙凌厲的眼睛,他指尖僵直著,又將書給闔上了,淡淡嘆了口氣。
他不知道此次他會否玩火自焚,不過再難,他也得迎頭而上——他沒有旁的選擇了,無論是試圖挽回他的阿烈,還是拉攏這位悍將,增加自己保的籌碼,他都只能著頭皮主出手。
正沉思著,外頭隨行進來了:“殿下,總制大人請見。”
李元憫呼吸微微一滯,半晌,道:“傳。”
很快,維帳一掀,帶了一陣風進來,高大健碩的男人大步流星而進,他已經卸了鎧甲,只一玄黑的勁裝。
他垂首看著眼前的人半晌。
“吃了沒?”
李元憫隨口道吃了。
猊烈沉默半晌,繞過了案臺,曲起指腹著他的臉頰:“你不該說謊。”
李元憫呼吸一滯:“你監視我?”
“當然,”猊烈分毫沒有想瞞的意思,“可惜你近之人個個忠誠,斷不能收買,也不進去人,打聽個小事可得費好大的功夫。”
“你——”
李元憫呼吸微,心念轉了轉,回想起他這幾日的狀,合該不知他妊子的事。
當下稍稍放松了臉,解釋道:“只路途顛簸,一時半會兒沒有胃口而已。”
話音未落,外頭又是一聲通報,“殿下,錢叔送藥來了。”
李元憫不聲:“拿進來吧。”
錢叔踽踽進來,看見總制大人,愣了一下,不過沒有說什麼,只朝著他稽首一拜,默默將適口的藥放在案上,李元憫讓他自行去了。
Advertisement
他只作平常的模樣,三兩口便喝了,這藥著實苦極,他習慣的拿了碟子里的飴糖,速速往里放了一顆。
驀地心念一,抬眸看了一眼眼前的男人,對方正盯著他看,邊含著一若有似無的笑意。
李元憫將目移開,輕咬著里的飴糖。
營帳靜默下來。
猊烈輕咳了一聲:“整日,沒得拖累了子,自要日日喝這苦口補藥,走,帶你外頭走走。”
聽得那補藥二字,李元憫一愣,他何其聰慧,隨即明白了來,心下更是松了口氣。
“來人!”猊烈自顧自朝帳門喚了一聲,門口的侍衛匆匆進來候命。
“給殿下備馬。”
侍衛遲疑片刻,看了看李元憫,見他沒有阻止的意思,當即命下去了。
猊烈走了幾步,回過頭來:“不走?”
李元憫深深吸了一口氣,跟上前去。
***
夕掛在天際,余暉照得四都攏上了一層金的暈。雖是初春,但今日日頭甚大,四自是暖洋洋的。
二人騎著馬一前一后出了營,李元憫在前,猊烈在后。行至一條溪邊,猊烈翻下馬,上前將李元憫從馬背上抱了下來。
李元憫抬頭看了他一眼,從他懷里跳了下來,沿著溪畔走去。
二人依舊是一前一后,夕將他們的影拉得長長的,溪水波粼粼,碎了蜿蜒的一條金,水聲清幽,平著躁的人心。
看著前方纖細高挑的背影,猊烈的心難得的平靜,卻又覺得幾分不足,思忖片刻,不由分說快步上前牽住了他的手。
Advertisement
李元憫不自覺掙了掙,卻是被拽著。
不由抬眸挑釁似得看他:“你如今是大皇子的人,不怕他發覺你跟我走得太近麼?”
猊烈停下腳步,看了他半晌,道:“你裝得那樣好,他怎會再忌憚你?”
“何況,”他結了,目中幽深:“你也是李元乾默許的,給我投誠的一個‘大禮’。”
李元憫的呼吸頓時重了幾分,屈辱沒有再盛,只強自了下去,沒有說話。
耳旁一聲嘆氣,隨之,李元憫被攬進了一個厚實寬大的懷里,低沉的聲音過廓傳他耳中,“告訴你,只是想讓你知曉,這天下,能隨心支配自己的,只有權,懂了麼?”
李元憫閉了閉眼睛,重重地咽下了頭的艱。
猊烈著他的雪白盈潤的耳垂,聲音不自覺低了下來,帶了些安:“別怕,至他是送給了我。”
李元憫沒有說什麼,只在看不見的地方,握了拳頭。
日頭漸漸下山了,四隴上了一喑啞的晦來。
草叢里窸窸窣窣一陣聲音,猊烈利目一瞇,足尖挑起一塊石子來,驟然往來聲飛去。
但聽得短促的一聲吱,猊烈上前,在草叢中撿起一只野兔來。
他瞟了一眼李元憫,拔出皮靴上的一支短匕首,當下便拎著那野兔去了溪水邊,宰殺剝皮清洗完,拎著回來了。
李元憫襟本就有些煩嘔,看著那剝了皮的禿禿滴著水的野兔,胃腑更是起了一陣翻騰,他暗自了。
猊烈卻是興致的,拾了些枯枝架了個篝火堆,用匕首削了支細竹將野兔穿了,架在火堆上烤。
Advertisement
他抬眸見到李元憫微微皺眉的模樣,難得的打趣:“這小畜生知道你沒用晚膳,便上趕著來了。”
李元憫怕他看出什麼異常,緩步過去,在他邊坐了下來。
不到一會兒的功夫,那野兔被烤得滋滋作響,猊烈練地割去焦裂的部分,切了一塊遞到李元憫邊。
李元憫聞著那油脂的味道,胃臟又開始翻騰起來。
猊烈見他為難的樣子,嗤笑一笑,“看你這氣樣兒,在軍中怕是挨不到一個月,若是遇上戰急,遑說烤著,生都得咽下去。”
李元憫沒有理會他,只暗自按捺住那強烈的作嘔之意。
猊烈將那往里一丟,嚼了嚼,睨了他一眼:“這還不算,你道韃靼這些蠻子戰俘什麼?‘兩腳羊’!”
李元憫再也忍不住,扭過頭在一側干嘔起來。
猊烈怎會想到他反應這般大,一時暗悔與他說這些。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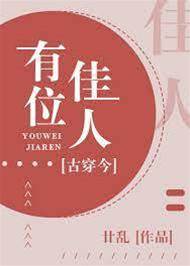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
完結115 章

出獄之后我懷了渣男的種
三年前,一場大火,兩個人。枕邊人和心頭肉,靳東陽毫不猶豫選擇把枕邊人沈念送進了監獄。沈念在獄中一天天的挨日子,日日夜夜,生不如死。半個月後,沈念莫名其妙的大出血。命都丟了一半。三年後,沈念出獄。沈念勢不再做枕邊人,一心逃離靳東陽。可偏偏踏在雲頂之上的人,卻揪著他不肯放手。出獄前的一場交易,讓沈念肚子裡意外揣了個種。靳東陽得意的笑:是我的種,你得跟我。沈念悶悶的想:有種怎麼了?老子自己養。 斯文敗類豬蹄攻x誓死不做枕邊人受。
29.6萬字8.18 116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