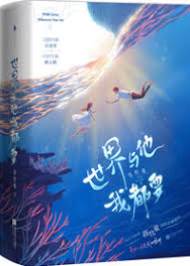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他站在時光深處》 第74章 他站在時光深處73
應如約回到家時, 溫景然還沒到。
應老爺子坐在遮雨的花架下, 正在修六角琉璃宮燈。朱紅的木漆工箱散在腳邊, 工堆碼在箱盒上,零零散散。
老爺子膝蓋上蓋著薄毯, 鼻梁上那副老花鏡,鏡框有些偏斜, 就這麼掛在鼻梁上, 一副隨時會掉下來的樣子。
應如約收起傘, 隨手擱在花架上, 蹲下替老爺子把就快拖地的薄毯往上拉了拉,攏住他的膝蓋:“爺爺。”
應老爺子專心地用鑷子搗鼓著琉璃宮燈的木架, 鏡片后那雙眼睛飛快地看了一眼:“一切順利?”
沒有任何鋪墊的一句話, 應如約卻聽得明白,點點頭,眉眼,角都漾著笑意:“一切順利, 不過外婆現在還在觀察期, 沒有徹底離危險。”
“老人家底子差, 傷筋骨輒百天,何況是開刀。手順利就好,后面好好養著。”老爺子替換了鑷子, 用十字螺旋刀把螺撬回去,注意力又回到了琉璃宮燈上:“回頭好好謝謝溫景然,他這段時間可不比你輕松。”
應如約有些不自然。
一個星期前那晚, 緒失控,雖及時拉回理智掛斷了電話,可說出去的話就猶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
還是頭一次,在應老爺子面前如此緒外。
事后,自然是無盡的尷尬。
每每看到應老爺子板正嚴肅的臉,都不敢回想那天發生的事,甚至心虛到不敢和應老爺子對視,總覺得……尷尬,尷尬死了。
好在這幾天因為外婆的事,不用天天回家,尚還有那麼一息息的時間,能夠避開應老爺子的詢問。
只不過……
如約一想起老爺子剛才發給的那條短信,一時有些不準老人家的態度。
Advertisement
這是打算替斬斷?
這個問題一直到溫景然出現,也沒有答案。
溫景然似乎本不知道晚上有相親這件事,從進屋到坐下吃飯,表現得都很自然。
這樣同桌而坐的場景和以往任何一次都沒有什麼不同,從醫院,病例聊到時政,應如約基本上沒有的機會。
吃過飯,夜已深。
屋外雨勢仍舊沒有停歇,淅淅瀝瀝地連續下個不停。
如約幫華姨把碗筷收拾進廚房,剛切了水果端進客廳,就見一束車燈從半敞開的窗戶里進來,投在雪白的墻壁上。
轎車的引擎聲清晰,就停在了院子里。
應如約的呼吸一,端著玻璃果盤的手一頓,下意識地看向正和老爺子談論國外局勢的溫景然。
察覺到的視線,溫景然側目看了一眼,有些奇怪今晚的心不在焉。
應老爺子已經起迎了出去,隔著門,約能聽到長輩互相寒暄的聲音。
沉默地移開視線,放下果盤后,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去廚房冰箱里拿了一瓶飲料,匆匆上樓。
溫景然蹙起眉心,有些費解。
應老爺子已經把人帶了進來,和他差不多年紀的知好友正樂融融地跟在他的旁,他們的后,是個和溫景然差不多年紀的瘦高男人,鼻梁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一正裝,幾分儒雅幾分銳意。
今晚相親的是應老爺子好友的孫子,以及前同事的孫,兩戶家庭相的橋梁維系在應老爺子一人上,商定后就決定把地點定在應老爺子家里,以便幾人也能湊趣聚聚。
而溫景然,只是恰好被應老爺子來吃頓晚飯而已。
這種場面,溫景然并不陌生,在應老爺子提及對方家庭孩的工作況后,頓時了然。
Advertisement
有些人,怕是誤會什麼了。
他想著,忽然有些想笑。
此時回想起來,當時下意識看自己的眼神里有戒備有警惕,只是這些緒全部源于一個并不存在的假想“敵”。
院子里再次響起轎車由遠及近的引擎聲時,應如約有些納悶。
赤腳蹲坐在沙發上,趴在窗口往下。
深藍的轎車里下來一個心打扮過的孩,撐著傘,隨一起前來的老先生走進屋里。
應如約眼看著那把在燈下格外深的墨藍雨傘消失在遮雨棚里,郁悶得整顆心不上不下的憋悶。
再也裝不了淡定,在房間里轉了幾圈,開了門,躡手躡腳地走到樓梯口,準備聽墻角。
不料,剛扶著樓梯扶手坐在臺階上,低頭一,視野里,本該在客廳言笑晏晏相親的人卻出現在了樓梯的拐角,正把的目盡數納進那雙眼睛里。
應如約一怔,隨即便是鋪天蓋地的窘。
慌忙站起,也不管是否已經暴了意圖,近乎丟盔棄甲地想要逃跑。
沒等走出幾步,溫景然住:“我想在老師的書房里找本書。”
應如約的腳步一頓,等他說下去。
“一本原籍的外科基礎理論,你幫我一起找吧。”
其實那本書,正躺在他的書桌上。
臨時想留住,溫景然唯一能想到的,只有這個借口。
應如約轉看著他,他還站在幾層樓梯下,影被夜披上了一層朦朧,那雙眼漾著笑意,清晰又明朗。
有那麼一瞬,應如約覺得,的什麼小心思都被他看了。
推開書房的門,應如約索著開了燈。
應老爺子的書架很大,實木的大書架連一片,占了整面墻。
書架上的書全是老爺子自己打理擺放的,也不知道據什麼標準分的類,原文書能夠和字典排在一起,散文可以和資料堆在一起。
Advertisement
從書架第一排,慢慢搜尋著,眼花繚。滿目都是醫書,有也曾翻過看過的,但大多數,連名字也沒有聽過。
那些書,是老爺子近年來淘來的。
卸去醫生的責任后,他平時看的書漸漸就從資料類的醫書變了各類古籍小說,有打發時間用的,也有用來欣賞的,收藏的。
應如約從柜子里出一本《基礎理論》,捧著書脊翻了幾頁,轉問他:“是這本嗎?”
溫景然倚著書桌,就站在后。
轉轉得突然,他來不及退讓,毫無預兆的,就把接了個滿懷。
左手還舉著那本厚重的《基礎理論》,鼻尖到了他的呢外套,微微有些。站在那,滿腦子都是嗡嗡聲。
直到手中的書被他走,應如約才反應過來,后退了兩步,后背抵著書架,也不敢直視他,著仍舊有些發的鼻尖,低聲道:“我以為是你要相親。”
溫景然沒作聲,抬起看的眼睛里有笑意一閃而過,沒等應如約看清,他又低下頭,手指落在目錄上,筆直下。
不過須臾,書頁在他指間快速地翻了幾頁。
應如約站在他面前,一時有些無措。
這種無措,是手腳都不知道該擺在哪里的覺。
是這麼站著,讓覺得格外不自在。
總會下意識地回想起離蒼山那日凌晨,他們將就在車后座等天明等日出;會想起初聽到外婆確診胃癌,在L市的那個夜晚,給他發的分手短信;更多的是今天,手結束后,他倚著墻,眼底的疲倦清晰可見,那雙冰涼的手握著,自嘲地說“有些張,怕你哭”。
這些對于而言,每一幀都是很寶貴的記憶。
Advertisement
他此時站在這,不是在樓下客廳和垂直的距離,懷抱著結婚的目的在相看一個完全陌生的孩,已然有一種松了口氣的念頭。
這麼想著,終于漸漸放松,輕吁了一口氣,問他:“喝茶嗎?”
溫景然的目流連在書頁上,搖搖頭:“不喝了,怕等會又睡不著。”
他的睡眠質量不太好,長期以來的壞習慣,不止生鐘有點混,就連睡有時候都有些困難。
晚上若非有事,他通常都會盡量避免喝茶,咖啡等一切會提神的飲品。
“那水果?”
……
“就什麼都不需要?”
這一次,溫景然終于有了反應。
他隨手合上書,手臂越過的耳畔,把書塞回書架里。
他的袖袖口過的耳畔,像剛才那樣的,耳廓有些,應如約忍不住想躲開,剛往邊上挪了一步,就被他用手按住肩膀。
溫景然一手扶在書架上,一手按著的肩膀,背著,低垂眉眼。目對視間,他余瞥見迅速紅起的耳廓,漸漸的,連帶著整個耳朵都紅了,在燈下顯得面若細瓷,說不出的白凈。
“以為我要相親的后面呢?”溫景然松開按住肩膀的手,手指沿著的手臂落下去,扶在的腰上。
覺到渾一,他低下頭,目和平視,故作不悅道:“把我拱手相讓,你眼不見為凈?”
他此時算賬,讓應如約接了個措手不及。
不是翻篇了,再討論需要什麼嘛……怎麼就折回去說相親的事了?
抿著,視線從他的眼睛落到他的鼻梁,再至他的,最后,重新對上他的視線,搖搖頭:“我剛才打算去聽。”
溫景然挑眉,有些意外竟選擇直白地回答他。
“我想我還會故意下樓,干擾你,給你搗。”應如約深呼吸了一口氣,張得面都有些發紅,但仍舊屏著一口氣,繼續道:“除非你對方很滿意,很喜歡……”否則,真的會做這些看上去就很沒有教養的事。
溫景然發覺,應如約有些地方不一樣了。
起碼,在對待他們之間的問題時,漸漸變得坦率。
這些以前本不敢這麼直白說出口的話,此時看來表達得毫無障礙。
本想看窘迫害的人,反被這樣的舉將了一軍,忍不住勾起角,似笑非笑地盯住,問:“以什麼份,嗯?”
他的問題無賴又惡劣,幾乎是在為難。
應如約抿著,不躲不避地和他對視良久,反問:“胡攪蠻纏,蠻不講理的前友?”
這回,溫景然是真的笑了。
他看著。
結微滾:“可我一點也不想做通達理藕斷連的前男友。”
猜你喜歡
-
完結199 章

惹不起的趙律師
遭遇家暴,我從手術室裡出來,拿到了他給的名片。 從此,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 “記住,你是有律師的人。”
51.2萬字8 27138 -
完結548 章

沈先生大腿我抱定了
在小說的莽荒時代,她,喬家的大小姐,重生了。 上一世掩蓋鋒芒,不求進取,只想戀愛腦的她死於非命,未婚夫和她的好閨蜜攪合在了一起,遠在國外的爸媽給自己填了個弟弟她都一點兒不知情。 一場車禍,她,帶著腹中不知父親的孩子一同喪命,一切就像命中註定...... 對此,重生後的喬寶兒表示,這一世,她誰也不會相信! 左手一個銀鐲綠毛龜坐擁空間,右手......沈先生的大腿湊過來,喬寶兒傲氣叉腰,她就是不想抱,怎麼破? ......
99.3萬字8 28232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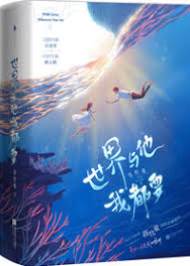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7880 -
完結566 章

滿級熱戀:傅少嗜妻如命
【甜虐 偏執霸寵 追妻火葬場】“傅延聿,現在隻能救一個,你選誰?”懸崖之上,她和季晚晚被綁匪掛在崖邊。而她丈夫傅延聿,華城最尊貴的男人沒有絲毫猶豫:“放了晚晚。”聞姝笑了,她一顆棋子,如何能抵過他的白月光。笑著笑著,她決然躍入冰冷的大海……後來,沒人敢在傅延聿麵前再提“亡妻”……某日,傅延聿不顧場合將一女子堵在角落,如困獸般壓抑的看她:“阿姝,你回來了。”女人冷笑著推開:“傅少,你妻子早死了。”傅延聿隻是紅了眼,死死的拽住她……
98.2萬字8.18 43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