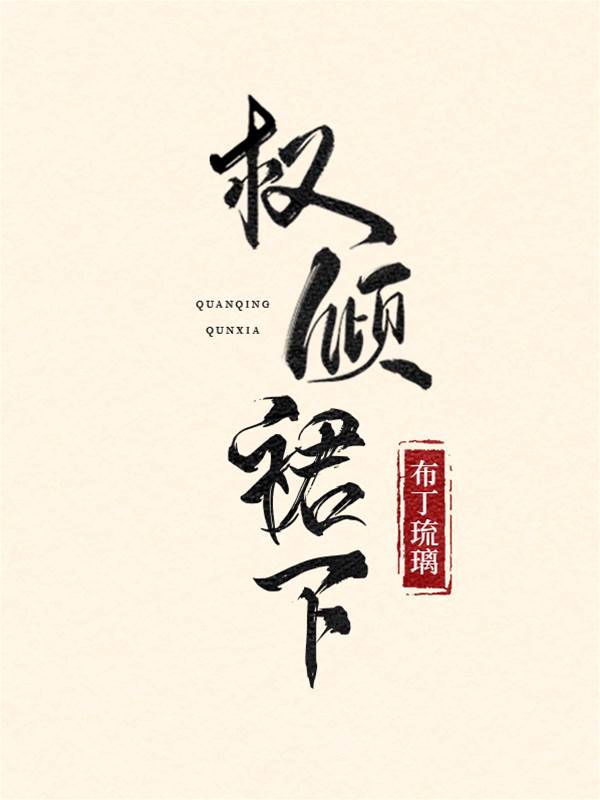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重生后成了權臣掌中珠》 第66章 逃生
魏鸞出城前, 特地去了趟敬國公府, 請伯父魏峻點派十幾位強力健的護院武師,隨去城外接魏嶠夫婦。
這些武師雖然比不上章家豢養的死士,卻也有不弱的功夫在。章家既用這等私手段誆騙,定是不愿鬧出太大的靜,天化日下,武師們足以護送魏嶠夫婦回城。只消進了城, 敬國公府有護院, 周遭更有兵馬司巡查, 便容不得章家肆意擄人。
魏鸞點好人手,孤乘車出城。
染冬則與盧珣一道暗中跟著, 并未現。
為保無虞, 還從曲園調了兩名護衛。
到得鎮國公府別苑附近, 魏鸞命車夫在道旁停車,暫未靠得太近,只命人拿了的手書去呈給鎮國公夫人。守門的護衛應是得了吩咐,先前攔著敬國公府的人不讓進,聽說是曲園來的,竟順利放行。
沒過多久, 遞信的護院武師便回來了。
“章夫人答應了信里的條件,說馬上讓人套車恭送,請夫人按約定行事。”武師雖不知,瞧見這架勢,豪的臉上盡是擔憂。
魏鸞頷首, 為免跟魏嶠夫婦撞見后節外生枝,吩咐道:“待會見著他們,只說是伯父派你們來接,不必提我。馬車用咱們的,路上當心。”而后便命車夫催馬前行,在別苑外一之地停穩,掀起側簾張。
等了好半天,朱漆大門吱呀推開。
先是數位男仆走向的馬車,恭敬守在兩側,旋即門扇大敞,刻著敬國公府徽記的馬車駛出來,魏嶠夫婦隨帶的仆婦侍亦跟在后面。那武師快步上前,朝車說了幾句話,果然見車簾掀起,魏嶠先探出來。
他穿的是家中常服,想必是被聽聞噩耗的魏夫人匆匆拽走,未及換裳。
Advertisement
此刻神沉穆,雙眉鎖,神頭還算不錯。
隨后出來的魏夫人就凄慘得多。
短短兩日間,比先前消瘦了太多,隔那麼遠都能瞧得出憔悴。
被魏嶠扶著下車時,子晃了晃,腳下虛浮無力。原就溫,未經世事磋磨,先前得知章皇后的歹毒居心時,雖心痛,人前卻還能撐著,只背流淚。此刻卻神恍惚,當著眾多侍從武師,走得跌跌撞撞,魂不守舍。
魏鸞遠遠瞧著,只覺鼻頭泛酸。
若當初章皇后的歹毒居心是鋒銳的匕首,狠狠扎在魏夫人的心上,如今外祖母的這場“病”,便是剔骨的尖刀,一寸寸地將剮得模糊淋漓。那是脈牽系的親生母親,這麼些年母慈孝,至深。
然而今時今日,仍為了章氏之利益,以探病之名,行之實。
毫不顧母間的。
易地而,若魏夫人做出這樣的事,魏鸞又豈能承?魏夫人明知章皇后之歹毒,得知噩耗后仍片刻不耽誤的趕過去探,為的是至親的,不敢猜疑耽擱。結果卻換來這樣的對待,其中傷心可想而知。
原來這就是章皇后所謂的“打斷骨頭連著筋”。
不過是欺負母親重,不像章氏刻薄寡義。多年和睦親,一朝利益相爭,面皮撕破后,拼的不止是誰強,還要看誰更無心狠。
魏鸞輕輕抬手,拭去眼角的潤。
那邊魏嶠似有所應,扶著魏夫人上車后,往這輛不起眼的青帷馬車瞧過來。
魏鸞忙落下側簾。
待敬國公府的車馬啟程,的馬車便被趕別苑。
……
對于章家的這座別苑,魏鸞并不陌生。
鎮國公是的堂舅,跟定國公府更是打虎的親兄弟,每嘗聚會游宴,兩府多是一起的。且先帝親封八位國公,魏章聯姻后,往來便愈發切。魏鸞往年踏青避暑,曾與母親來這做客過幾回,雖不算門路,大抵記得方位。
Advertisement
而今故地重游,是人非。
供外祖母養病的正屋屋脊已然不遠,魏鸞被章家的侍從引路圍隨,心里多是張的。
畢竟,今年才十六歲。
比起章家那些久經風浪的老狐貍,實在得很。
但再張,還是得從容應對。
仆婦掀起錦繡簾,一淡淡的藥味撲鼻中,魏鸞腳步微頓,在門外深吸了口夏日郊外清冽的氣息,而后抬步邁。繞過那座白玉打磨的致屏風,里面羅珠翠環繞,不出所料的,外祖母跟前坐著鎮國公夫人竇氏,定國公府的喬氏妯娌卻不在場。
魏鸞行禮拜見,先問外祖母病。
章太夫人倒是醒著的,見是來探問安,便牽住手輕輕握著,說許久沒見,小姑娘出落得愈發.漂亮,又說病時好時壞,不過是熬著云云。
魏鸞初聞病訊時的那點擔心,也在這虛假的寒暄中消磨殆盡。
過后挪開目,便見竇氏亦抬起眼皮看。
“嬸母向來子骨弱,這也是剛喝完藥才能撐著說幾句話,還是得睡會兒靜養。鸞鸞既瞧過了,先到偏房坐坐,等晚點嬸母醒了再來。”說著話,囑咐仆婦照顧好太夫人,而后緩緩起出門。
魏鸞亦跟出去。
到得偏房,竇氏屏退侍從,那雙眼睛黑沉沉的向魏鸞,“先前皇后娘娘說你聰慧,我還不信,如今看來,自打嫁進曲園,果真是靈了,也很有孝心。魏鸞——好歹也是公府出門,就這麼寒磣,沒帶個隨從?”
“夫人會讓染冬照顧我?”魏鸞抬眉。
撕破臉后,連聲舅母都不愿再。
竇氏聞言哂笑,盯著魏鸞的目也添了寒意,“念桐被廢掉太子妃的位子,圣旨雖未明言,卻也被栽了個云頂寺行刺的罪名。我后來查過,你邊不止染冬,還有曲園的護衛。盛煜手下的人都不是廢,豈會容你孤前來。”
Advertisement
魏鸞款款坐椅中,“家父家母也帶了侍從,夫人還不是說扣押就扣押。我便帶了人,難道還指從這別苑殺出去?總歸是我為私自投羅網,不該連累旁人,倒不如將他們留在曲園,還能幫我照料外子。”
“盛煜若需照料,我也不必費這份事了!”
竇氏冷聲說罷,起,將早就備好的紙筆丟過來。
魏鸞沒,只靜靜瞧。
竇氏羅貴重,發間金釵熠熠生輝,那張臉卻是冰寒的,微微俯道:“念桐的賬以后再跟你算,今晚你就待在這里給盛煜寫信。這信怎麼寫,不用我教吧?”
“寫了也沒用。外子不會因私廢公。”
“你寫就是!否則——”竇氏瞥了眼窗外,道:“我府上多的是宮里出來的嬤嬤。”
這些嬤嬤中,不乏通刑罰之人,過手的罪眷數不勝數,只消主子吩咐,便是宮里的妃嬪、獲罪的誥命都能下手,更別說魏鸞這種小姑娘。章家仗著太后和皇后照拂,行事向來跋扈肆意,這時節連抗旨犯上的事都能隨意做出來,真想審,輕而易舉。
魏鸞久在宮廷,清楚們的厲害。
若真嬤嬤沾了,怕是能生不如死。
不敢討苦頭吃,便放任恐懼蔓延,臉微變。
竇氏頗滿意地敲了敲桌案,“快寫!”
盛煜會不會因私廢公,可不是魏鸞說了算。先前竇氏進宮,曾聽章皇后提過,說盛煜此人恃寵而驕,為了魏鸞,連忤逆犯上、威脅中宮的事都做得出來。以玄鏡司統領的沉穩做派,能如此行事,自是新婚纏綿,極為看重貌瑰艷的魏鸞。
就像兩軍作戰時挾持家眷,至能擾軍心。
若盛煜憤怒之下拿著冷的脾氣上門算賬,更是中竇氏下懷。
Advertisement
坐在椅中,盯著魏鸞寫。
魏鸞則咬著筆頭,黛眉鎖,甚至額間滲出了細的汗。
其實不怕寫家書,畢竟臨走前特地叮囑過門房與管事,不必理會章家送來的任何東西,而章家又不到盛煜的行蹤,這封信絕不可能送到盛煜手里。但過于鎮定未免令對方起疑,年紀尚弱,為了至親孤犯險,此刻勇氣褪去,害怕才是對的。
遂咬抖筆,裝著竭力鎮定的姿態,廢了五六稿,才將家書寫好。
外頭已天昏暗,暮四合。
竇氏頗滿意地收好家書,又剪了段指甲封信中,命人轉告曲園,今晚只是指甲,明晨便是手指,明晚到手,若三日不至,便送項上人頭。章念桐既背了行刺的罪名,章家絕不怕將其坐實。
這些話竇氏是在窗下吩咐的,清晰傳屋。
自然是威脅魏鸞。
魏鸞亦聽進去了這些話,將初別苑時的淡然姿態換憂心忡忡。
是夜,魏鸞食不下咽,被鎖在偏房。
竇氏為出章念桐丟了太子妃之位的惡氣,也不肯讓魏鸞安生,命人拿鐵鏈將魏鸞雙腳鎖住,又取繩索反捆雙手,綁在床柱上。這待遇雖在預料之中,但麻繩捆住細弱手腕時,仍勒得魏鸞生疼。
也不敢多反抗,可憐地沉默坐著。
……
夜愈來愈深,周遭漸漸安靜。
魏鸞沒敢吃章家給的晚飯,腹中頗,不過在敵營神繃,倒沒覺得困。聽到外面響漸停,仆婦安排完上夜的人手,各自回房睡覺后,魏鸞終于松了口氣,被捆著在背后的手探向袖,出一片極細薄鋒利的刀片。
這是盧珣給的,拿極薄的銀編薄袋,藏在素白袖里,極不起眼。
這姿勢也在南朱閣練習了好多遍。
此刻屋里沒人,門口唯有上夜的仆婦,刀片將繩索割開大半,悄無聲息。
魏鸞緩了緩,只等四更時分才輕聲喚人。
這屋子離章太夫人養病的屋舍極近,周遭有護衛巡查,亦有侍值夜。只因此刻夜深人靜,且此是別苑的腹地,值夜的仆婦早已睡意昏沉。聽出聲,門口值夜的仆婦未敢擅,有位侍詢問緣故。
魏鸞認得那是竇氏的得力侍,名寶桔。
便蹙著眉頭,輕聲道:“寶桔姑娘,舅母是想讓我這樣坐上整晚嗎?”
“上子倔的人,都是這樣磨脾氣的。”
“那……”魏鸞渾難似的扭了扭子,道:“我若此刻就寫求救的書信,能稍稍松綁嗎?”見寶桔面遲疑,又嘆氣道:“不然整夜困頓,明天手僵著,寫信未免太慢。終歸是我選的路,沒必要自討苦吃。回頭若能和解,我必重謝姑娘。”
說話間面黯然。
寶桔在竇氏跟前頗有臉面,跟魏鸞不算陌生,知道在公府里養得氣,平生沒吃過這種苦頭。如今能熬半夜才開口服,已是出乎意料了。且魏鸞早點服寫信求救,于竇氏而言,自是有益無害。
生得健壯,對付兩三個養的姑娘不在話下,自不將魏鸞放在眼里。
稍加思索,便去準備紙筆。
魏鸞趁著這時機,割斷繩索后出細紙包著的藥,待寶桔上前幫解繩索時,瞅著鼻子便揚過去。這是玄鏡司制的,百多斤的壯漢都扛不住一小撮,魏鸞用了數倍的量,寶桔哪能抵抗得住?
在昏迷摔倒前,魏鸞忙手扶住,而后就勢讓躺在榻上。
開鎖的東西,盧珣也曾教過。
等閑牢獄的鎖都不在話下,別苑里這種糊弄眷的更是手到擒來。
只是魏鸞怕鐵索磕發出聲音,小心翼翼地挪著,等雙腳困,已是鼻尖冒汗。
慶幸的是份特殊,章家這手段又著實齷齪,竇氏不愿讓下人知道太多,臨走前曾吩咐仆婦值夜死守即可,屋里的事由的親信持。是以屋人仰馬翻,外間昏昏睡的仆婦也不曾察覺。
魏鸞迅速下外衫,跟寶桔換了裳,匆匆改換發髻。
又將寶桔捆在床柱,臉朝側。
上下檢看過,沒太大破綻后,拿了封空的書信,推門而出。
猜你喜歡
-
連載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6994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36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35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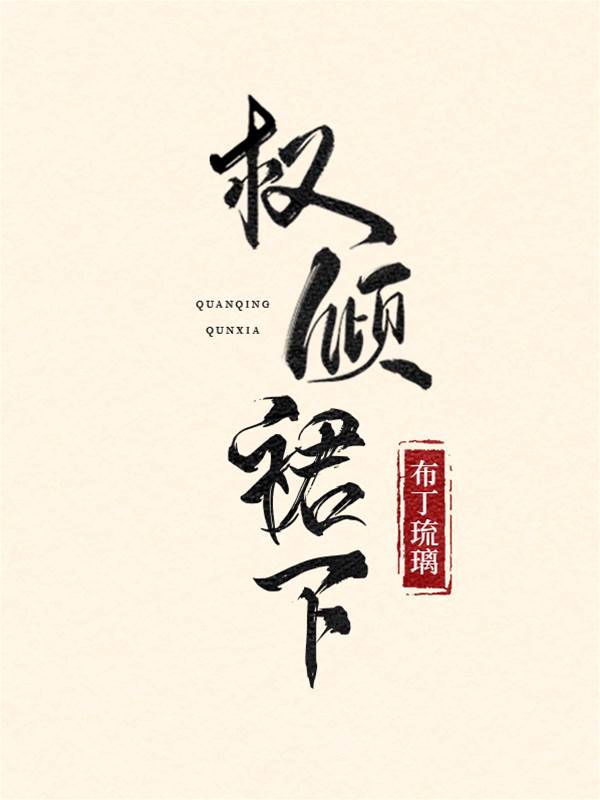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6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