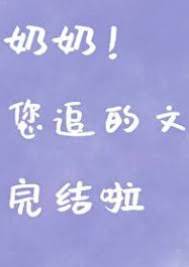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敗給喜歡》 第48章
書念盯著那行字幾秒,眼睛眨了眨,隨后抬眼看向謝如鶴。注意到他繃著的表,訥訥道:“我知道是假的呀。”
謝如鶴似乎有點難以啟齒:“我擔心你會信這一條。”
“……”雖然覺得不應該,但書念莫名想笑。
謝如鶴沒再多說:“我不打擾你了,回去吧。”
書念拉住他,問:“怎麼會突然上熱搜?”
不怎麼玩微博,不清楚他以前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此時擔心他是不是惹到了什麼人,會不會對他有影響。
對上張的眼,謝如鶴輕聲安:“就是一些營銷號,不用擔心。”
出了大樓,謝如鶴坐上方文承停在附近的車。他的心顯然很差,周帶著郁氣,連帶著關車門的聲音都大了不。
砰的一聲,嚇得方文承心臟直跳。
方文承咽了咽口水,著頭皮說:“爺,熱搜已經撤了。我找人查了,據說料給他們的是黎盛的經紀人。”
謝如鶴的眼皮了:“誰?”
方文承連忙解釋:“就是之前讓您改歌的那個……”
“啊。”謝如鶴拖著腔調,平靜道,“理由。”
“黎盛最近被料有私生子,一直在熱搜前三沒挪過位置。”方文承把手機遞給謝如鶴,給他看上面的容,“估計是想找人來轉移熱度。”
至于為什麼拿阿鶴來擋刀,大概是因為他的脾氣惹到了太多人。
方文承沒敢把這話說出來。
謝如鶴掃了眼,忽地把手機扔到旁邊。他輕笑了聲,漂亮的桃花眼不帶一溫度,一字一頓道:“還好玩。”
“……”方文承很識時務地保持沉默。
“哪來那麼多沒腦子的總來擋我的路。”謝如鶴懶洋洋地靠到椅背上,涼涼地說,“那就陪他玩。”
Advertisement
方文承大氣都不敢一口,思考著該如何回話。
還沒等他想到,謝如鶴已經閉上了眼。
“開車。”
一路開回萊茵河畔花園。
車是平常慣有的安靜,仿佛還夾帶著一僵。想到那個微博長文里,一筆帶過了自己的話,方文承總有種隨時就要被炒的覺。
為了緩解氣氛,方文承打開了廣播。
放的恰好是最近突然紅起來的網絡神曲。
謝如鶴皺眉,職業病犯起,暴躁地問:“這放的什麼垃圾。”
“……”方文承立刻關掉廣播。
把車子開到地下停車場,方文承跟著謝如鶴一起下了車。他主道:“爺,您有看評論嗎?大多數都是理智的,除了一些帶節奏的營銷號……”
謝如鶴沒說話。
兩人一起進了電梯。
方文承自顧自地說了一大堆話,字里行間的意味格外明顯,表面上是安,實際上是希他不要介意,也不要把他炒掉。
電梯在十六樓停下。
謝如鶴抬腳走了出去,沒有半點要回應他的意思。他用指紋開門,正想走進去的時候,忽然一頓,回頭看著跟在他后面的方文承。
方文承連忙道:“爺,怎麼了?”
謝如鶴重新垂眼,指了指門鎖:“把你的指紋刪掉。”
“……”
進度完得快,導演干脆讓書念把接下來的三集戲份錄完。等出棚的時候,這一天已經快要過去了。
天空暗了下來,像層黑布,染著濃霧。
書念從包里翻出手機,猶豫著要不要聯系謝如鶴。
還沒等考慮好,書念的目一抬,立刻注意到謝如鶴的影。此時他就站在電梯旁,沒做別的事,就安安靜靜地呆在那兒。
書念愣了下,連忙小跑了過去:“你來多久了呀。”
Advertisement
謝如鶴抬手捋了捋的頭發:“沒多久。”
書念小聲說:“我一般都這麼晚出棚的。”
謝如鶴嗯了聲,沒太在意:“外面冷,把手套戴上。”
“哦…哦,好。”
書念把手套拿出來,正想戴上的時候。
謝如鶴突然拿過的包,搭在手肘的位置。他接過手套,把的袖子向上捋了些,冰冷的指尖不經意地到的皮。
書念睜著圓眼,盯著他,沒了作。
他的眉眼清俊,細的睫像把小刷子,格外好看。線抿直,模樣專注而認真,慢條斯理地給套上手套,然后把的袖拉下來。
像個什麼都不會做的小朋友,書念乖乖地等他給自己戴好。
隨后,謝如鶴很自然地牽起的手,進了電梯。
兩人都不是話多的人。
在一起之前,一般也都是書念主找話題,說一下自己最近發生的事,又或者問一下他的近況。就是很正常的朋友之間的流。
但當關系更近一步的時候,反倒不知道該如何相了。
就是每天都想見他。
見到他的時候會覺得很開心,也會覺得張。
想跟他更靠近一點,卻拿不準那個分寸。
想起今天那個制片人跟說的話,書念干脆把這個當一個話題,問道:“你還記得《趁他還在》的制片人嗎?”
謝如鶴思索了下,點頭:“嗯。”
書念的聲音細細小小的,轉述著制片人的話:“他也是我今天錄的這個劇的制片人。然后他剛剛問我要不要轉臺前,說他最近在籌拍一個網劇,想找一些生一點的面孔。”
謝如鶴沒太驚訝,只是問:“你想去嗎?”
“沒有。”書念認真地說,“我不適合在鏡頭面前,會很張的。而且我只喜歡配音呀,希別人喜歡我都是因為我的聲音,就會很有就。”
Advertisement
看著明亮的眼,不知道為什麼,謝如鶴突然很想的腦袋。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過了一會兒,書念突然發現。
這樣說覺就是,如果去當演員,別人就會因為的臉喜歡一樣。書念怕他誤解了自己的話,細聲補充:“還有,我長得也沒那麼好看。”
娛樂圈里好看的人太多了。
書念也不想去獻丑。
聽到這話,謝如鶴停下了腳步,側過頭看。路燈散發著暖黃的,撒在他的上,在他的眼里折出細碎的,專注而溫。
桃花眼天生帶了點迷人的意味,此時像是在放電,細細地盯著。
書念被他盯得不太自在:“怎麼了?”
謝如鶴收回視線:“不用謙虛。”
書念一愣。
又走了一大段路。
書念被他牽著走,腦海里不斷重復著他剛剛說的那四個字,一時有些迷糊,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冒出這樣的話。
半晌,遲鈍的書念終于明白了他想表達的意思。
臉蛋在一瞬漲得通紅,幾乎要冒煙。
這樣青的互持續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書念才稍微適應了兩人之間份的轉換,以及偶爾會有的親舉。
覺得現在過得很快樂,特別快樂。
每天醒來之后,書念不需要再給自己做心理調節,不再需要去想,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有多的壞人在暗滋生。那些戰戰兢兢,似乎已經然無存。
書念只需要涂上自己喜歡的口紅號,換上好看的服。帶著對一天的期待,用力地推開門,去見門外那個想見的人。
睜眼之后見到的第一個人是他。
睡前見到的最后一個人也是他。
偶爾會給書念一種,回到了初中的時候,那段無憂無慮的時。
Advertisement
每天準時起床準時睡覺,做著父母老師代好的事。起床后,迅速地喝完母親遞給的牛,背上書包,快速地跑出去,笑嘻嘻地跟不知等了自己多久的謝如鶴道歉,然后嚴肅地問他做完作業沒有。
是多好的一段時。
連著一周的棚蟲生活,偶爾還要加班趕進度。把這段戲錄完之后,書念也沒了別的工作。
好幾天的假期,書念跟謝如鶴商量著要不要出去玩,但因為天冷,想的好幾個計劃都否決掉。
最后,謝如鶴只提議讓在家好好休息。
書念有點小失,但也沒多說什麼。
應了聲好,在床上百無聊賴地滾了幾圈,很快就抱著被子出到客廳,找了部喜劇片來看。因為心思總放在手機上,半部電影過去,書念也不知道講了什麼容。
但手機那頭的人卻沒再找。
書念悶悶地吐了口氣,忍不住蹬了蹬腳。
恰在此時,玄關的門鈴聲響起。
書念頓了下,莫名有了種猜測,是預極其強烈的猜測。拿起手機走到玄關,順著貓眼向外看。
能清晰地看到站在外面的人是謝如鶴。
書念立刻開了門。
謝如鶴今天穿得休閑簡便。拉到脖頸的黑風,寬松的運,看起來像個大學生。他進了門,把鞋子掉,問道:“怎麼不穿個外套。”
書念家的客廳沒有空調,雖然門窗閉,溫度依然很涼。
顯然沒想過他會過來,書念傻愣愣地指著沙發:“我剛剛在被子里。”
謝如鶴點頭,把外套下來裹在上:“給你帶了蛋糕。”
他先往沙發的方向走。
書念跟在他后面,像條小尾一樣。
坐到沙發上。
謝如鶴把袋子里的蛋糕拿出來,拆開,放了一塊在書念面前。
書念剛吃完午飯沒多久,此刻還吃不下,沒去。完全沒有克制自己高興的模樣,笑瞇瞇地,想去牽他的手。
謝如鶴幾乎是立刻避開。
書念沒反應過來。
謝如鶴剛在外面吹了風,手冷到僵。怕不開心,他低聲解釋:“我的手太冷了。”
“……”
他看向書念,耳有點燙,慢慢地補充了句:“一會兒再牽。”
書念沒聽他的話,依然湊過去握住他的手,兩只手都用上,想給他捂熱。
謝如鶴的表頓住,角忍不住勾了起來。
過了一會兒,謝如鶴還是怕會涼,恰好看到放在旁邊的熱水袋,他猶豫著說:“有熱水袋。”
書念看了過去,定了兩秒,又收回視線:“我的手也暖和的。”
謝如鶴說:“嗯?”
書念的聲音含糊不清,小小的強調:“應該比熱水袋暖和。”
聽到這話,謝如鶴看向,表若有所思。
不知道自己這是什麼病,就是想跟他親點接,但又怕他不喜歡。書念咽了咽口水,自以為很委婉:“你可以把我當熱水袋。”
“……”
客廳里安靜一瞬。
“這樣嗎。”像是忍不住,謝如鶴氣息悠長地笑了一聲,眼里閃著璀璨的,語速緩慢,刻意拉長了音,“好啊。”
書念默默地松了口氣。
下一刻,謝如鶴握住的手腕,往懷里扯。
書念毫無防備,整個人撲到他的膛前。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舉,半跪在沙發上,雙手撐著他的肩膀,慌慌張張地問:“怎、怎麼了?”
謝如鶴單手虛托著的背,微微垂下頭,與的視線撞上。他的聲音低而啞,漫不經心的,帶著笑意。
“我喜歡抱著熱水袋。”
猜你喜歡
-
完結633 章

天價暖婚:司少放肆寵
結婚前夕遭遇退婚,未婚夫不僅帶著女人上門耀武揚威還潑她一身咖啡。池心瑤剛想以眼還眼回去,卻被本市權貴大佬司少遞上一束玫瑰花。捧著花,池心瑤腦子一抽說:「司霆宇,你娶我吧。」「好。」婚後,池心瑤從未想過能從名義上的丈夫身上得來什麼,畢竟那是人稱「霸道無情不近女色」的司少啊!然而,現實——池心瑤搬床弄椅抵住房門,擋住門外的司姓大尾巴狼:是誰說司少不近女色的,騙子!大騙子!!
59.4萬字8 104591 -
完結490 章

嬌妻很大牌:秦先生,你被捕了
夏云蘇懷孕了,卻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她只知道自己的嬸嬸跟別人合謀,要將自己送到其他男人的床上。很快,夏云蘇流產了。她被冠以水性楊花的罵名,卻發現自己的未婚夫搞大了堂妹的肚子。所有人都在奚落她,包括她的母親。直到那個男人出現,用一紙合同逼她…
85.1萬字8 33006 -
完結88 章

般配關係
【先婚後愛 暗戀成真 豪門霸總 白月光 雙潔 HE】【嬌俏傲慢女律師X深情狠厲大老板】為了家族利益,許姿嫁給了自己最討厭的男人俞忌言。在她這位正義感爆棚的大律師眼裏,俞忌言就是一個不擇手段、冷血無情的生意人。何況她心中還藏著一個白月光。婚後俞忌言配合她的無性婚姻要求,兩人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直到許姿白月光回國,許姿開始瘋狂找俞忌言的外遇出軌的證據,想以此為由跟俞忌言離婚。得知俞忌言有個舊情人,許姿本以為勝券在握了,沒想到俞忌言竟將她壓到身下,承認:“是有一個,愛了很多年的人。”“你想要我和她親熱的證據是不是?”俞忌言輕笑,吻住她:“那好,我給你。”
20萬字8 24924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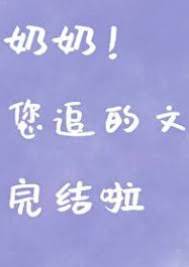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