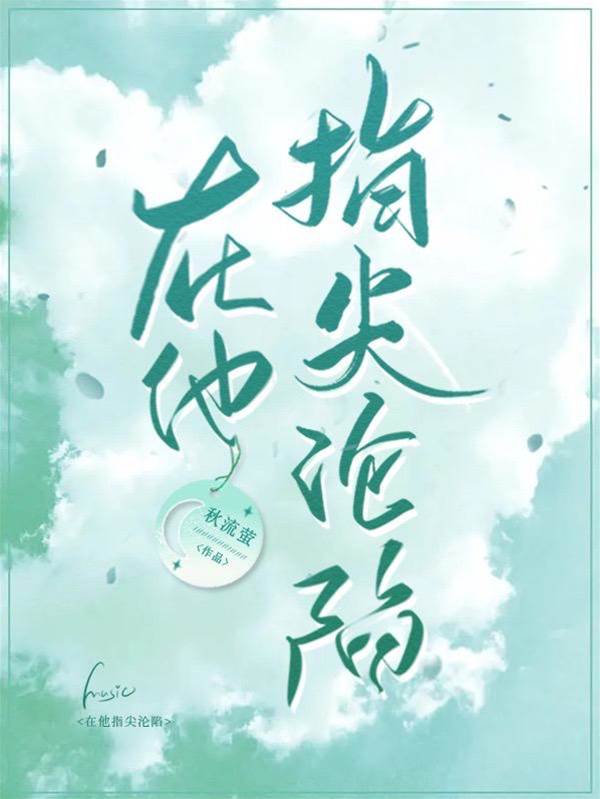《美人宜修》 第四十一章
近在尺咫的距離。
他們不是第一次離得那麼近,卻是第一次……近到呼吸相聞,齒纏。
咬得重了,怕又哭。
所以紀言信只是輕輕地咬住的下,下去,用力地吻住。
瓣相的清晰得可怕。
的,彌漫著淡淡的酒香。
紀言信并不啤酒的味道,可意外的,這一次卻覺得香甜可聞。
戚年不敢置信地睜大眼,連哭都忘記了,只看得見他那雙在黑暗中卻越發明亮的眼睛。漆黑的,卻帶著。
他的呼吸滾燙,鼻尖卻微微地帶著涼意。
可戚年卻覺得,有一種奇異的麻從心尖漫開,一點點地匯的里,走遍的全。
這個吻甚至都算不上吻,也不那麼溫。
可就是……意迷。
那種以他為中心,漸漸旋轉開的漩渦。而在岸邊,毫無預兆地被卷,深深地陷了進去。
直到……
戚年的被他得發麻,難地了。想說話,被他咬著,封住了所有可能說出口的話。
麻得難,了,被他得更。那一陣酸麻把剛咽回去的眼淚又了出來,小聲地嗚咽著,不敢招惹他,卻又忍不住。
紀言信蹙眉,終于往后一退,松開的:“怎麼還哭?”
語氣無奈得似乎拿沒有辦法。
戚年的眼底盛滿了眼淚,被涼薄的月一襯,卻像是一捧星輝,亮得奪目。
吸了吸鼻子,有些不太好意思:“……麻了。”
紀言信靜默了幾秒。
這種時候,他竟然有些想笑。
但顧念著戚年薄得不能再薄的面子,他花了幾秒鐘克制住。原本鉗制的手一用力,把從沙發里拉起來。著的也松開,在旁坐下。
Advertisement
旁的沙發往下一陷,戚年咬住才抑住倒冷氣的聲音。緩過那一陣麻意,一也不敢,忍得一頭冷汗。
紀言信沒去開燈。
勉強能視下,給自己倒了杯水,可送到了邊又想起,這水……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又放了回去。
等過了一分鐘。
他問:“好了沒有?”
那聲音著幾分沙啞,似乎沒有休息好。
“沒有。”戚年用手指了一下,那酸酸漲漲的覺讓忍不住“唔”了一聲,再開口時,聲音都有些抖:“你……不是明天回來嗎?”
都打算好今晚回去問紀秋要航班號,然后明天帶著七寶去接機……
“有點事。”紀言信的聲音淡了淡,不想多說。
“那紀秋呢?”
“過兩天跟爺爺一起回來。”他轉頭看了一眼,問:“為什麼晚上過來?”
戚年委屈地只想對手指:“李越今天回來,我去接他。本來是送他回去之后,我正好順路來拿……可是發生了一些小意外,就這個時間了……”
努力地看清手表,小聲地:“也……沒有很晚吧?”
紀言信閉了閉眼,不想和說話。
這個念頭還沒超過三秒,他又無力地問起:“怎麼過來的?”
他不問,戚年差點沒想起來……
代駕還在樓下等著啊!
“我要走了……”戚年火急火燎地站起來,抬步就走。
紀言信下意識地在經過自己面前時,用力地握住的手腕,那聲音早已沒了之前的溫厚,冷冽得像墜了冰窖:“又要逃?”
他的掌心灼熱,扣住,用力得讓戚年無法再往前。
戚年遲鈍,沒有覺到他那約的怒意,一愣后才想起回答:“我、我是找了代駕過來的。我上來很久了,不……”
Advertisement
紀言信打斷:“我送你回去。”
戚年腦子空白了一瞬,隨即拒絕:“你不是剛回來嗎?我自己回家就行了。”
紀言信松開的手,站起來,順手從椅背上拎起自己的外套穿上。
戚年還想阻攔,拉住他的袖口:“紀老師,真的不用了。你現在……”
“我不放心。”他垂眸盯住:“這個理由可以嗎?”
戚年一怔。
連著被搶白了兩次,今晚本就不太靈的腦袋跟僵住了一樣,無法思考。
默默地松開拽住他袖口的手,聲音低若蚊蠅:“可以。”
——
戚年抱著狗糧跟在紀言信的后下樓。
代駕的姑娘正靠在車門旁煙,指間的火星一明一滅。看見戚年跟在紀言信后出來,原本平靜的眸子微泛起嘲弄的笑意。
指間的煙被擲在地上,幾下用腳碾熄,笑了笑,問:“還走不走?”
“我送回去就行,多?”
代駕的姑娘豎了下手指比了個數,看著他數了錢,接過來收進口袋里。
轉走了幾步,想起什麼,回過頭:“我不是壞人,對的也沒興趣。”
話落,朝紀言信拋了個眼,這才笑著快步離開。
戚年一愣,第一個反應是……這姑娘的格還真是率直啊。
第二個反應……難不以為自己是害怕有企圖才找了紀言信出來?
可明明只是順手牽羊……唔,嚴格說起來,還是這只羊自己非要出來的……
※※※
一路上,紀言信除了剛上車問了一句“現在住哪”之外,一直冷著臉沒說話。心看上去非常糟糕的樣子……
戚年想起當初自己只是問他要了手機號碼,他就不高興了那麼久,何況剛才那孩直接向他拋了眼……這會應該想掐人?
Advertisement
估著自己纖細的脖子還不夠讓紀言信折的,就沒敢湊上去,安靜地抱著狗糧數經過的路燈。
遠遠地已經能夠看到小區了,戚年才想起問:“那七寶……你今晚帶走嗎?”
“不方便?”紀言信看著路況,沒轉頭。
“方便!”
這段時間養下來,戚媽媽對狗狗的恐懼已經降低了不,除了不敢溜七寶,別的都沒問題。
至于戚爸,他知道七寶的主人就要回來了,想起來就會問:“七寶什麼時候被接走啊?讓它多住兩天,以后可不一定會來我們家了。”
他跟戚年骨子里都是喜歡小的,尤其七寶又懂事又乖巧,還能滿足他奇怪的拍攝……
真是喜歡得不得了。
“那等從北巷古城會來,再接回來吧。”他放緩速度,經過小區門前的減速帶,再往里就不知道戚年住哪了:“指路。”
“一直開,最后一棟。”戚年看著或是散步,或是逛街回來的左鄰右舍,莫名心虛。
想著等會他就要從這里走出去,不知道會被多人看到,就控制不住地燒紅了耳。
等拐進最后一棟公寓樓,戚年示意:“停在空著的那個停車位就可以。”
車燈明亮,一眼看過去,能夠很清晰地看見地面上一個白漆的“7”字。
紀言信挑了挑眉,頗有些興味:“你家是不是什麼數字都要和七掛鉤?”
戚年想了想,一本正經地回答:“好像的確是這樣,我小學到大學,所有的學號基本上都帶了七字。”
停好車,熄了火。
紀言信轉頭看,在路燈下,的鼻尖有些紅紅的,那雙眼睛因為剛哭過不久,還泛著意。這會角彎著笑,倒顯得那雙眼熠熠生輝。
Advertisement
鬼使神差的,他問:“就沒有什麼想問我的?”
他意有所指得那麼明顯,戚年幾乎是瞬間就想起了前半個小時發生的事。原本就熱烘烘的耳就像是被水點了一把火一樣,那滾燙的熱度漸漸地往的兩頰蔓延。
下意識地咬住,剛咬住,就想起他咬著自己下用力吻上來的樣子,電一般松開,吶吶地攪著自己的手指,不知所措。
他瞇起眼,突然有耐心翻舊賬了:“除夕夜不是還問紀秋我的相親結果?”
戚年愧地埋頭。
還想著要矜持下的……結果……
“不好奇?不想知道結果?”他聲音低沉,徐徐之。
戚年捂住漲得通紅的臉,抗拒不了,用力地點了點頭:“想知道……”
想得都快走火魔了。
聯系不上紀秋,不知道他是不是對相親的對象很滿意,這些時間是不是還有再跟那個孩約會見面,會不會……就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只是這些沮喪的緒只能在心底最的角落里,一旦得見日,它們就會像漫天飄舞的飛絮,一點點地侵占全部的心房。
讓不安,讓焦慮,讓痛不生。
從不在意他始終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樣子,怕得是——有一天連仰他的資格,都沒有了。
鼻子酸酸的,又想哭了。
戚年用力吸了吸鼻子,有些哽咽:“如果是不好的消息,那你還是別告訴我了。”
聽出那約的哭腔,紀言信卻沒有一不耐。
他專注地凝視著像鴕鳥一樣把自己埋在“沙堆”里的戚年,有那麼片刻,似乎聽見了心里某一塌陷的聲音。
那是很的力量,讓他也無力抗拒。
“我沒去。”他手,住的下轉過來。
戚年悴不及防地撞進他專注的眼神里,有些發懵。
心臟比先一步知到空氣中那似有若無的電流,“砰砰砰”地劇烈跳著。
“沒有興趣,也不想期待。”他似笑非笑地看著:“雖然這麼說有些薄,但我……確實不是一個有耐心等陌生人走進這里的人。”
戚年的心跳聲幾乎要蓋過自己的聲音,唯一清晰的,是沮喪得要哭出來的緒:“我……我有些聽不懂……”
猜你喜歡
-
完結1175 章
霸愛成癮:穆總的天價小新娘
一場空難,她成了孤兒,他也是,但卻是她父親導致的。八歲的她被大十歲的他帶回穆家,本以為那是他的善意,冇想到,他是來討債的。十年間,她一直以為他恨她,他的溫柔可以給世間萬物,唯獨不會給她……他不允許她叫他哥,她隻能叫他名字,穆霆琛,穆霆琛,一遍遍,根深蒂固……
183.4萬字8 183694 -
完結2167 章

許你萬丈光芒好
“你救了我,我讓我爹地以身相許!”寧夕意外救了只小包子,結果被附贈了一只大包子。婚后,陸霆驍寵妻如命千依百順,虐起狗來連親兒子都不放過。“老板,公司真給夫人拿去玩?難道夫人要賣公司您也不管?”“賣你家公司了?”“大少爺,不好了!夫人說要把屋頂掀了!”“還不去幫夫人扶梯子。”“粑粑,謝謝你給小寶買的大熊!”“那是買給你媽媽的。”“老公,這個劇本我特別喜歡,我可以接嗎?”陸霆驍神色淡定“可以。”當天晚上,寧夕連滾帶爬跑出去。陸霆驍!可以你大爺!!!【雙潔歡脫甜寵文】
196.3萬字8.33 198147 -
完結395 章

公關的品格
公關——一個智商與情商雙高、掌握著企業生死的職業。失業記者卓一然轉型成為一名戰略公關,在變化無常的商業競爭中,靠著自己敏銳的新聞嗅覺與聰明才智,一次次為世嘉集團化解危機,也在公關部的職場變遷中,一步步從菜鳥成長為公關精英……
89.8萬字8 4256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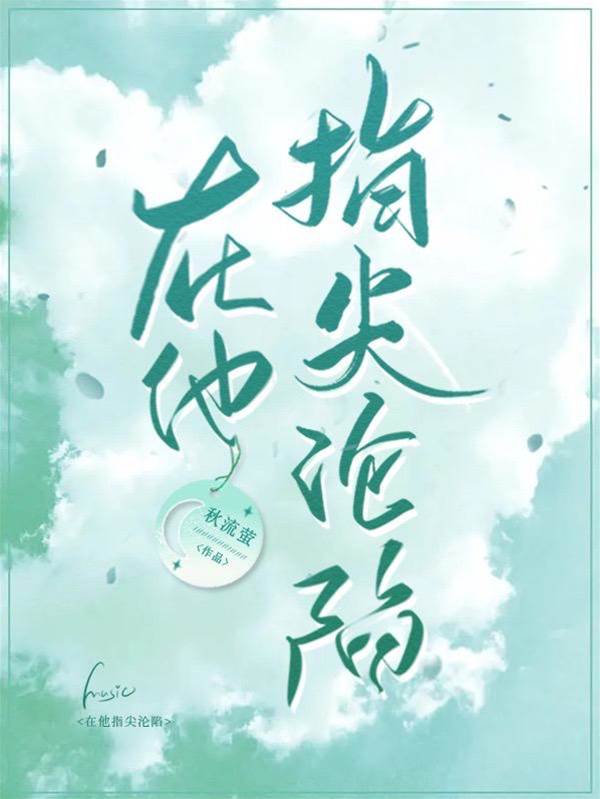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0313 -
完結344 章

離開後,小叔悔不當初
【追妻火葬場 先虐後甜 雙潔 HE】薄肆養了她10年,卻在一天晚上喝醉酒闖入她閨房。意濃之際,他喑啞著開口,“我會負責”。桑田滿心歡喜,憧憬和他攜手共度一生。他卻牽起了白月光的手,一度要步入殿堂……她一直以為他是迫於形勢,他是身不由己,可他對她十幾年的關懷備至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她聽到他和他母親談話……她才意識到一切都是謊言,是他從一開始就布的一個局。迷途知返,她藏起孕肚離開,搖身一變,成了海城第一豪門最尊貴的公主。……再次相見,薄肆看到她懷裏的兩個小女娃和站在她身後英俊挺拔的男人頓時紅了眼眶。他將人堵在衛生間抵著牆,不可一世的男人也會低頭,聲音哽咽,“孩子我不介意,跟他離婚,孩子我養。”
62.6萬字8.33 200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