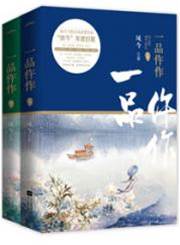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法醫秦明》 第317章
我突然鼻子一酸,很捨不得離開。想了想,俯在床邊親吻他的小臉蛋後,穿上外套走出了家門。
我們趕到現場的時候,已經被從蛇皮袋裡面拽了出來。
因為作坊裡的氣味太難聞了,被抬到了作坊外面的空地上,平躺在地面上。
我們圍在蔡隊長的邊,把他從盯梢開始,一直到行的全部過程都聽了一遍。我們並不急於檢驗,朝「黑作坊」裡一探頭,便聞見了一惡臭。
「我去。」大寶說,「這是什麼味?」
「死龍蝦。」蔡隊長說,「我還以為你們法醫都是聞不見臭的呢。」
「這比還噁心。」大寶皺起了眉頭。這個嗅覺靈敏的傢伙,在這個時候就比較吃虧了。
市局刑警支隊的兩輛勘查車都開來了,車頂的探照燈把現場部照得雪亮。
「喏,就在這兒。」蔡隊長走到了被發現的地方,說,「袋口是打開的。」
Advertisement
「你們沒抓到人?」我問。
「邪門的。」蔡隊長撓了撓後腦勺,說,「我行這麼多次,還沒有哪一次像今天這樣,一個人都抓不到的。不過,他們跑不掉。」
「你們的行洩了?」我試探著問。
蔡隊長此時也沒有了信心,說:「這我也不知道。恐怕是臨時接到通知的吧。我們到現場的時候,燈還開著,鍋爐也還開著。我們這一進門,天哪,就像是進了澡堂子。熱氣一接著一。不對,澡堂子不臭啊,這兒多臭啊。」
「你們關了鍋爐?」我問。
蔡隊長點點頭看看手錶,說:「這會兒離我們關鍋爐都半個多小時了,還開窗開門進行了通風。不然你們一來怕是就要被熏倒。」
「我們天天被熏,也沒倒過。」我笑著說。
「現場太髒了。」林濤蹲在地面上,用足跡燈照著地面,說,「這樣的現場,啥也留不下啊。」
Advertisement
「門鎖什麼的,也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痕跡證。」陳詩羽說。
「老韓,你們看過了嗎?」我問市局的韓法醫。
「從僵和斑的況看,也就是昨天晚上死的。」韓法醫點點頭,說,「上有一些損傷,主要在膝蓋和脛前。不過大側有不,裝的蛇皮袋裡也有。」
我順著韓法醫的手指看去,死者的大側果真是有不拭狀的,甚至有些還被拭到了腳踝部。我有些疑慮,皺了皺眉頭。
「是不是又要找源?」大寶說。最近我們被找源弄得暈頭轉向。
「又是年輕,又是隨意拋,會不會是指環專案啊?」韓亮在一旁提醒道。
大寶歪著頭看了看屋外地面上的,說:「不不不,這明顯不是鮑冰冰,比難看多了。」
「那會不會是有新的害者?」林濤問。
Advertisement
「韓亮不是說只有三段視頻嗎?」大寶說,「那不在視頻裡的人,肯定不會是一系列案件的害者。」
「確定只有三段視頻。」韓亮肯定地點點頭。
我說:「肯定不是指環專案,因為之前的都有穿服,而是赤的。之前的都被隨意拋,而是被藏在蛇皮袋裡的。」
「我看哪,肯定是黑作坊裡的人,是不是發生了什麼糾紛,弄死後準備運出去呢,正好聽說你們要來抓他們,」大寶攤攤手,說,「然後就跑了。」
「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釋了。」我說。
「不過,從表看,並沒有什麼致命損傷。」韓法醫說,「源倒是不難,的右頸部有文。」
猜你喜歡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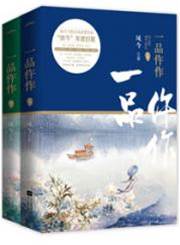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9155 -
完結911 章

鄉野詭事
在民間有一種說法,養“仙家”的人,仙家無論幫他賺多少錢,給了他多少好處,臨死前,仙家全都會收回去。聽村里的老人說,步規并非親生,而是七奶奶托“仙家”送養來的孩子。七奶奶是遠近有名的神婆,如今,七奶奶快死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找上了步規,步規為了活命,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將要到來的危機。鄉野詭事,民間傳聞,奇詭禁忌,一副光怪陸離的民間雜談,在步規面前展開……
196.6萬字8 5273 -
完結1565 章

苗疆蠱術雜談
我蠱毒纏身,從一出生就注定了死亡……可我卻活了下來。 我的故事,從那年的冬至開始。 捉屍蟲,鬥陰鬼,豢金蠶,養蛇蠱,采毒草,煉煞魂! 苗疆詭秘,盡在此書……(本故事純屬虛構)
280萬字8.33 202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