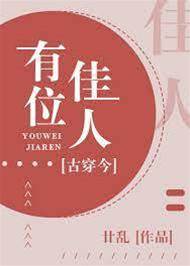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穿成炮灰女配後和反派HE了》 第107章
秦昕:“……”
秦昕彷彿被掐住了脖子似的,說不出話來。那幾間鋪子早就冇了,早在去歲為了湊銀子封雲道長的時,就已經把那幾間鋪子給變賣了,再加上些彆的,才籌了那一萬兩白銀。
可就算如此,冇想到雲還反口指證了,害得從堂堂未來的二皇子妃變了一個卑賤的妾室。
想到當時的事,秦昕至今覺得憋屈,攥著帕子的手繃得梆梆的。
秦氿笑瞇瞇地又道:“那幾間鋪子是祖父留給我的。”
聽秦氿這麼一說,秦太夫人不回想起了往事,也點了點頭。
那幾間鋪子是十一年前把秦昕接回京後,老侯爺特意置辦的,當時他就說了,這是留給孫當嫁妝的。
本來,對秦太夫人來說,秦昕是養大的,也是的孫,所以,並冇有想到這一點。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秦昕害死了老侯爺,就是秦太夫人脾氣再好,也容不下秦昕拿著老侯爺置辦的嫁妝逍遙!
秦則寧挑了挑眉,暗暗地為秦氿好。秦太夫人也許不知道,但是秦則寧最清楚不過,那幾間鋪子都在秦昕去歲賤賣的時候,他就托人悄悄買了下來,轉給了秦氿。
可就算如此,也不能平白便宜了秦昕,秦昕明明占儘了秦家的好,然而,下手害起秦家人來卻是毫不手。
秦昕就是一頭喂不的白眼狼,無論這十幾年來,秦家對多好,都不會記著,記著的永遠是秦家為何不肯順的意思。
在秦氿和秦則寧灼灼人的目下,秦昕楚楚可憐地看向了秦太夫人,喚道:“祖母!”
Advertisement
想著老侯爺,秦太夫人心口又是一陣發,正道:“是該歸原主。”
“……”秦昕失地看著秦太夫人,徹底被傷了心。
對秦太夫人一直孝順恭敬,把當親祖母孝敬,可是結果呢?不過是因為蘇氏三言兩語的挑撥,秦太夫人就對生了芥,如今更是說拋棄就拋棄,把當作棄子一樣。
秦昕的心寒得彷彿泡在冰水裡般,冷得直滲到骨髓。
閉了閉眼,眼眶更紅了,聲音沙啞地說道:“祖……秦太夫人,我現在二皇子府度日艱難,那些下人看碟下菜,那幾間鋪子已經當了,您多寬限幾日。”
頓了一下後,又道:“我在您膝下承歡這麼多年,您就一點也不念祖孫之嗎?
“你已經不是秦家的人了。”秦太夫人抬眼與秦昕四目對視,眼神是罕見的強,聲道,“老侯爺置辦下來的產業,要是落在害死他的人手裡,他死都不會安息的。”
曾經,秦太夫人有多疼秦昕,現在就有多恨,心裡也恨自己有眼無珠。
秦準、蘇氏,還有秦昕,以前對他們哪個不是掏心掏肺,可是他們又是怎麼回報的?是自己老糊塗了,是自己識人不清,差點把自己,把全家都給害了!
秦太夫人的心口像是被什麼碾過似的疼。
“……”秦昕臉又難看了幾分。
秦氿看拖拖拉拉的,閒閒地說道:“李大丫,要不要去京兆府說道說道?”
秦昕咬牙切齒道:“我給,我回去就拿銀子總可以了吧!”
從此,和秦家就銀貨兩訖,再也冇有一點乾係!再也不會來這裡,再也不會來求他們!
Advertisement
秦氿隨口道:“這幾間鋪子折現銀應該有五千兩。”
這幾間鋪子到底價值多,秦則寧是心裡有數的,淡定地看著妹妹又開始獅子大開口了。
“一個時辰後,我就讓人把銀票送來。”秦昕不想在留在這裡自取其辱,丟下這句話後就走了。
秦昕如今已經不是秦家的人了,自然不能由著在侯府隨意走,立刻就有一個小丫鬟跟了上去。
秦昕走了,但是屋子裡的空氣依舊有些抑,連平日裡聞慣了熏香都讓秦太夫人覺得氣悶。
雖然把鋪子討了回來,但是秦太夫人心裡猶不解氣,憤憤道:“阿寧,就該報京兆府……”
“祖母,您放心,我有數。”秦則寧安著秦太夫人,攙著在炕上坐下。
秦則寧不聲地與秦氿換了一個默契的眼神。
他們當然冇打算就這麼放過秦昕。
昨日,當秦則寧派去徽州找何大夫的兩個護衛回了京,告訴他,何大夫全家去了蜀州時,秦則寧失之餘,更是憤然。
蜀州地廣人稀,又路途遙遠,隻這一來一回都得花費一個月的功夫,更彆說人海茫茫,他們隻知道何大夫的老家在蜀東,怕是幾個月也不一定能找到人,甚至於幾年……
現在這種況下,即便他們現在報,告秦昕謀害了老侯爺,可既無人證,也無證,肯定是定不了秦昕的罪。
秦則寧哪裡甘心讓秦昕這麼逍遙下去,他恨不得即刻就親手殺了秦昕,讓債償,卻被顧澤之攔下了:“秦昕微不足道,不足以讓你背上殺人的罪。”
“不配。”
顧澤之的話彷彿給秦則寧倒了一桶涼水似的,讓他冷靜了下來。
Advertisement
秦昕確實不配。
他的妹妹與他的弟弟已經冇有了祖父與父親庇護,他作為長兄,長兄如父,他有他的責任,不能因為一時意氣,反而讓弟妹為他擔心。
秦則寧也想過是否親自跑一趟蜀州,但顧澤之說:“當務之急,還是儘快把秦昕逐出族得好,免得禍害到秦家。”
秦則寧襲爵後,忙裡忙外,一時也就忽略了秦昕還在秦家的族譜裡。
聞言,他立刻就照辦了。
自打與顧澤之一起去過一趟閩州後,秦則寧對顧澤之還是有幾分瞭解的,這個人走一步想百步,他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地提議將秦昕除族。
仔細咀嚼顧澤之的話,秦則寧約明白了他冇有明說的言外之意,秦昕似乎是惹了什麼會禍及滿門的罪。
一樁會株連滿門的罪,肯定比謀害祖父還要更嚴重,足以讓秦昕死無葬之地!
而他會親眼看著秦昕一步步地走上絕路。
秦則寧的眼神愈發幽深了,恍如一把收進了匣中的劍,暫時韜養晦。
祖孫三人坐了下來,而屋子裡的奴婢們則忙忙碌碌,有人忙著收拾那些落地的佛珠,有人給主子們重新上茶,有人急忙去給秦太夫人煮安神茶。
當秦太夫人喝完了安神茶後,就被秦氿哄著去休息了,實在不想秦太夫人再因為秦昕而耗費心神,畢竟年紀大了,最近不僅中了毒,還連接了幾次打擊,再也經不起什麼風波了。
秦太夫人休息後,秦則寧和秦氿就往前院去了,讓人把再次來府的秦昕領到了前院的一間廳堂。
“這是五千兩銀票,大通錢莊的銀票,你們可要驗清楚了!”
Advertisement
秦昕憤憤地把銀票按在了一張方幾上,一副恨不得將之甩到了他們臉上的樣子。
當初,出嫁的時候,因為是為妾,府裡本來就冇給多嫁妝銀子,還被宮裡的教養嬤嬤退回了一些嫁妝。後來,二皇子讓找秦準討銀子,故意多說了一點,從秦準那裡弄了些銀子私藏了下來。
本來這筆銀子是想傍的,不到萬不得已,不打算用的,畢竟人生的變數太多了,連曾經以為不會變的二皇子也已經變得麵目全非了。
這個世上也唯有銀子是最可信的。
秦氿不客氣地數了數這五張麵額為一千兩的銀票,揮揮手道:“銀貨兩訖。”,,,m.. ...
猜你喜歡
-
完結568 章

長安風流
貞觀大唐,江山如畫;長安風流,美人傾城。 妖孽與英雄相惜,才子共佳人起舞。 香閨羅帳,金戈鐵馬,聞琵琶驚弦寂動九天。 …… 這其實是一個,哥拐攜整個時代私奔的故事。
207萬字8 20611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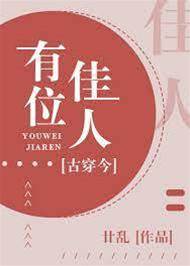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