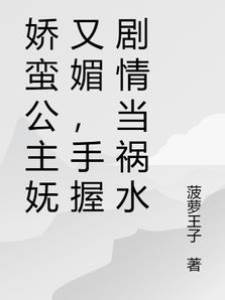《侯門美人骨》 第231章:番外再言前世因6
秦臻遇到言梓陌是一個偶然,那一日正隨著顧輕黛去皇覺寺上香,他瞧著手上的鐲子終究在那梨花樹下問了一句:「想不想報仇?」
那時他的眼眸裏面沒有憐惜沒有驚慌,只有那幽深至極地等待,甚至心深還有一種對未來計劃的期待。
他清楚,別看眉目親和婉轉,可彼時的言梓陌不過是用偽善的面龐掩藏著的仇恨,他相信會上船的。
——所以他毫不掩飾地扔出給治癒臉上的傷痕,想辦法恢復聲音的橄欖枝,他知道會答應,任何一個過那般摧殘的子都會答應。
人這一生也不過是屈屈數十載,想要活的肆意張揚、想要用鮮洗刷自己的恥辱,必須站在那最高的頂峰,所以那一日之後他在不遠看著告別顧輕黛,住到了清心觀。
從乾元五年到乾元七年,整整用了兩年去之語臉上的傷痕,秦臻依稀記得那日帶著醫師趕過來的時候所說的話:「這葯有毒,毒致命。」
【多大的害】
揚起了一張臉,恐怖的劃痕在臉上麻麻,雖然曾經得到過醫治,可那醫師的能耐並不高明,可那下筆的時候卻異常的堅定。
「服下只有五年的壽命。」
秦臻依舊神如常,看的時候就像是在看待價而沽的品,而言梓陌卻沒有一點傷痛的覺,五年前便是一沒有靈魂的品罷了,而如今這人不過是為了讓他盡其用。
【為什麼是我?】
無法說話,所以只能用最簡單的筆畫來勾勒自己心中所想,秦臻出手了寫下的字跡,聲音近乎低喃:「心中有很的人,方能功,對皇室有仇的人,方能勝任,思來想去你是最好的抉擇,而且你我之間終有些許牽連。」
Advertisement
當日平西侯府出事太快,快到讓人沒有辦法應對,就算母親寫信讓自己照一二也終究了鏡花水月。
只是沒有想到偶然的時機,他會認出來,手上那玉鐲母親好似也有一個,猶記得母親曾說這是和那隔房姨母同姐妹的憑證。
他原以為早已經死去卻不想還滿懷仇恨的蟄伏,瞧著無意間對著楚熏的殺意他無奈一笑,那散落各地的春宮冊或許是洗不去的污點。
【謝謝!】
用自己的手寫下了真摯的緒可他心卻狼狽的有些不敢直視,若不是偶然間得知乾元帝暗暗藏著畫軸的,他或許不會這般鋌而走險。
人在面對選擇的時候終究是自私的,其實他知道心也明白這個道理,畢竟看遍了這世間的醜陋,之所以這般做可見這些年的境。
——或許正是沒有人給溫暖,才會這般稀罕這不見底的明。
他用盡辦法恢復地容,甚至請來院的老人教導如何上取歡,他親眼看著越來越妖嬈的姿態越來越嫵的眼神。
那一日輕笑著站在自己面前,一雙充滿老繭的雙手早已經白無比,一字肩的紗輕輕點綴,甚至還能看出晶瑩的。
他知道,這是藥效起作用了!看著自己的時候並沒有一丁點害,反而像是接檢驗的子,他知道他又在心口上劃了一道口子。
「時間到了。」
他說出話語的時候聲音有些然,這兩年很聽話很聽話,聽話到讓他不由得想要推翻之前的計劃。
可他終究是一政客,政客在另一意義上已經不是他自己。
潔白的下輕輕一點,就算那一雙眼眸米娥友直勾勾地盯著自己,可那自然而然的魅讓他不由得苦笑了一聲。
Advertisement
時也、命也,當日那風和日朗的小山村指不定也是很好的歸宿,可如今卻生生走上了另一條不歸路。
言梓陌臉上的傷痕終究為了過去,那一日韓臘雪之日他親手將他送到了乾元帝的手中,那個沉穩的帝王在他印象當中第一次那般驚慌失措、視若珍寶。
後來的一切事都順理章,雖然依舊不能說話,可他相信會開口的,那個人在他心頭留下了痕跡卻又被他親手毀掉。
宮之後很低調,可帝王的三千獨寵怎麼可能讓獨善其?而且也沒有獨善其的資本,上肩負著使命。
乾元帝很寵,雖然他刻意不去打聽的消息,可從衛颯那張沉的臉上他也能看出幾分來,剛開始心免不得幸災樂禍,可後來午夜夢回時的苦卻無人知曉。
楚熏兒被乾元帝厭棄送出京城之外安置的時候,他親自帶人將劫走,當初了多大的罪他便一點一點地返還給。
他記得衛颯趕來時候楚熏那毫無的臉龐,而那位冷無的衛大人等待事完才艱地開口:「當初,你就是將人藏到這個別院嗎?」
「是啊,你站在外面跪在裏面,就和我現在一般。」
楚熏的聲音裏帶著無喜無悲的神,最後更是哈哈大笑了起來,最後不知道是汗水還是眼淚,了污濁的臉龐。
「你當日說一小丫鬟背主,路過的時候來這裏看一眼,就是為了讓看到我嗎?」
秦臻整暇以待地著衛颯突然兇狠的臉龐,還有那狂怒的聲音,他第一次看到冷清絕的衛大人會用那紅通通的眼眸看人。
或許他是的吧!只可惜錯了方式。
「是啊,你自詡算盡天下人心卻不知你邊最親近的人背叛了你,若不是蕭千城臨時用你的名義調走那些護衛之人,我怎麼可能那般輕易就得手呢?衛颯,那春宮冊你看了嗎?你瞧多啊!」
Advertisement
他和衛颯都沒有理會那瘋子,因為生不如死會是最大的懲罰,兩個人出去之後迎面而來的便是一拳頭。
他了鼻子下面那溫熱的東西也沒有發怒,輕笑著道:「難道衛大人憐香惜玉了?若是如此我送衛大人一個人。」
「你毀了。」
「是你毀了。」
他的眼眸瞬間危險了起來,這個男人自己沒有本事親信旁人造今日的局,居然還數落自己的罪責,他真是好大的臉面。
「我。」
「嗎?」
他嗤笑了一聲離開,其實他知道當初他之所以沒有親自守著言梓陌是為了送言梓煜離開,他為了救走言梓煜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甚至不惜迷皇室。
——可說一千道一萬,他終究沒有保得住。
三年的時間乾元帝從一個中興之主了奢靡之帝,而手握重兵的尚家裏應外合之下一舉拿下了皇城。
其實乾元帝有殺了的機會,可終究是沒下那狠心,最後在皇座上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引頸自刎。
若是乾元帝知道自己會上這個年齡可以當自己兒的子,他當初或許不會火急火燎地將言家打垮。
只可惜,這世上沒有後悔葯。
不管乾元帝也好,衛颯也好或者自己也罷,都明白這個道理。
尚家取得山河之後除了對楚皇室趕盡殺絕對其他人可以說相當的懷,所以一時間也進了鼎盛時期,而衛颯更是原封不的為了新朝的宰相。
那一日清心觀前,他是最後一次見言梓陌,如花的容已經開始頹敗,雙眸沒有多神,兩鬢添了白髮。
那葯發作了,這是早已經明白的道理,可他還是盯著瞧了許久,只聽淡然一笑:「你其實不用自責,這是我當初選擇的路,無怨無悔。」
Advertisement
的聲音自從恢復之後,自己還是第一次這般近距離的傾聽,很很魅,他知道不是故意的,而是這種上的東西已經刻了的骨。
「我……」
「日後我死了將我埋在後山的梨花樹下,聽說梨花是最純潔的花。」說的淡然,可他的心卻揪的生痛,最後還是答應了。
「你不見那兩個孩子嗎?」
「不用了,免得污了他們的名聲。」
秦臻能聽出來,的聲音裏面沒有一點作偽,甚至也沒有一點憾,或許是人生最後旅途已經沒有了能牽心弦的東西。
「他們……」
「我想過見他們,那小娃滿臉戒備地著我……額,我知道我不是好人。」
說完走了進去準備輕輕合上門,卻又聽說了一句:「告訴山下那人,這一切塵歸塵土歸土,我不會見他。」
「好。」
他輕聲應了一個字,也不知道有沒有聽到,只看到將腦袋了進去,他知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活生生的見面。
下山的路上果不其然又到了衛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只可惜這個人不敢上去,也不敢去見,他或許是怕宛若銅鈴的笑聲也怕溫言語的問候。
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仇恨,而是什麼都不在乎。
「……」
「不想見你,死後想魂歸毓秀山。」
「還在乎嗎?」
「呵,你的臉真大!已經撐不住和你細話當年了,既然如此還不如不見。」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落井下石的小人,可面對衛颯的時候他本能的嘲弄。
「兩個孩子想見。」
「都是快死之人何必多了那些牽掛?生來富貴卻慘遭蹉跎,你縱使為了著想也別想這些了,還不如放手讓離去。」
「秦臻,你真可怕!冷心的讓人恐懼。」
自此毓秀山下多了一個牧田人,而大宣王朝了一個翻雲覆雨的國之巨宰,同一年秦臻登上了宰輔之位。
猜你喜歡
-
完結93 章

鹽霜美人
容虞是個媚色無邊的女人。 眾人皆知,她是沈映身上最大的污點,惡毒又放浪,沒有一個人不厭惡她。 而沈映向來溫雅清雋,容色世間少有,是高山之雪,是天上明月,也是無數女人藏在心頭的白月光。 但是又沒有一個人不嫉妒容虞。 因為這個妖艷的女人,把不染凡塵的沈映從天上拉了下來,弄臟了他。 對自己狠對別人更狠的絕代風華高嶺之花|毒的一批想要什麼就一定得到手的艷冠天下大美人 ——我想讓你學會的,從不是怎樣愛我,而是怎樣去愛你自己。 男主白切黑,女主黑切黑。一個譽滿天下,一個聲名狼藉,一個神仙公子,一個絕美女妖精。 【高亮】1v1 he sc (別看文案這樣其實本文感情雙箭頭,很粗很粗的那種) [排雷] 1.【重中之重】女主心理有病,好多行為常人根本不能理解,沒有憐憫之心或者說她根本就沒有心!可以說是個神經病吧(?)后面會越來越像一個正常人。 2.由于女主的成長環境,她對男主有近乎偏執的占有欲,說起來論慘還是男主慘,只是寫文女主視角多一點,故而會有一定偏差。 3.把這條單獨拿出來說,這是一場對等的愛情,沒有誰卑微一點,作者本人非常不喜歡地位上的差距帶來感情上不平等,不要連正文都沒看就說什麼女主過于卑微從而上升到什麼什麼,謝絕ky
27.7萬字8 9845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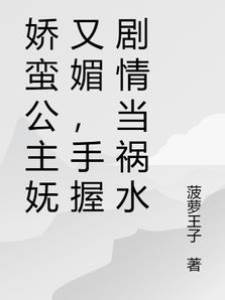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3966 -
完結214 章

瑜珠
初進周府那年,瑜珠十四歲,家破人亡,無依無靠。 周家念著與她祖輩的一點情分,只將她當表姑娘養。 可是及笄后的某日,她遭人算計,被發現與周家嫡長子同臥一張席榻。 二人只能成婚。 婚后,所有人都認為她是為了上位不擇手段的女人,包括她的丈夫。 她在整個
34.5萬字8.33 11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