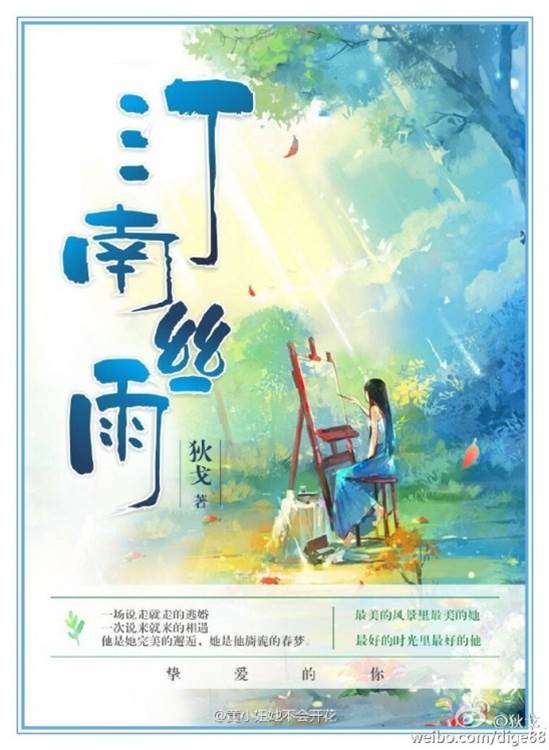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慈悲城》 第20章 他的方式
書房門前,慕善腳步一頓。
陳北堯的心腹們都在。暮照進初秋微涼的房間,也照亮他們的臉。那些容明明五迥異、年紀不同,可眼神中偶爾閃過的明冷漠,卻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陳北堯,是那個模子嗎?
“嫂子!”李誠最先看到,立刻起。其他男人也紛紛站起,一口一個“嫂子”此起彼伏。周亞澤甚至還笑嘻嘻的明知故問:“約!嫂子舍得從北京回來啦?”
只有陳北堯靜靜坐在單人沙發裡沒,淺藍細紋白襯,影清冷料峭。因為沒痊愈,他的臉還很蒼白,神很平靜,在下有一種脆的病態的俊。
慕善站在原地,只覺得十指指尖,微微發涼。
他看起來這樣靜好,明明與這些男人都不同。他怎麼會是最壞最狠那一個呢?
陳北堯也抬頭看著,有片刻的沉默。
他對最後一幕記憶,停留在離開那天。那時因為多日照顧傷重的他,幾乎都有些蓬頭垢面,容悲傷憔悴,黑眼圈深得像只可憐的熊貓。
可離開他的半個月,這個人明顯把自己調整得很好。此刻俏生生站在那裡,細瓷般淨白的臉,恢複水一樣的澤。墨玉般的大眼睛澄澈亮,只消上一眼,就令他心神舒暢,愈發想要把這些鮮活的,統統納為己用。
他已經等了太久。
在他二十六年的生命中,被熱烈的著的十八歲那年,是他最快活的日子。沒有母親的哀愁,沒有父親的忘,也沒有這些年近乎麻木的腥和風口浪尖的驚心魄。
Advertisement
只有豔得令人迷醉的容、甜糯的溫言細語、充滿慕的怯凝,像一場能融化他心的迷夢,多年來,令他流連忘返。
所以重逢那一天,他坐在寶馬上,看到安安靜靜站在一堆混混中,幾乎是立刻下了決定——
他要重新得到。重新得到那些熱烈的、溫的、赤誠的意。
他要心甘願,他要兩相悅。
於是忍了又忍,等了又等。
百般手段都放棄不用,有時實在忍不了,就在黑夜裡抱著的軀,自己淺嘗即止。
他告訴自己,既然想要最好的,理應付出耐心。
可明明蜷在他旁,溫而委屈的喊他“北堯哥哥”;明明吻得比他還要不舍和火熱。
明明著他,卻固執的想要停止。
想停止?
也許是他太縱容,是他退讓太久,才令覺得,可以決定他們的?
好吧,既然他的人倔強正直,那他只能換一種方式。
他原本就更加擅長的方式。
想到這裡,他看著,角微彎,笑意淡如水紋。
“過來。”
慕善長眸清亮盯著他。
過來?
簡潔的兩個字,卻著陌生的強。
他以為他是誰?
以往在陳北堯面前,總是輕易失去方寸。可這一次,一極堅定的力量支持著——那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強烈意志——保護父母,不讓任何人傷害他們,哪怕是陳北堯。
於是不慌不忙走過去,低頭看著他,淡淡的笑:“陳北堯,你可真啊。口口聲聲說我,轉把我父母往絕路。他們五六十歲了,你也下得了手?誰的命在你眼裡都跟草似的吧?”
Advertisement
清脆利落的聲音,又甜又狠。
李誠看一眼,沒做聲;周亞澤一挑眉,頗有興趣的看著。其他幾個男人,個個神不。慕善就是故意說給他們聽的,心頭有火,逮住一點機會就想報複。
陳北堯也不生氣,淡笑著抬手,抓住了的胳膊:“坐。”
慕善的目掃過他的手,落在他上。
單人沙發被他高大頎長的軀占據大半,只留下掌大塊空地。
他要讓在眾目睽睽下坐到他懷裡?
他沒聽到剛才的嘲諷嗎?
皺眉,人還沒,手上猛的傳來一大力!
恍惚間,似乎看到他眼中掠過笑意。接著一個趔趄,半個子跌坐在他大上。
悉的堅實溫熱的,令心頭一。這恥辱的栗愈發加深了對他的怒意。
立刻往邊上一挪,下他的大,坐到沙發上。
所有人都沉默。不想在眾人面前與他撕扯,沉著臉,並沒有急著掙站起來。
陳北堯卻沒看。
他目視前方,微微抬起的側臉俊安靜,沉黑雙眸有淺淺的笑意。
慕善腰上忽然一麻。
是他的手,悄無聲息搭上來,將的腰線穩穩握住。慕善只覺得一涼意“嗖”的從腰間,一直躥到後背,激起陣陣栗。
竟然……竟然有點怕這樣的他,不聲的他,勢在必得的他。
可轉念想到父母,又強迫自己鎮定下來。
“老板,要不下次再議?”李誠清咳兩聲,率先開口。
“說完。”陳北堯偏頭看一眼懷裡的慕善,目微沉。
李誠清咳兩聲道:“柯五幾個已經到了深圳,我讓他們躲個半年再回來。湖南幫絕對查不到。”
Advertisement
慕善心頭微冷。
周亞澤又笑道:“丁珩從湖南回來了,好像還跟湖南幫談妥。要不要幹掉他?”
卻聽陳北堯淡道:“不行。最近死的人太多。”
李誠點頭贊同:“上個星期,荀市長的書還給我電話,說生意平平穩穩就好。最近風頭很,低調點好。”
正聽著,慕善忽然到側額被什麼韌的東西住,輕輕的蹭著。
那是他的側臉,上的長發。
慕善全發麻,只覺得整個都要石化。
接著,一縷微熱的氣息,羽般拂過的臉頰耳際。覺到,是他埋首在長發間,深深嗅了嗅。
然後,他發出一聲微不可聞的滿足歎息。那種覺,像是極的人終於覓得水源,又愜意又歡喜。
只歎得慕善骨悚然,心頭發。
沒看到,旁的陳北堯察覺到的僵,臉上笑意更深。
幾個人又商量了一陣,全是些見不得人的事,甚至還包括上次殺丁默言的幾件善後小事。慕善完全明白,陳北堯就是要讓聽這些機。
終於,男人們起告辭,書房門被周亞澤順手關上。
兩人並肩而坐,同時靜默。
慕善斟酌半瞬,剛要開口,他卻忽然低頭,埋首在脖子上。
一陣熱麻傳來,那是他的吻,自顧自細細的流連。
慕善心頭再次發:“你幹什麼!”
他又狠狠吸了一口,看著肩頭一片深深紅痕,才緩緩抬頭。清俊容在燈下璀璨如玉,烏黑的眉眼笑意。饒是慕善看慣了他的英俊,也沒見過他笑得如此舒心,心頭微震失神。
Advertisement
就在這時!
慕善只覺得一極大的力量上肩頭,後背被迫重重撞上沙發!眼前一花天旋地轉,本看不清他的作。接著,一個重重的溫熱軀了上來。
再定睛一看時,他的一雙黑眸竟已無比近的停在面前。
不,還不止。
大概剛才的作牽了傷勢,他微著氣,雙臂卻著的,將的上半扣在沙發上。雙跪在側,軀幾乎是完全近。
曖昧親昵,勢在必得。
饒是慕善心中早有籌謀,此時也被他的突然發難驚呆了。不能,也本忘了。
他近在咫尺的著,眼神清冷、篤定,含著笑意。
他徑自閉上雙眼,一低頭,冰冷的就狠狠了上來。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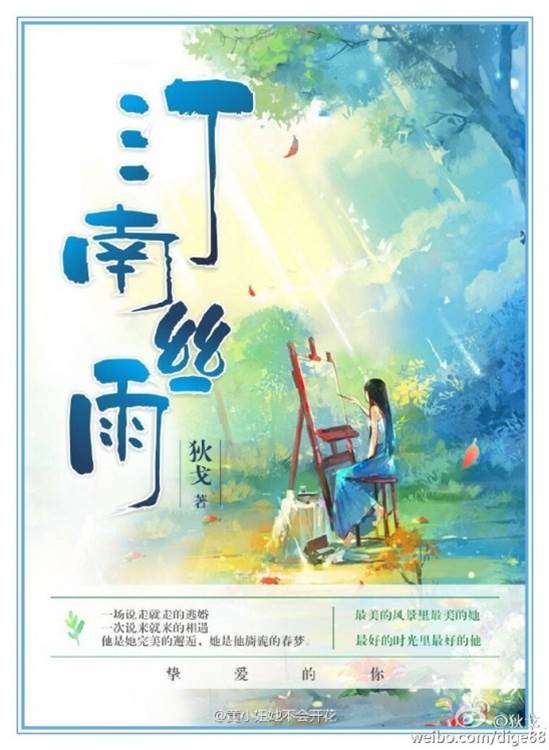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