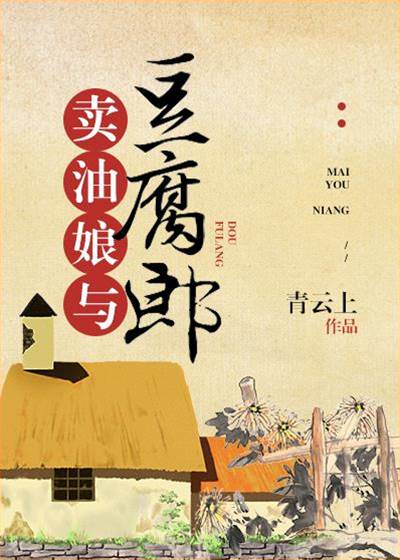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隔壁的小書生》 第92章 觀日出 日出
長江黃河乃本國聞名的兩大天塹, 兩岸危崖聳立,各怪石嶙峋;中河水滔滔,晝夜奔騰不息。
都說“活人難渡, 飛鳥難行”, 意思是哪怕你水再好,奈何水深河闊, 也是游不過去的;就算鳥兒飛得再高,中間也是要歇一歇的。
而越是這樣艱險的地方, 越有人想去瞧瞧。
故而在兩條大河附近, 頗多名勝古跡, 也有今人專門修建的高樓莊園, 都是預備人賞景的。
自從出去放了一回風箏后,莊秀秀整個人就野了, 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著去看長江。
甚至還連夜打發人出去買了許多游記話本來,專門翻到寫長江的部分細細品讀,在腦海中一遍遍回味。
長了這麼大, 還沒出過遠門呢!
此去南邊的九層高塔,若乘馬車慢行, 往返說也要七、八日, 勢必要在外留宿的。
且不說莊文興到底怎麼說服弟弟和弟媳, 對侄兒一行人外出游玩的事, 他卻也是謹慎到了骨子里。
路上有兩莊家的宅院, 略可以住一住, 至于其他時候, 也早就派人先行一步,去當地最好的酒樓飯莊打點……
就連跟著的人,也都是兄弟倆手底下最明強干的護院隨從, 務必要做到萬無一失。
畢竟莊家本家這邊,就只剩莊秀秀這麼一個姑娘了,若再有閃失,只怕一眾人上吊的心都有。
其實出行真的是件很費心神的事:
怎麼走,走哪條路,什麼時候走,什麼時候歇,吃什麼、住哪兒……樁樁件件都馬虎不得。
之前白星三人獨自上路,一切都是自己來,如今既然有莊家這個“地頭蛇”打點,他們也樂得自在,真就跟著吃吃喝喝起來。
Advertisement
南方天氣多變,白星就發現自己觀天象的本領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北地氣候穩定,一般前一晚看了天之后,第二天是什麼樣兒就不帶變的;可南方不同,且不說更西南的十里不同天,就是這未過長江的云間府都像小孩子的臉,說就,說下雨就下雨,著實人猝不及防。
白星邊走邊看邊學,竟也迅速掌握了不以前從未接過的新天象。
這次出門,穿的還是慣常的短打。
阮太太雖是好意,但顯然不太了解江湖客的生活習和真實需求。那些都是上等綢做的,則矣,但真心不耐用,不就勾。
上回放風箏時白星穿了一回,還沒玩到一半時,子就被滾蛋,上面滿是褶皺和被刮起來的細……
于是白星長了記,決定將那兩套麗的長收起來,等什麼時候閑在家中不出門時再穿。
此番出行的四位年輕人都沒來過這一帶,看什麼都新鮮,見好吃的好玩的了,也會隨時停下來瞧一瞧。
走著走著,又下雨了,一行人只好去路邊的茶棚歇腳。
云間府的雨水一向來得快,去得也快,要不了多久就可以重新上路了。
說是茶棚,但因為這里位于民道三岔路口,多有往來客商停下歇腳,所以不附近的村民甚至是商販都會來這里擺攤。
賣各吃食茶水的自不必說,甚至就連修車打鐵、補裳的攤子都有,老遠去但見人頭攢熙熙攘攘,竟宛如一個型的小型集市。
廖雁不耐煩枯等,牽著大黑四溜達,走著走著就聞到一奇異而醇厚的甜香。
湊近了一瞧,淡黃的一長條,約莫黃瓜那麼細,像點心又不太像……
Advertisement
“這是什麼?”他好奇道。
這攤子上一共兩個人,一個四十來歲,一個二十來歲,長相有六七分相似,約莫是爺倆。
他們一個在前頭招呼客人,另一個卻在后面棚子里忙活。那里架了一口鐵鍋,旁邊一塊案板,年輕些的正揮汗如雨熬著什麼,濃郁的甜香味就是從鍋子里飄來的。
“嵌字豆糖。”年長些的男人說著,又從旁邊了一把刀出來,麻利地將那一長條切約莫半指厚的方片。
切完之后,他用手往長條上面輕輕一推,一溜兒幾十塊方片便都整齊地傾倒,竟出來里面黑的“福”字!
嵌字豆糖,原來如此!
廖雁喜得抓耳撓腮,覺得這可太有意思了。
“老倌兒,這怎麼做的?”他越發好奇道。
那男人憨憨一笑,“客,這可不好告訴您知道。”
做買賣的,求的就是獨一份兒,萬一給人學去了,他們還靠什麼賺錢呢?
說話間,后頭的年輕人已經熬好一鍋糖漿,果然不遠就有許多人或明或暗,長脖子、踮起腳尖看,試圖破解其中的奧妙。
奈何人家早有防備,直接就搬著鐵鍋往棚子里頭去了,進去后把布簾子一蓋,啥都瞧不見了。
眾人發出一片憾的噓聲,第無數次怏怏散開。
廖雁本也是順口一問,他就是個使刀的,難不還真想師學藝改行賣糖去?故而人家不說,他也不在意,只是大手一揮,豪爽道:“來半斤!”
糖果價高不易得,尋常百姓往往一次只買一二兩甜甜兒,誰想到這個年輕小伙子張口就是一斤,那漢子愣了下才不敢置信地跟他確認道:“客,您,您要多?”
“一斤啊!”廖雁道,“這玩意兒重吧?”
Advertisement
點心之類的倒罷了,但凡混著麥芽糖的糖果,基本就沒有輕巧的。
恐怕一斤也稱不了多。
那漢子見他不像說笑,頓時歡喜起來,忙取出干凈的油紙折了幾下,變敞口紙袋的模樣,又往里裝嵌字豆糖。
果然如廖雁所料,這豆糖十分沉重,一斤也不過掌大小一捧。
廖雁手要接,卻見對方非常謹慎地躲了一下,然后陪笑道:“這錢?”
廖雁嘖了聲,下意識往懷中去,“還能你的不?”
然后……沒有然后了。
他這才想起來,眼下的自己是個窮蛋。
攤主的笑容看上去已經不那麼真摯了,眼神中也漸漸堆滿懷疑。
外頭的雨越下越大,穿過叢林時發出的刷拉聲,仿佛也在肆意嘲笑:
窮蛋,窮蛋!
廖雁:“……”
攤主張了張,微微嘆了口氣,手腕一翻,就要把糖倒回去。
他娘的,本以為來了個大客,沒想到是個消遣人的窮鬼!
“慢著!”廖雁覺察到他的意圖,不有些惱,“誰說老子沒錢?”
說罷,他立刻扯開嗓子往遠喊道:“星星,過來付錢!”
說完,廖雁抱著胳膊,得意洋洋地向攤主。
就見那攤主看清過來的是個年輕姑娘后,非但沒有改變態度,反而過來的眼神中……同更濃了。
沒想到啊,還是個吃飯的。
“別攔我!撒手,老子要砍死他!”
一路上,廖雁都暴跳如雷地囂著。
白星沉默著,一手抓著裝滿豆糖的紙袋,一手鐵鉗般抓住他的肩膀,一言不發往車隊那邊走。
丟的人已經夠多了,非常不愿意繼續。
孟舉著傘迎上來,聞言忙道:“雁雁,不要難過。”
剛才他也大約聽見了事始末,因為覺得太丟人,所以沒好意思上前。
Advertisement
“呸!老子才不難過!”廖雁直接從地上蹦了起來,面紅耳赤道,“老子有的是錢!”
頓了頓,到底還有點良心,又著鼻子補充道:“經常!”
孟敷衍地點頭,“是,所以眼下,你不還是沒錢嗎?”
廖雁:“……老子砍死你!”
回到營地后,白星就撒手了,然后就見剛還囂要砍人的廖俠瞬間偃旗息鼓,開始蹲在角落吃起豆糖來。
這種豆糖是用麥芽糖加豆熬煮的,中間的字跡則是芝麻,兩種面團混合在一,經過拼接后做各種吉祥字眼的圖案。
三種原材料都很香甜,混在一起更為出,白星咬了一塊在口中,覺著它們在齒間緩慢融化的,微微瞇起眼睛。
他們三個是外地人,沒吃過倒也罷了,沒想到莊秀秀竟然也稀罕得,“這個真好吃!”
跟著的丫頭忍了又忍,聽到這里終于忍不住道:“也沒什麼稀奇的,街頭把戲,姑娘別吃多了,當心肚痛。”
這種糖齁甜又粘牙,曾有不孩無意中被粘掉大牙,吃得滿口,所以莊家人一直沒怎麼讓孩子接過。
莊秀秀不以為意地擺擺手,又拿了第二塊,結果才要開口,就發現自己開不開了!
“唔唔唔!”瞪圓的雙眼中充滿震驚,顯然已經覺察到兩排大牙之間粘的死的半融化糖果。
真是怕什麼來什麼,一掙扎,邊的丫頭婆子就都嚇得飛狗跳,又是掰著看,又是準備熱茶的,忙得不亦樂乎。
白星三人默默地退開一點,真心實意說了一句,“你好沒用啊!”
這里面加了大量豆,黏度已經大大降低,可饒是這麼著,莊秀秀竟然還能把自己粘住?
這要換了純麥芽糖還了得?
類似的事,他們也只在冬冬上看過了。
如此這般邊走邊玩,眾人足足花了五天才到目的地。
因比原計劃慢了不,莊秀秀就派了一個伙計先回去傳話,省的家人擔心。
在客棧休整一夜后,次日天還不亮,眾人就往九層高塔敢去。
白星和廖雁一直在江湖上討生活,早就習慣了隨時保持清醒,倒是孟和莊秀秀,兩人是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走在路上眼睛都睜不開。
“白姐姐,”莊秀秀把下墊在車窗上,努力睜著惺忪的睡眼問道,“為什麼這麼早出門啊?”
外出闖的夢還沒做完呢。
白星興致道:“之前聽人說起過,于江邊登高看日出,別有一番風味。”
曾看過無數次日出,也曾過無數次日落,但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更不是這般輕松愉快的心。
一切都不一樣了。
有了朋友,不是危機四伏的江湖,所以難免想像最尋常不過的游客一般,做點普通人游玩過程中會做的事。
他們這群人都不悉這一帶的路徑,所以還特意雇了個本地人帶路,那人聽后笑道:“是呢,這位姑娘是個懂行的,站在九層高塔上,日出日落都是極的。還有許多文人客專門來看,又寫游記又作詩的,那些個墻壁和柱子上啊,都寫滿了,每個兩年都要重新刷一遍呢!”
文人嘛,有事沒事都寫點兒,可地方就那麼點兒大,總會寫滿。
于是本地員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親自過來瞧瞧,若有出的詩篇文章就命人保留下來,不堪目的全部刷……
孟一聽,瞌睡去了大半,立刻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臉,“走走走,去瞧瞧!”
他雖不能科舉,但素來喜詩詞文章,如今既到了圣地,怎麼不用心觀一二?
于是眾人便加快速度,舉著火把黑爬塔。
越往前走,空氣中的水汽就越重,大家甚至已經能聽見深沉的咆哮,似一只蟄伏于黑暗的遠古巨,從管中發出驚雷般綿綿不絕的低吼。
是長江!
是翻滾奔騰的江水!
無人開口,可所有人都意識到了,于是腳步越發迅捷。
這一爬,力差異頓時暴無。
若不管眾人,白星和廖雁估計幾次呼吸的工夫就能翻上去,而力最差的莊秀秀,還沒到三層就開始雙打、汗如漿下,整個人累得跟熱水里撈出來一般。
好在帶的護衛隨從多,一干人番攙扶,好歹勘勘趕在晨曦突破地平線之前到了塔頂。
莊秀秀也顧不上什麼千金小姐的風范了,直接一屁蹲在地上,一時間竟是有出氣沒進氣。
“不,不行了……”頹然擺著雙手,雙目無神瞳孔渙散,整個人都要廢了,“我,我不行了……”
白星穩穩站著,臉不紅氣不,同道:“你得練練。”
莊秀秀已經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只是拼命點頭。
“看,太出來了!”
也不知是誰喊了一嗓子,眾人紛紛停下話頭,齊齊往東邊看去。
就見黎明漆黑的天際中,突然顯出來一紅。
那紅極細,卻也極耀眼,仿佛墨中驟然燒起的火線,又好似九重天上掉落的火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突出天際。
仿佛過了很久,又或許只是須臾一瞬,萬丈金重現人間,耀眼的芒用力穿黑暗,用力向未知的遠方展出去。
渾圓的日頭披五彩云霞,自地平線下緩緩升起,肆意揮灑金,漸漸映紅了穹窿。
東邊的天,亮起來了。
一直藏在影中的巍巍山巒、蜿蜒河道,甚至是那翻滾的長江水都漸漸顯在面前。
那長江多麼壯闊,迷蒙的水霧遮天蔽日,深黑的河水在微弱的晨曦下力翻滾、奔騰,晝夜不休,它們迎來無數人,又送走無數人,見證了悲歡離合,也目睹滄海桑田。
無人知曉那咆哮的河水究竟來自何,又將去往何地,但它依舊這麼流淌,如一條墜人間的巨龍。
河岸兩側是綿延不絕的群山,山上的翠濃到化不開,像天神無意中打翻的染料匣子。山巒之中中煙霧繚繞,偶爾有微風襲來,那些霧氣便好似仙們手中的薄紗一般,輕輕開,宛若仙境。
剛還喧鬧不已的九層高塔上安靜如夜,所有人都本能地屏住呼吸,貪婪地著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哪怕被刺激得雙目流淚也不肯眨眼。
呼吸間是積蓄了千年萬載的水汽和泥土芬芳,回在耳畔的是亙古不變的江水咆哮,在這一切面前,人類何其渺小,又何其卑微?
猜你喜歡
-
完結369 章

穿書養娃:農門棄婦有空間
成親當日,蘇珍珍喜轎未下就被休妻換人,由表姐替嫁,理由竟是她命格克夫! 娘家嫌她是麻煩,轉頭就要將她嫁給村裏的癡傻鰥夫。 蘇珍珍一哭二鬧三上吊,再醒來就變了個人,竟乖乖嫁了! 都說蘇珍珍是認命了,誰知之後的蘇珍珍令人大跌眼鏡。 繼母續弦不好當?蘇珍珍挽起袖子,孩子丈夫一手抓,賺錢養娃不耽誤。 日子淒慘不好過?藥圃空間在手,買田置地,小小棄婦二嫁後,反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財主。 極品親戚急了,拖兒帶女上門打秋風,蘇珍珍冷笑,不想死就趕緊滾! 數年後,癡傻鰥夫搖身一變,竟成了當今聖上的親皇叔,三個崽崽個個都是金疙瘩。 眾人吃瓜,什麽情況? 事情還沒完,蘇珍珍揮金如土在京都大殺四方之時,親娘卻找上門來? 蘇珍珍:「……」她親娘不早死了嗎,面前的這位貴婦人又是哪位。
55.9萬字8.18 98087 -
完結353 章

瘋批暴君被福運農女喊去種田
【共享空間+點雀鳥語+大數據】 她把那人從車廂里拉出來,那人把她拉進樹林,然後…… 周瑾玉看著空間裡一袋袋米麵和亂七八糟的物資,拎起一根臘腸,咬牙切齒問對面的小女子。 “你要去逃荒麼?我空間裡你就放這些?給我解釋一下!” 吃完一頓飽飯後 “真香!” 周瑾玉左手一隻喜鵲,右手一隻烏鴉,面帶戲謔的看她道: “以後你的消息也要跟本王共享!” 崔佳雲……馬甲什麼時候掉的? “消息?什麼消息,呵呵我只是個小農女,真噠!” 眾人:……信你個鬼!
58.9萬字8 20374 -
完結590 章

攝政王的末世小農妃
末世女王莊雲黛一朝穿越,成了山村破屋中快要病死的傻女。親爹戰死,親娘遺棄,極品親戚將她跟弟弟妹妹趕到破屋中想把她熬死。莊雲黛當即擼起袖子決定就是乾!原本她只想在古代當個普普通通的女首富,卻沒想到一眼見到在採石場被拘為苦役的他,當場就決定把他認作老公!陸霽青一朝從雲霄之上墜落,成了採石場的苦役,遇到一女子熱情的邀請他當面首。最初,陸霽青:離我遠點!最後,陸霽青:別走!
106.1萬字8.18 205474 -
完結650 章

下堂棄妃要休夫
葉鳳頃穿越成又蠢又癡又慫的葉家二小姐,大婚之夜被人打死,給王爺下藥、被欺負不還手、抱著藥罐子老媽,窮的丁當響,這特麼是人過的日子?為了吃飽飯,葉鳳頃決定遠離渣男,好好種田! 誰知道狗王爺竟纏上她,屢教不改,葉鳳頃拿著包袱相求:王爺,求放過!
114.6萬字8 53227 -
完結625 章

穿書后我成了三個反派的惡毒后娘
季知歡從特工組S級成員,穿書成了死于第三章的炮灰女配,嫁給活死人前戰神裴淵,還成了三個未來反派的后娘。而自己就是三反派的黑化第一步,間接導致了他們長大后下場凄慘,死無全尸,挫骨揚灰!季知歡表示拒絕被安排狗血人生,要做就做原劇情里最大的Bug!好在她空間在手,技能全有,斗渣渣,撕極品!種田養娃,賺錢養家,天要亡我,我便逆了這天。后來,從小沉默寡言的大兒子成了當朝天子,大力金剛二女兒成了最彪悍的第一女將平西侯,連那小兒子也成了百毒不侵的絕代毒醫。季知歡覺得自己美女無用武之地了,然而卻被令朝野聞風喪膽的...
111.5萬字8.18 175266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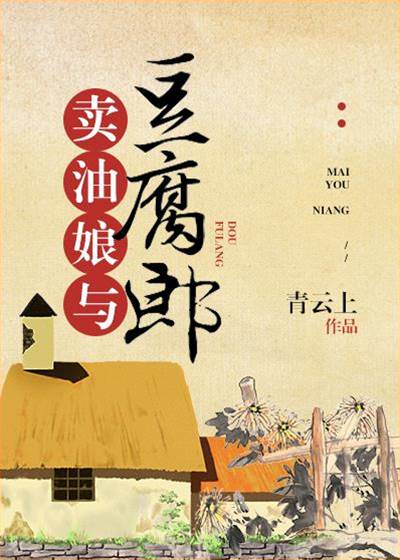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1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