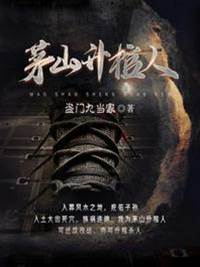《死人經》 第26章 習武
顧慎為當天就留下跟雪娘學習武功,兩人不是師徒,也不是朋友,卻是一個教得認真,一個學得刻苦。
顧慎為心里非常清楚,雪娘與小姐的目標不會只是為金鵬堡提供殺手學徒,們牢牢握住他的把柄,當然另有所圖,但是在們開口提出最后要求之前,他會擁有暫時的安全。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組合,顧慎為自稱“楊歡”,復仇的矛頭很可能指向八主上怒,為八的羅寧茶竟然不以為意,雪娘也沒有深究,輕易就相信了這套說辭,而他,一名心懷殺機的殺年,卻要依靠兩位心懷鬼胎的的人保證自安全。
還有一件事出乎顧慎為的意料,跟著雪娘習武的不只他一個人。
金鵬堡對奴的命名方式與男仆差不多,也是從《千字文》當中選一個字,唯一的區別是后面綴的字是“”。
跟顧慎為一塊習武的人荷,也是“大頭神”攔路買來的十名之一。
這是一名沉默寡言的,如果不是神過于嚴肅的話,可稱得上是,總是一副沉思默想的模樣,對周圍的一切事都心存警惕,尤其注意傾聽雪娘的每一句話、觀察雪娘的每一個作。
從雪娘的角度來看,荷是一名優秀的弟子。
顧慎為從來沒聽遙奴提起過,對那個喜歡夸夸其談的尖臉年來說,這是極為罕見的行為。
雪娘傳授武功的方法跟顧家完全不一樣,第一天,一招也沒演示,就讓男兩名“弟子”對打,不是點到為止,而是傾力而戰。
顧慎為第一招就被突如其來的一腳踢倒,這才明白荷是真格的,也明白了遙奴此前經常傷是怎麼回事了。
Advertisement
荷沒有武基,全憑著良好的悟與一子狠勁兒,才在幾十天的時間里跟隨雪娘練就一拳腳,顧慎為開始還想藏實力,最后卻要使出渾解數,將第一層“合和勁”全都發揮出來,才能勉強打平手。
荷本沒有修習過功,只是臨戰經驗比顧慎為富得多。
只對練了不到半個時辰,顧慎為就已經大汗漓淋,丹田氣息翻涌,竟似有不支之意。
雪娘在一旁隨時指點,但是大多是針對荷,對第一天留下的歡奴,直到最后才給出建議,或者說是命令:
“忘掉你學的破爛拳,練好你的功。要想進東堡,并且活著為殺手,你得重頭練起。”
那天下午,雪娘去服侍小姐,讓荷教歡奴“伏虎拳”。
打不過與自己同齡的,就夠沒面子的了,還要跟一招一式地學習拳,更是令顧慎為無地自容,尤其是荷態度冷漠,一句話也不多說,像是極不愿的樣子。
不過,傍晚回到“積薪院”之后,顧慎為領略到的又是一番想不到的待遇。
新院管第一次主和歡奴說話,還鼓勵了他幾句,告訴他以后不用再管院里的傷者了。
另外五名年也掛著尷尬的笑容,迎接“結拜兄弟”的歸來,累奴甚至幫他撣了撣上的尖土,態度變化之大,令顧慎為一時間竟有點接不了。
他重點關注的還是遣奴,遣奴一如既往,雖然也來示好,但是話不多,往往在將要冷場的時候說出一句,給人一種覺,好象他是小團的帶頭人。
顧慎為決定將白絹的事暫時放下,他要專心學武,既為了進東堡當殺手學徒,也是為了討好那兩個人。
Advertisement
金鵬堡好像一座金剛巨山,遠堅不可摧,靠近觀察卻能見到細小的裂痕,顧慎為已經到了幾條,但是對于報仇大業還遠遠不夠,他要繼續深,直到所有裂痕的匯。
顧慎為現在可以明正大的練習武功了,除了吃飯睡覺,他將幾乎全部時間都用來練武,即使從雪娘那里回來,他也要去鬼崖修行“合和勁”,他要把浪費掉的十來年時全都追回來。
雪娘迫切希將要推薦的兩名年能在東堡出類拔萃,所以督導極為嚴厲,甚至手歡奴的功修練,這也是怕遙奴的悲劇重演。
雪娘可不像顧侖,傳授功時循序漸進求穩不求快,近乎是以暴力手段推歡奴提升力,顧慎為每天都要在面前練一次“合和勁”,則時不時在他上一指,每下都命中不同位,輸一霸道的熱氣,幫助他打通經脈。
這對修練功自然大有益,可是也痛苦萬分,沒幾天,顧慎為就已全遍布青淤,晚上睡覺時都找不到舒服的姿勢。
與荷的每日對練更是痛上加痛,這個沉默的對歡奴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莫名的嫉恨,等到雪娘單獨幫助他修練功,更令將同門年視若仇敵。
顧慎為還從來沒被人這麼痛恨過,他對此非常茫然,隨之而來的是一惱怒和不服氣,他想要過荷。
學習伏虎拳時,這一目標很難實現,顧慎為本來就不怎麼擅長拳腳功夫,雪娘門下又比荷晚了近兩個月,但是十天之后雪娘傳授刀法時,況就不一樣了。
東堡每年一次招收新學徒的日期已然臨近,雪娘為了趕進度,必須在短時間傳授盡可能多的武功,提醒歡奴與荷:
Advertisement
“練武之人,拳腳是基,輕健,再學其它兵自然水到渠,可是拳腳也只是基,不要指用它與人爭斗,無論你的拳腳功夫有多好,握著一把利刃只會讓你更強。有人赤手空拳打敗刀槍劍戟,那是因為雙方實力差距太大,而不是拳腳勝過了兵。記住,你要當一名殺手,以殺人為業,你的對手不是由你選擇,而是由主顧指定,所以,你千萬不要想著以拳勝刀,只有以刀勝刀,以刀勝拳。”
雪娘自己練的是鐵指功夫,與的這番理論不大適合,可不是殺手,也不想當殺手,而且常年在深宅大院中服侍小姐,的確不怎麼需要刀劍。
顧慎為對家傳刀法爛于心,但他已經說過自己學得不到家,所以刻意藏,好在雪娘也不在意,傳授的是實戰刀法,沒有固定套路,共是一十八勢,每勢都很簡單,或劈或砍或刺或格,殊變化,但是練之后,雪娘要求兩人自行將十八勢組合,又演變出無數新招來。
雪娘說這套刀法是“鐵山刀法”,是鐵山匪幫賴以縱橫大漠的武功之一。
顧慎為覺得“鐵山刀法”不如自家刀法妙,但勝在易學好懂變化多端,他偶爾在組合一十八勢時加一兩招顧家刀法,竟也大有益。
對荷來說這卻是一道難關,在此之前,連真正的刀都沒拿過,是悉握刀姿勢和用力方法就用了好幾天,因此在對打中,遠遠落后,有時差距太大,雪娘不得不親自場與歡奴對陣。
荷因此變得更加沉默郁,顧慎為每次來都看見已經在練刀,走的時候仍然刀不離手。
顧慎為的“合和勁”進展也很神速,一個月過去,他連闖兩送,二勁都達到了第二層。
Advertisement
自從進金鵬堡以來,顧慎為從來沒覺這麼好過,報仇的信心也大為增加,雖然他現在離最終目標還隔著千山萬水,但是他已經能見那座最高的山峰,他要為最強的殺手,再向殺手們復仇。
“大頭神”的兒無聊的時候會來看雪娘傳授武功,當然還是要隔著屏風,在鐵山時的許多習慣都被迫放棄了,只有這一條越發堅持,不僅丈夫以外的男人止看,就連堡一般婦也看不到的真容。
據說小姐每天向婆婆請安時也要戴著好幾層面紗,這也就不難理解,婆媳之間的關系為何如此惡劣了。
顧慎為與荷練“鐵山刀法”時,小姐有時會點評幾句,“稱心遂意”那四名丫環就會借著話頭跟小姐一塊回憶從前的快樂時。
從這些羅里羅嗦的回憶中,顧慎為發現小姐一點武功也不會,“鐵山”也不是真實的地名,匪幫營地扎在哪,哪就“鐵山”,雪娘也不是貨真價實的娘,在小姐幾歲時才加匪幫。
東堡招收殺手學徒的那一天剛好秋,頭天晚上降下當年的第一場霜,天空沉,絕峰之上的空氣卻很清新。
雪娘親自帶著歡奴與荷前往東堡,堡建筑眾多,巷路縱橫,宛如迷宮,若不是有人帶領,外人寸步難行。
進堡時間也不太長,雪娘就對復雜的路徑了若指掌,顧慎為對此并不意外。
東堡和西堡一樣,也有數不清的院落,雪娘帶兩人進了一座很小的院子,和金鵬堡許多地方一樣,歷經百年風雨的小院已有破敗之象,但是長桌后面的記名先生卻保持著威嚴,讓人覺得,金鵬堡的實力在人不在房屋。
記名先生抬頭看了一眼來者,這是第一撥新學徒,他的簿子上還沒有留下墨跡。
“哪個院的?”
“八主。”
“姓名。”
“荷。”
……
記名先生發問,容繁雜,連學過哪些武功都一一記錄在冊,問題全是雪娘代答,顧慎為與荷只需要在一旁靜靜等待。
一切順利,荷為今年第一名記錄在案的殺手學徒。
這時又來了兩三撥新學徒,小院里顯得有點擁。
到顧慎為,本來一切也很順利,歡奴的名字已經寫在簿子上,只差最后幾項,問到所學武功時卻出了紕。
“他學過功?”
“嗯,學了一點門功法。”還是雪娘替他回答,眉頭微微皺了起來。
記名先生低下頭,將簿子上“歡奴”名下的記錄一一劃掉,然后抬起頭,說:
“他不能進東堡。”
猜你喜歡
-
完結1218 章

死人經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人鬼不誅,神得而誅之。 一本死人經,半部無道書。 斬盡千人頭,啖吞百身骨。 你要么忍受世界的不公,要么成為世界的主宰。 他選擇成為殺手,和仇人一樣的殺手,但是更加冷酷更無情。 刀光劍影中,他要尋求真理——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338.9萬字8 8054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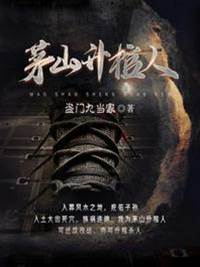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5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