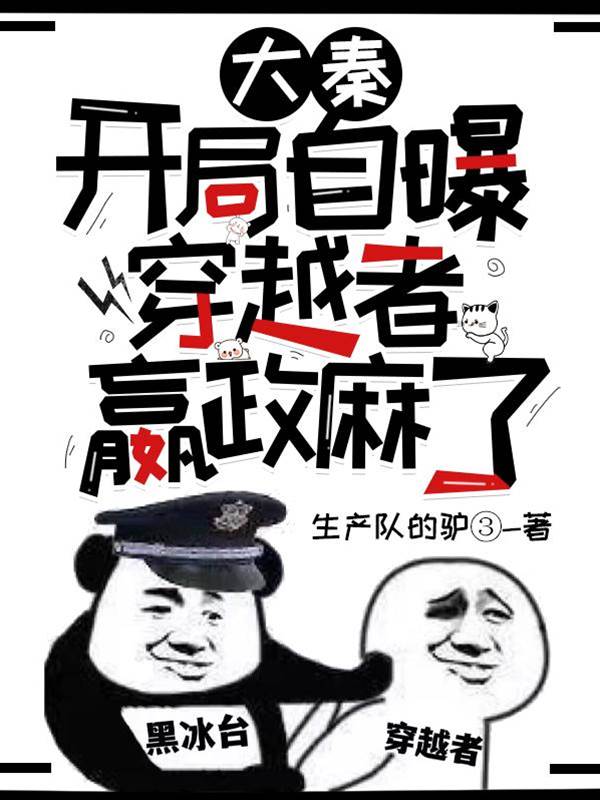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我見殿下少年時》 第14章
許昭儀想準備什麽賀禮,還要先打聽打聽三皇子跟誰關系好,和誰走的頻繁麽?
難不還打算送個大變活人?
高悅行不願意再繼續蹩腳的虛與委蛇,也急,皇上殺心已定,聖旨一下,李弗襄困在那個地方就是死路一條,時間來不及了,沒有徐徐圖之的機會了,再等,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死,倘若還想爭取點什麽,必須放開手腳賭這一局。
上一世,許昭儀故去之後,李弗襄一直把的畫像珍藏在書房。
于是,高悅行選擇相信李弗襄的這位“生母”。
這一局,賭上的是和李弗襄兩個人的命,抉擇的痛苦一陣陣頂著的口疼。想起了李弗襄小院裏那致的火盆和銀碳,無一不昭示著那人尊貴的份,的最後一希都牽在那上頭了。
高悅行認真回想,如實回答:“除了隨伺候的奴才,似乎沒見他和誰走頻繁。”
許昭儀急死了,逐漸失去耐心,親自走下主位遞了一塊桂花糖給:“高小姐再仔細想想?”
高悅行著黏糊糊的糖,反手抓住了許昭儀正準備回去的袖子。
許昭儀不解地著。
高悅行向前傾斜子,們的距離得非常近。
許昭儀袖中那馥郁的熏香順著的嗅覺直鑽腦門。
高悅行覺得這可能就是令暫時頭腦發昏的原因之一。
“許娘娘。”高悅行用只有們倆才能聽清的聲音道:“我們明人不說暗話,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訴你,我不知道的,也可以想辦法替你去查。”
許昭儀僵在原地忘了作,驚愕的看著。
高悅行黑白分明的眼珠尚未完全去稚氣,正因如此,才尤為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許昭儀也在賭。
幾乎是當即下了決斷。
Advertisement
誰不知道與虎謀皮危險,若非不得已,誰又願意自己主跳進火坑。
許昭儀的袖在小幅度的抖。
這是易。
許昭儀竭力穩住自己的聲線:“你想要什麽?”
高悅行道:“真相。”抓著許昭儀袖的手指骨節幾乎泛出了青白,說:“你曾是鄭皇貴妃邊侍奉的人,有關小南閣,沒有人比你知道得更詳細了。”
小南閣。
又是小南閣。
繞來繞去,似乎宮裏所有不同尋常的事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
許昭儀此時算是豁出所有,不怒反笑:“你敢去皇上的逆鱗?你高家上下多人頭夠給皇上砍啊?”
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六歲的小孩子會摻和進當年的驚天巨案。
他們所有人第一時間考慮的,都是背後的家族,高氏。
高悅行此前還沒相通這節關竅,經許昭儀無意中的一點撥,高悅行眼前霎時雲開見月。
有時行走在高高的宮牆,心裏也會彷徨,并不想連累家族,可終究是高氏,無論做什麽,都撇不開高氏,無論結果如何,高氏全族要麽共榮要麽同罪。
許昭儀盯著,自己也迷不已,喃喃自語:“……怎麽高氏也攪合進來了?”
高悅行閉了閉眼,深淵在側,已容不得有半步差池,說:“皇室脈存疑、江山不顧,家父食君俸祿為人臣子,理應有所作為……”
高悅行一字一句說得艱難。
許昭儀聽著,神卻變的怔忪,繼而出了喜:
——“什麽?你父親是怎麽知道三皇子份存疑的?朝臣還有誰知?陛下呢?陛下也起疑了嗎?”
果然……
高悅行在慶幸自己賭對了的同時,拿穩紫檀,平靜地回答:“陛下不知。”
許昭儀的表暫時凝固,心大起大落,堪比一盆涼水澆在火上。
Advertisement
高悅行不能讓的餘燼涼,嘗試著讓重新燃起希:“許娘娘,單憑一張沒用,我們辦事需要證據。”
許昭儀:“對,你說的對,我怎麽糊塗了,證據……”
放開高悅行。
那一小塊桂花糖在兩人的手裏,已經被地融化、發黏,高悅行低頭盯著那糖,靜默了一會兒,忽然一松手,任由它掉在自己幹淨的子上。
許昭儀已經恢複了冷靜,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揮手,來門外伺候的人,坦道:“高小姐的服髒了,服侍高小姐到室沐浴更。”
高悅行正大明地進了綺閣的室,服侍的宮是許昭儀的心腹。
許昭儀撥開紗帳,把宮打發到外門守著,急不可耐地去牽高悅行的手:“好孩子,難為你了……高大人是因為在宮外,鞭長莫及,所以才安排你進宮的吧。”
高悅行擡出了父親,于是一切的不合理,都變了事出有因。
哪怕還有些其他疏,許昭儀自己就可以幫圓上。
高悅行就坡下驢:“是。只是……當年的事太過,相關人等死的死,逃的逃,僅剩幾個知人,也都有各自的難,三緘其口。家父即使有所懷疑,也始終不得其解。想重翻舊案,太難了。”
許昭儀:“我說,我都告訴你……你說得沒錯,當年事,沒有人知道得比我更詳細了。”
當著高悅行的面,許昭儀飛快地回憶十年前。
其實本不用回憶。
那夜的事刻在的記憶裏,十年了,從不曾淡忘,夢裏都是鄭雲鈎的音容。
“我在西北邊境就跟著皇貴妃了,我出生在那邊偏僻的鎮子,十歲就被家人賣了換米,淪落奴隸,關在集市上的木籠子裏,等人買走。皇貴妃那日路過集市,可憐我年紀小,出錢買了我,從此,我再也沒有離開。”
Advertisement
“後來,進宮,我也跟著。想給我選個好人家出嫁,我不肯。我本沒打算嫁人,因為那樣就要離開邊。皇貴妃不忍見我孤老此生,于是讓皇帝納了我,并勸我,就算沒有喜歡的人,至也養個孩子在膝下。”
高悅行:“皇貴妃難産而死,我聽說,皇上是因你照顧不周,才遷怒于你。”
許昭儀低頭:“我卻是照顧不周,以至于讓人鑽了空子……但皇貴妃的死,說到底,其實是早産。”
意料之中。
果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巧合。
高悅行:“早産的原因是什麽?”
許昭儀贊了一句:“你問到關鍵了。皇上也知道皇貴妃的産期不對,當晚就派人嚴查,最後查到的結果是——皇貴妃誤喝了我的避子湯。”說到這,許昭儀再也不下眼中的殺氣:“而那碗湯,正是經我手,遞到了皇貴妃面前。”
高悅行靜等下言。
許昭儀說:“我有幾回侍寢時,正趕上皇貴妃孕期子不方便,我便給自己備了避子湯,可人算不如天算,即使我已經很小心了,還是不慎懷上了孩子。我發現自己有了子,于是立即停止了服藥,那碗避子湯本不可能出現在貴妃宮裏。”
算算時間。
五皇子今年九歲,許昭儀沒說謊,懷孕的時間,與皇貴妃的孕期剛好有段重合。
許昭儀終忍不住落下淚:“我之前從太醫院拿的避子湯還有剩餘,存在小倉庫裏,被近衛搜出來,當做我害人的證據,我百口莫辯……皇貴妃撐著最後一口氣,對皇上說,相信我,懇請皇上不要責難我。”
從明面上看,證據確鑿。
只要皇上信了,便可就此結案。
許昭儀道:“那天晚上太了,到我本來不及細琢磨,接著,貴妃薨了,差點要了我半條命,皇上要殺要剮我不在意,讓我殉葬我也是肯的,但皇貴妃是人所害,真正的兇手金蟬殼逍遙法外,真相不查,我死不瞑目。”
Advertisement
高悅行問:“那你查到什麽了?”
許昭儀靜默片刻,長嘆一聲:“我若是能查出有用的證據,早就呈到皇上面前了……我無能,皇貴妃死後很長一段時間,我把自己困在憤恨裏,卻什麽也查不出來。”
高悅行:“但你必定有所懷疑。”
許昭儀:“沒錯,轉機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兒因功課不好,惹皇上生氣,被罰在文華殿的書房反省到半夜,我放心不下,便去瞧他,回來的路上,途徑小南閣,恰好見三皇子。我那天穿得比較素淨,邊也沒帶任何伺候的人,忽然出現在三皇子面前,可能嚇到他了,他誤以為我是什麽不幹淨的東西……”
說得很委婉。
所謂不幹淨的東西,無非是傳說中的鬼魅魍魎。
許昭儀表變得耐人尋味:“你猜,三皇子當時做什麽反應?”
三年前,三皇子七歲吧。
小孩子見了鬼能有什麽反應。
高悅行:“嚇哭?跑掉?”
許昭儀搖頭:“你猜都猜不到,三皇子他啊,站在原地愣了一會兒,居然追上來喊我娘。可不可笑啊,堂堂皇子,盛寵的皇子,皇貴妃的兒子,半夜不睡覺,獨自跑到地附近轉悠,還追著一個鬼喊娘!”
說著,許昭儀開始笑,笑得有些癲狂可怖。
華貴的珠飾淩在的耳側。
含淚帶笑,神倒真的有點嚇人了。
高悅行:“許娘娘!”
猜你喜歡
-
完結1106 章

諸天福運
公府庶子的強者之路!被限制在后宅只能當小透明怎麼破?剛剛到叛逆年紀就被勾著往紈绔上走怎麼破?初一成年就被親爹扔到塞外領地自生自滅怎麼破?正趕上靈氣復蘇天地異變……幸好哥們有金手指福運寶塔!穿梭諸天強大自身,一切阻礙都是浮云!
263.3萬字8 25504 -
完結118 章

我給男主當嫂嫂
——今天你把我當替身,明天我給你當嫂嫂。 慕明棠是大男主文里的白月光替身,她家破人亡,被蔣家收養,后來代替失蹤的白月光和男主晉王訂婚。 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替身,所以打斷爪牙,活成晉王想象中白月光的模樣。她不敢說不敢笑,安分守己當另一個女人的影子,直到有一天,真正的蔣大小姐回來了。 正主蔣大小姐重生,得知自己原來是男主的白月光,立刻回來奪婚約奪身份。晉王為了討好白月光,將替身慕明棠送給已成了活死人的岐陽王。反正只是一個拙劣的替代品,敢惹正主生氣,自然要讓其無子無女,無依無靠,守一輩子活寡。 被嘲笑為爛泥扶不上墻的慕明棠徹底爆發:好啊,你將我送給別的男人,我這就讓你改口叫嫂嫂。 恐怕他們誰都沒有想到,殺神岐陽王竟然醒來了吧。
46.5萬字8.47 44635 -
完結1681 章

我用閑書成圣人
開局一口棺材。 陳洛的穿越從靈堂開始。 這是一個讀書就能獲得超凡威力的世界。 讀儒門經典,可養浩然正氣; 讀道門典藏,可生先天源炁; 讀佛門經文,可悟輪迴真意; 偏偏陳洛的金手指卻是一堆天道都不允許在這個世界出現的閒書! …… 什麼? 《聊齋》被妖國當做天書? 什麼? 《天龍八部》打開了武學天地? 別慌別慌,都是小場面! 這位儒生,虎將如雲、謀臣如雨的《三國演義》聽過嗎? 那位道士,《封神演義》看過沒有?你們道家在裡面老牛了! 哎,高僧請留步,我這裡還有一本《西遊記》,你感興趣嗎? …… 經史子集天上道,說書演義人間貌。 你煉陽神他修佛,紅塵有我向天笑。
562.1萬字8 32741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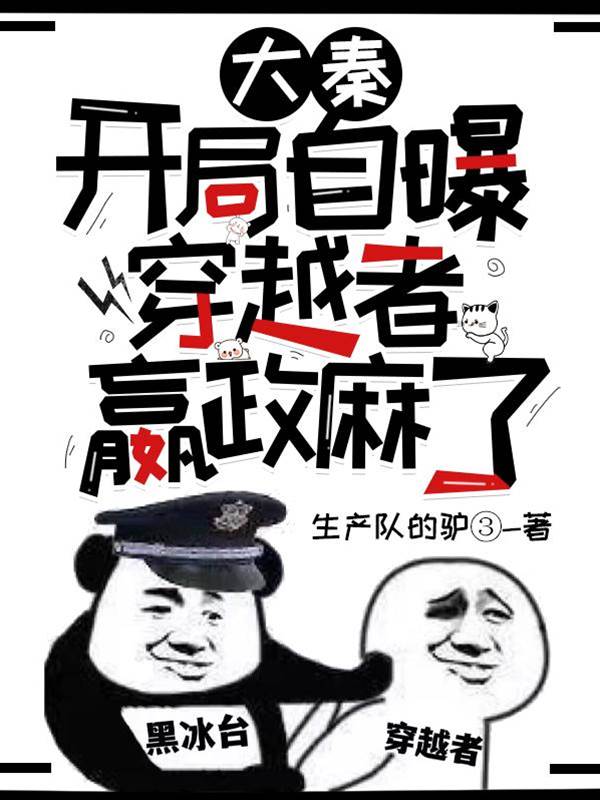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