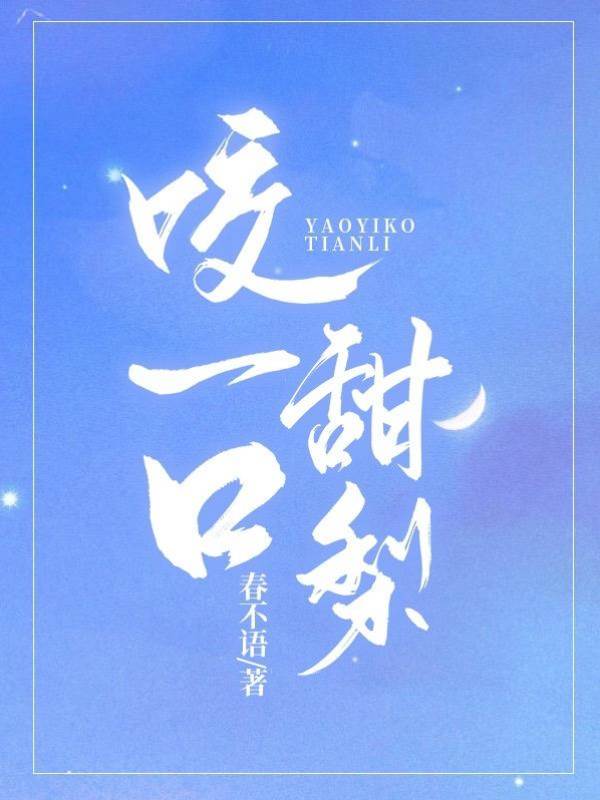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薄總別虐了,今天是夫人葬禮》 第445章 還是想離婚嗎
霍啟東略顯蒼白的臉上出運籌帷幄的笑意。
“嚴城,給你歸給你,至于霍家這些老骨干,能不能調度得,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話說到這一步,薄嚴城心里已經明白了。
就算霍啟東承認他是霍家的婿,但畢竟溫晚梔才是正統的繼承人。
他就算再有能力,也不能完全越俎代庖。
溫晚梔還在鎖眉思考著,不知不覺,整個人都窩在了薄嚴城膝彎里。
發頂茸茸的發掃在男人下上,卻毫沒察覺后人的不自在。
咚咚——
一陣敲門聲打破沉寂,病房門外傳來護士的聲音。
“霍先生,查房。”
霍啟東應了聲“稍等。”
中年男人靠近手機屏幕,神有些憂慮,正囑咐著。
“我能做的非常有限,事就給你們了。晚梔,記得,你心,不是壞事。但一旦決定出手,就別再給對方和你對簿公堂的機會。明白了嗎?”
溫晚梔也神一冷,認真點點頭“爸,我懂。”
死過一次,早已經看了這一切。
心,只適合留給尚有人的人。
而面對的,是早已泯滅人的惡鬼。
溫晚梔掛斷視頻電話,心里平靜了不。
剛才霍啟東把霍家資源的調度權給薄嚴城的那一刻,心里一涼。
Advertisement
不喜歡那種置事外的覺,尤其是被最親近的人排除在外。
無論是出于保護的意圖,還是因為無法依賴的實力,都難以接。
但霍啟東話說得委婉,溫晚梔卻明白了。
沒有的出面,霍家人也不會全聽薄嚴城的。
這是表面上架空了,實則給減輕了不負擔。
溫晚梔輕輕笑了笑。
原來霍啟東和天下任何一個最普通的父親都一樣。
不再那麼
擔心霍啟東的傷勢,溫晚梔突然有點犯困。
不知道是喝了熱巧克力的原因,還是繃著的弦終于松了下來,周暖烘烘的,眼皮開始打架。
聽到懷里的人發出均勻的呼吸聲,薄嚴城都不敢一下。
垂眸看向溫晚梔閉的眼,纖長濃的睫在眼下打下一片小小的影。
小巧的鼻子下面是輕輕抿著的兩片,淡得幾乎蒼白。
薄嚴城心里泛起刺痛,太累了。
即使已經可以心無芥地靠在他懷里睡著,但一雙細白的手臂還是戒備地抱著自己,似乎沒什麼安全。
薄嚴城苦笑著移開視線。
人果然都是貪婪的。
他明明想著,幫溫晚梔完復仇,自己就放離開。
可有了溫暮和薄林,他似乎變得,越來越貪心。
Advertisement
他妄想著,重新組建一個兩人曾經夢想過的家庭。
他甚至開始有了,重新擁有溫晚梔的念頭。
殊不知,每一個他看似淡然從容的時刻,心都在激烈戰著。
溫暖的夕漸漸散去,夜幕降臨,溫度稍微降了下來。
溫晚梔睡得安心,了,低聲哼哼了幾聲。
薄嚴城呼吸一窒,拳頭攥,結滾了幾下。
暖玉溫香在懷,還蹭來蹭去,他畢竟是個正常男人……
薄嚴城一邊子已經麻了,另一邊舉著案件材料在讀,三行字已經讀了八百遍。
讀著讀著,每個字都變了最悉的三個字。
溫晚梔。
薄嚴城淡淡笑了笑,低頭輕輕吻了吻懷里人
的發頂,心里快被暖暖的意撐破。
他不應該再害怕去。
第一縷晨照進屋子的時候,溫晚梔似乎醒了過來,卻不想睜眼。
自從焦慮復發以來,難得睡了個很漫長的好覺。
按理說,這樣的好覺,應該配著一個好夢。
可什麼都沒有夢到,一夜無夢,難得平靜。
雖然已經覺到是早上了,但溫晚梔還是不想從這樣的舒適中太早醒來。
反正是周末,再睡一會兒也沒什麼吧……
懷里的人不過變了變呼吸的頻率,薄嚴城就微微睜開了眼,醒了過來。
Advertisement
他小心翼翼地側躺在沙發上,子圈住溫晚梔,把牢牢護在靠背和自己前,蓋上溫暖的牛羊絨毯。
這一夜過去,他似乎覺不到自己上的酸痛。
懷里護著睡的溫晚梔,似乎從來沒有這麼安心過。
如果這一刻永遠不會結束就好了,甚至,他愿意就這樣死在這一刻。
日上三竿,溫晚梔有些熱,手掀開了上的被子,卻被一只手很快蓋了回去。
有些煩躁,這才不不愿地了子,閉著眼了個懶腰。
拳頭似乎打到了什麼東西,耳邊是一聲低沉的悶哼。
“唔。”
溫晚梔猛地睜眼,就看到捂著下,一臉吃痛的薄嚴城。
臉一紅,溫晚梔剛要掙扎著起,卻被一只壯的手臂箍進懷里。
“別。”
溫晚梔被薄嚴城的溫燙得一,低聲開口“我,我要起床了……”
薄嚴城聲音喑啞得很,手臂了,熱氣拂過溫晚梔的耳側,引得輕。
“好,等一會兒就起床,好嗎……”
溫晚梔呼吸都變得有些
急促,剛要扭著子手推他,卻被什麼頂的作一滯,馬上沒了作,連呼吸都小心翼翼的。
薄嚴城看到懷里人老實了,沒忍住低笑出聲,聲音寵溺“怎麼不掙扎了?”
Advertisement
溫晚梔臉一紅,聲音蚊子似的。
“你現在不好起……”
薄嚴城喟嘆一聲,嗓音似乎又喑啞了幾分。
“嗯,陪我隨便聊聊天吧。”
溫晚梔點點頭,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口聊著。
“薄嚴城,我昨晚吃藥了嗎?”
男人淡淡嗯了一聲“吃過,晚飯后。”
溫晚梔想了想“今天幾號了,距離孩子們的學測試還有多久?”
薄嚴城幾乎不假思索,自然接過了話“十天,三天后應該是最后一次模擬賽。”
溫晚梔心里暖暖的,薄嚴城似乎真的變了,細心,,比從前更甚。
而且半夢半醒,在晨起的中掙扎的男人,難得懵懵的,似乎有問必答。
溫晚梔起了些玩心,眼珠一轉,低聲開口問。
“理掉王彪和霍玫,你打算做什麼?”
薄嚴城像是又來了困意,聲音更輕了些。
“順手收拾了薄彥真和薄遠。”
男人像一頭卸下防備的獅子,在自己的領地里,對伴毫不設防。
溫晚梔臉上的笑意收斂了幾分,低聲認真問著。
“那……我們什麼時候離婚?”
薄嚴城閉著眼,眉頭蹙起,難得有些焦急。
“不離婚了!”
似乎被這個問題驚醒了,男人終于回過了神,腔起伏著,心跳都猛地加快了速度。
薄嚴城認真看著懷里的溫晚梔,聲音干的,猶豫著。
“晚梔,你……還是想離婚嗎?”
猜你喜歡
-
完結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31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9340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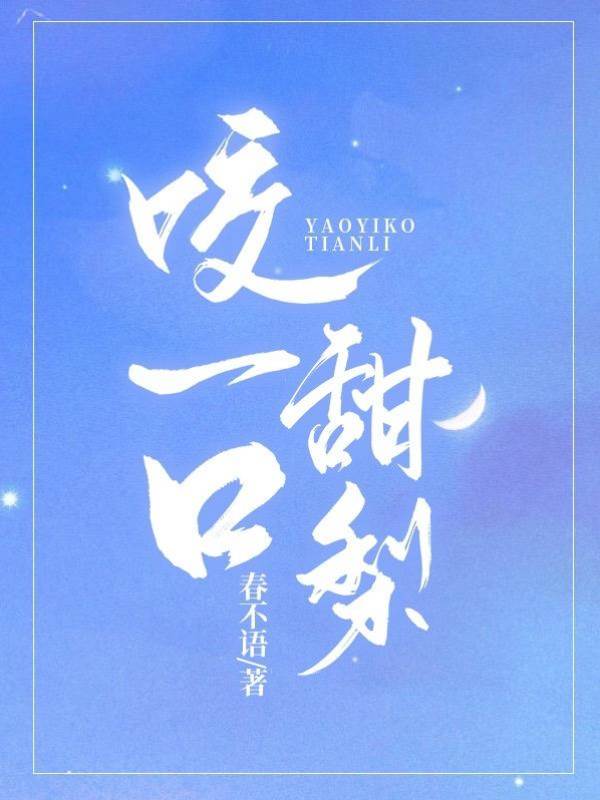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6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