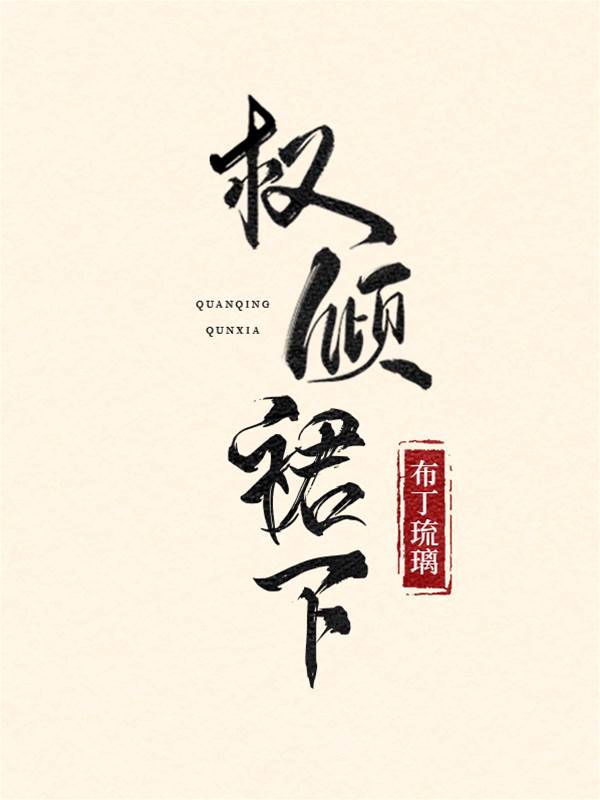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二十二章 膽敢對本將軍無禮
姜姒停了手,出神地向窗外那棵繁茂的梨樹,在月華下杳然岑寂。離開東宮的這些時日,那葳蕤的枝葉越發將院落遮了個嚴實,大把大把的白花飄飄轉轉往下跌去,若不仔細看,恍然還以為是人在墜樓。
的眉頭輕輕蹙起,眸黯然,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半晌方道,“不記得了。”
白芙絳開了又闔,似是要說什麼話,終是什麼都沒說。
又聽姜姒喃喃自語道,“五歲前的事,已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母親著華麗,死在我眼前。”
“的眼神似是很絕,我看著的時候,到已經支離破碎。”姜姒棄了茶筅,扶住額頭,一時悲從中來,朱輕,生生地忍住眼淚。
良久,白芙才過來抱住,輕輕拍姜姒的削肩薄背,眼里的緒十分復雜,“姜姒,你的心是干凈的。”
“我不及你。”
*
許鶴儀負重傷回東宮,那些朝廷僚太子賓客們自翌日下了早朝開始便絡繹不絕地登門探。
許鶴儀因子不適,著人一一婉拒了。
大將軍趙世奕卻堅持要進東宮面見太子。
趙世奕是太子妃的父親,太子妃雖了責罰形同,但趙世奕畢竟還是太子岳丈。因而當他著了盔甲又拉著一張富態臉刀立在徐安跟前時,徐安只得再去重華殿稟報。
到了重華殿,趙世奕行了跪拜大禮,寒暄一番后,許鶴儀便賜了他一方席。說起了甘州的軍,那支白蛇教如今在西北益發猖獗,已形氣候。若不及時鏟除,只怕影響朝廷基。今日一大早又有軍傳來,說西南滇桂一帶也有人打著白蛇教的名義起事。乾朝立國不過十年,基尚未穩固,務必及早清除白蛇教才是。
Advertisement
只是,許鶴儀此次去甘州暗中查訪,發現這子勢力組織嚴,又極善于藏。他們從不與朝廷的軍隊正面沖突,往往是干了一票便匿起來。神出鬼沒,十分難纏,頗是令人頭疼。
陛下便有意派趙世奕去甘州平定匪患,臨行前,他來東宮討個主意。言及許鶴儀此次傷,也猜測是燕王許之洐派人追殺。
“陛下已派人去燕國查實燕王的行蹤,若燕王未經允準,私自離開封國,陛下必要問罪。”
趙世奕說著話,便劇烈咳嗽起來。
“將軍可是子不適?”許鶴儀問道。
“哦......”趙世奕一邊咳一邊說道,“近日時常干咳,若飲點涼茶便會好許多。”
忽又似突然想起來,問道,“咦?殿下邊一直侍奉的那姜姑娘,聽說點茶手藝甚好,不如請來。”
許鶴儀聞言,便也溫聲吩咐下去,“徐安,請阿姒來。”
白芙是一定要與姜姒在一的,聽徐安說起大將軍要請姜姒點茶,自然要跟著姜姒一起。徐安覺得似也沒有什麼不妥,便也默許了。
進了重華殿,給許鶴儀與趙世奕行了禮,姜姒與白芙便跪坐案前點茶。白芙雖不會,只坐在一側偶爾打個下手。兩人俱是絕,一個仙姿清雋,一個艷無雙,落進眸中,已是一場春日盛景。細細看去,眉梢眼角間,竟有幾分相像。
碎茶、碾茶、籮茶、撮末于盞、注湯盞,最需耐心。只是趙世奕的心原不在此,便連連咳嗽,不耐地催道,“還需等多久?”
Advertisement
姜姒垂頭道,“就快了,請大將軍再等一等。”
不多時,趙世奕臉愈發難看,又揚起聲催道,“本將軍急著飲茶,你為何如此怠慢?”
姜姒加快擊拂手中的茶筅,雙臂酸痛。雖時常點茶,卻都是細細打磨,不急不躁,許鶴儀亦有十分的耐心慢慢等待。眼下趙世奕急不可耐,還沒有細細調膏,他卻三番兩次地催促。
此時又聽趙世奕面含慍道,“殿下東宮的佳人越來越多,老臣本不好說什麼。只是,老臣來東宮也有一個時辰了,為何遲遲不見太子妃,難不太子妃也病了嗎?”
許鶴儀笑著,話里卻著幾分疏離,“太子妃了風寒,暫且不便見客。松花釀酒、春水煎茶,是雅事,大將軍不妨耐心等候。”
趙世奕冷著聲道,“姜姑娘既還未點完茶,老臣心急如焚,便不再等候。殿下若開恩,便準老臣去椒菽殿探太子妃。老臣來時,人亦是托老臣去給太子妃帶幾句話。”
此時,見姜姒已匆匆點好茶,許鶴儀便命道,“阿姒,奉茶。”
姜姒雙手端了茶盞便向趙世奕恭恭敬敬端去,不料趙世奕卻一下子掀翻茶盞,將那沸茶潑到了姜姒的臉上。姜姒吃痛尖一聲,忙拿袍袖擋住臉。
許鶴儀面僵住,神瞬間晦暗了幾分,子下意識地朝前傾去。
白芙一下子探過去,擰著眉頭道,“大將軍這是何意?”
趙世奕冷笑著著一青,聲音糲強,“這茶碗里竟有一人的發,當著殿下的面,你居然如此侮辱本將軍!”
Advertisement
姜姒的面頰燙的發紅,顧不上去滿臉的茶水,慌忙跪下,“大將軍恕罪,奴婢失職!”
許鶴儀冷冷地看著,沉著臉一言不發。
白芙輕笑道,“大將軍是征戰沙場的人,竟因一杯茶與一個小子計較,未免有失風度!”
趙世奕瞇著眼斥道,“你又是哪個?膽敢對本將軍無禮?”
姜姒趕拉著白芙的袖子,示意不要強出頭。白芙哪里管這些,只清清脆脆地說,“我嘛,我不過是殿下的客人罷了,將軍的規矩自然也管不著我!就事說事,大將軍今日當著太子殿下的面為難一個小子,便是為難太子殿下!大將軍說我無禮,真正無禮的只怕是大將軍吧!”
姜姒倒吸一口涼氣,白芙到底是什麼人,居然敢對著大將軍橫沖直撞。甚至昨日夜里去爬許鶴儀的床榻,此時竟也毫無怯之意。
有這般膽識,絕不是許之洐邊普通的侍婢。若今日許鶴儀不護著,只怕要惹上殺之禍。
又見奪過趙世奕手中的發,疑道,“殿下,這發堅,絕不是子之!”
趙世奕一時氣的語噎,站起指著白芙道,“你!你......”轉過頭又沖許鶴儀氣道,“東宮竟有這樣的人,殿下難道要袖手旁觀嗎?”
許鶴儀反倒輕笑起來,“大將軍不必介意,確實不算東宮的人。昨日亦沖撞了孤,孤也拿無法。”
趙世奕氣的冷笑連連,“若是這樣,老臣便也不計較了。只是,今日非要見太子妃一面不可!殿下若不允,只怕要傷老臣的心,誤會殿下狡兔死,走狗烹!”
Advertisement
許鶴儀溫和地笑道,“太子妃抱恙,醫叮囑見不得風,應好生休養。過幾日,待太子妃好些,孤便允回府探親,大將軍放心便是。”
趙世奕這才緩了臉。
姜姒跪在地上,心下卻一涼。長姝不過才關了一日,父親這樣一鬧,眼看就要出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1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491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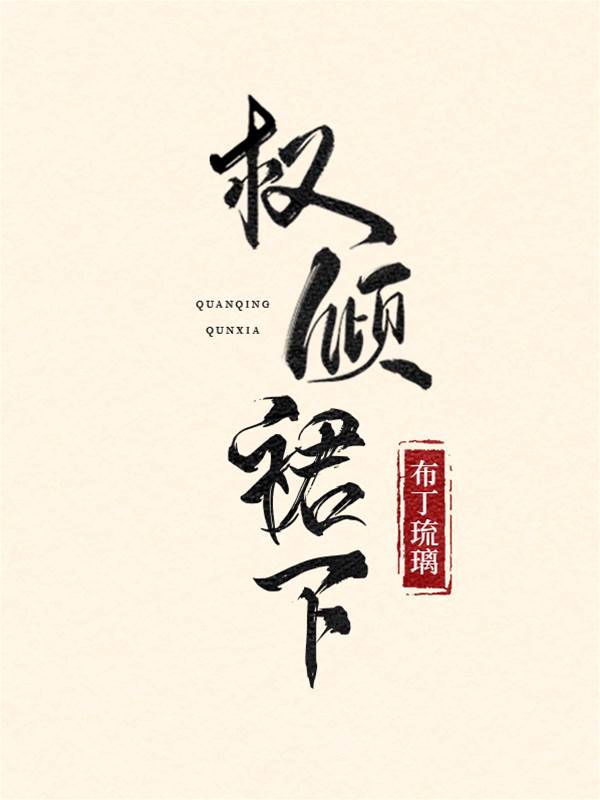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