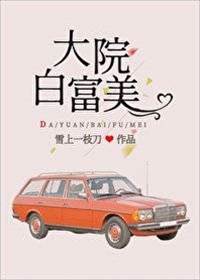《前妻攻略:傅先生偏要寵我》 第24章 你老公是不是對你不好?
梁漢卿扶著人,聽到這話,眼里劃過一抹驚訝。
盛眠結婚了?
可看傅燕城的神,不像是在開玩笑。
當年盛眠大學剛畢業,就邀進了他的工作室。
這三年來,從未見過和哪個異走得近,怎麼會已婚。
瞥見梁漢卿臉上的驚訝,傅燕城挑眉,“先把人送上去吧。”
梁漢卿點頭,小心翼翼的扶著盛眠,進了醫院大廳。
傅燕城也沒多待,愿意送人過來,已是看在兩人以后會相一段時間的份上。
開車回傅氏的路上,突然接到了老爺子的電話。
“燕城,你見到眠眠了麼?這丫頭是不是變得更漂亮了?”
老爺子說幾句,便會咳兩下,幾口氣,可見這次病兇猛,還不太好。
Advertisement
“爺爺,您好好在療養院待著,其他的事不用你心。”
“真要不用我這個老頭心,你們就早點兒生個大胖孫子給我看看,那孩子生斂,又是學畫搞藝的,你是男人,不能主一點?”
傅燕城皺眉,很想知道當初那個人到底給爺爺喂了什麼迷魂湯。
本反駁,那頭卻又傳來老爺子的咳嗽聲。
擔心沖撞了人,到底緩了語氣,“我會努力的。”
老爺子眉眼舒展,瞬間開心了起來。
“我下個月就回來,在國外待著,人都見不到幾個,許久沒見過那丫頭了,還有些掛念。我不在的時候,你可要把人護好,別讓被人給欺負了!”
傅燕城眉頭皺起來。
當初老爺子出國的時候,說是會在那邊的島上養老,沒想到這才一年不到,就打算回來了。
Advertisement
他本來準備先離婚,到時候再慢慢給老爺子做思想工作。
可若老爺子真的下個月回來,猛地聽說他離婚的事兒,會不會一氣之下直接暈過去?
想到這個可能,傅燕城臉沉了下去,修長的指尖著方向盤,眉宇仿佛染了霜雪。
這婚暫時不能離。
至在老爺子回來這段時間不能離了。
不僅不能離,還得佯裝恩的模樣。
看來有必要找時間親自和那個人談一下了。
醫院這邊,盛眠打了退燒針,還輸了后,總算醒了過來。
緩緩睜開眼睛,看到雪白陌生的環境,眉宇一皺,撐著就要起來。
起到一半,因為力氣耗盡,差點兒摔回去。
打水回來的梁漢卿忙手將扶住,“別,你都快燒到四十度了。”
Advertisement
盛眠聽到這悉的聲音,繃著的神經緩緩放松,但想到暈倒前那一幕,心臟又是一。
“傅總呢?”
梁漢卿嘆了口氣,給倒了杯水,“我倒是想問你,怎麼跟他在一起?”
盛眠接過,潤了潤干啞的嗓子,“還沒來得及告訴你,景苑那一單拿下了,工作室暫時不用賣了。”
梁漢卿一愣,接著就有些,“辛苦你了。”
盛眠的嗓子好了一些,又聽到他問,“不過你什麼時候結婚了?”
盛眠猝不及防,差點兒被水嗆著,連忙整理了一下語句,“結了三年了,抱歉,一直沒跟你說起過。”
“這是你的私事,說不說倒無所謂,只是這三年從未見過你老公來接你下班,就連今天你暈過去,他也沒出現,若不是傅總提了一,我都不知道你已經結婚了。”
盛眠有些尷尬,只能將給傅燕城的說辭又大致重復了一遍。
“我老公他工作忙。”
“再忙也不能如此忽視你,你把他號碼給我吧,我打電話通知他,醫生說你得住院兩天,我要回工作室的話,總不能讓你一個人待醫院。”
“老板,不用了。”
梁漢卿平時與盛眠相,除上下級之外,他拿當妹妹一般,看到盛眠如此排斥,他遲疑再三,終于問了出來。
“小眠,你老實告訴我你老公是不是對你不好?”
剛剛護士給盛眠打針時,了一小截服上去,他不小心看到了上青紫的痕跡。
像是被人掐出來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和周先生先婚後愛
婚後,宋顏初被周先生寵上了天。 她覺得很奇怪,夜裡逼問周先生,“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對我這麼好?” 周先生食饜了,圈著她的腰肢,眼眸含笑,“周太太,分明是你說的。” 什麼是她說的?? —— 七年前,畢業晚會上,宋顏初喝得酩酊大醉,堵住了走廊上的周郝。 周郝看著她,隻聽她醉醺醺地歪頭道:“七年後,你要是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吧!” 少年明知醉話不算數,但他還是拿出手機,溫聲誘哄,“宋顏初,你說什麼,我冇聽清。” 小姑娘蹙著眉,音量放大,“我說!周郝,如果七年後你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
13.1萬字8.09 58565 -
完結280 章

總裁夫人她馬甲轟動全城了
前世,花堇一被矇騙多年,一身精湛的醫術被埋冇,像小醜一樣活了十三年,臨死之前她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場巨大陰謀。重生後,她借病唯由獨自回到老家生活,實則是踏入醫學界,靠一雙手、一身醫術救了不少人。三年後她王者歸來,絕地成神!先替自己報仇雪恨,嚴懲渣男惡女;同時憑藉最強大腦,多方麵發展自己的愛好,畫家、寫作、賭石...隻要她喜歡,她都去做!她披著馬甲在各個行業大放光芒!權勢滔天,富豪榜排名第一大總裁席北言:媳婦,看看我,求求了!餘生所有,夢想、榮耀、你。
51.6萬字8 29860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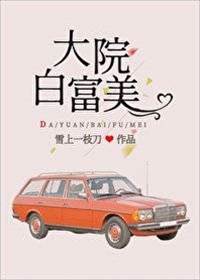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440 -
完結1436 章

我在娛樂圈修仙
【女強+絕寵+修仙】暴發戶之女林芮,從小到大欺女霸男,無惡不作。最後出了意外,一縷異世香魂在這個身體裡麵甦醒了過來。最強女仙林芮看了看鏡子裡麵畫著煙燻妝,染著五顏六色頭髮的模樣,嘴角抽了抽。這……什麼玩意兒?! “雲先生,林影後的威亞斷了,就剩下一根,她還在上麵飛!” “冇事。”雲澤語氣自豪。 “雲先生,林影後去原始森林參加真人秀,竟然帶回來一群野獸!” “隨她。”雲澤語氣寵溺。 “雲先生,林影後的緋聞上熱搜了,據說林影後跟一個神秘男人……咦,雲先生呢?” (推薦酒哥火文《我,異能女主,超兇的》)
135.2萬字8 23125 -
完結169 章

勾月亮
『特警隊長×新聞記者』久別重逢,夏唯躲著前男友走。對他的形容詞隻有渣男,花心,頂著一張帥掉渣的臉招搖撞騙。夏唯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江焱回她:“沒關係,玩我也行。”沒人知道,多少個熬夜的晚上,他腦海裏全是夏唯的模樣,在分開的兩年裏,他在腦海裏已經有千萬種和她重逢的場麵。認識他們的都知道,江焱隻會給夏唯低頭。小劇場:?懷城大學邀請分校特警學院的江焱學長來校講話。江焱把她抵在第一次見她的籃球場觀眾席上撕咬耳垂。他站在臺上講話結束後,有學弟學妹想要八卦他的感情生活,江焱充滿寵溺的眼神落在觀眾席的某個座位上。一身西裝加上他令人發指的魅力,看向觀眾席的一側,字音沉穩堅定:“給你們介紹一下,你們新聞係的19級係花小學姐,是我的江太太。”--婚後有天夏唯突然問他:“你第一次見我,除了想追我,還有沒有別的想法?”他低頭吻了吻女孩,聲音帶著啞:“還想娶你。”他擁抱住了世間唯一的月亮......於是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江焱——已婚!〖小甜餅?破鏡重圓?治愈?雙潔〗
28.6萬字8 75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