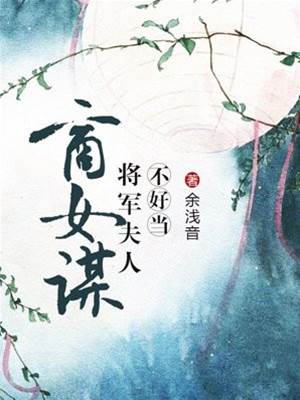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夫人讀心術失靈,小侯爺日日邀寵》 第20章 夢中預劫,闖青樓救夫君!
“為何要另找一位掌櫃?”卿扶瞧著,不解道:“你自己不是很好嗎?”
老夫人沉片刻,“你若是擔心對商號不能練經營,我早年有一位老友,倒是對這方麵很了解,我待會兒便寫封信,托從揚州回來。”
奚挽君沒反應過來,“母親、祖母,你們…不介意我經商?”
卿扶失笑:“為什麽介意?我認識你娘的時候,的絕英閣尚在雛形,其間還問過我一些朝廷的消息,你若是擔心我們介意這些,可把我們想得太刻薄了。”
奚挽君忙擺手,“挽君沒有此意,隻是聽聞皇後姨母不喜商賈,所以我才……”
“挽君。”卿扶輕輕了下的額頭,“你是笨蛋嗎?”
徹底糊塗了,“啊?”
“京城裏的傳言數不勝數,有說藺家門風森嚴,將子孫管教得方言矩行;
亦有傳言,說你奚家繼室賢惠大度,待你這個嫡很是疼惜;
還有傳言,說我桑家都是些不識墨水的大老,靠著結皇後和家才能有今日的地位。”
卿扶耐心地了的鬢角,“挽君,這其中傳言,你自己也清楚孰真孰假,
不管別人怎麽說,但皇後與我是親姊妹,的子我極為了解,絕不會歧視或厭惡商賈,
況且再退一萬步來說,就算皇後不喜商賈,與你有什麽關係呢?與咱們家有什麽關係呢?”
奚挽君整個人都怔住了。
老夫人像是瞧明白了心深的自卑,疼惜道:“挽君,你要記住了,子立世,當比男兒活得更清醒,要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麽,
若是渾渾噩噩,聽人任人,那與行走有何區別?”
卿扶認可地嗯了聲,“你若是害怕這些個,倒全然不必,
就算日後遇上了險阻,也不要因為一些不值當的眼和指點退讓,
Advertisement
這也是你娘當初經曆過的,但堅持下來了,母親希你也能堅持。”
老夫人笑道:“如今阿遠有事做,你也有事做,夫婦倆共同進步,桑家的明日實在可期。”
桑家的明日……
奚挽君眼眶微微發酸,心頭萬般複雜。
從前是奚家嫡,卻任人欺辱,莫說想要做的事,就算連最基本的穿戴溫飽都難以做主。
可如今方嫁進桑家,與這一家人尚不稔,們卻認真地傾聽想做的事,甚至鼓勵不要放棄。
深覺局促不安,又之有愧。
也是現在才理解,為何桑渡遠在聽說想要繼承絕英閣時,表現得那般無所謂了。
正是因為他從小所教育便是如此——男子與子並無不同,子亦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許,嫁到桑家來,是個正確的選擇。
從正堂出來前,卿扶二人還同代了一些回門的事項,叮囑讓桑渡遠與一同回去,多住幾天也無事,正好正式拜見過莊憫生和莊采黠。
奚挽君正要同桑渡遠商量一下回門之事,但房夜闖進來的黑人再次出現。
“你是奚挽君?”
黑人今日換了藏藍玉麵華袍,頭發高束,麵上洗去跡後眉眼冷桀,等在春歸院門口,見他們二人來了,一個箭步便衝了上來,嚇得奚挽君後退了半步。
桑渡遠一把將扯到自己後,瞳孔裏泛起不悅,“李逢生,你搞什麽鬼?”
李逢生咬牙關,聲線發,“你是莊采黠的誰?”
奚挽君愣了下,“外、外甥,怎麽了?”
李逢生再度近,桑渡遠卻毫不客氣擋在了他麵前,語氣很冷:“做什麽?”
“阿遠,先前沒跟你說過,奚挽君……”李逢生瞳孔中的緒百轉,隻剩下,“是我的夫人。”
Advertisement
“啊?”
“啊?”
二臉驚呆。
桑渡遠第一個反應過來,指著奚挽君,“你在外頭給我戴了綠帽?”
“胡說什麽!”奚挽君錯愕地盯著李逢生,“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位?”
“桑渡遠,你要是把我當你兄弟,挽君便是你嫂子,還不快些讓開。”李逢生又要衝上來。
“天爺,我不是啊!”奚挽君以為這人瘋了,連忙閃躲。
桑渡遠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一邊讓大焱攔住人,“李逢生你個狗玩意,我把你當好兄弟,你搶我媳婦兒?”
李逢生大聲道:“那是我媳婦兒。”
“你放屁,跟你拜過堂嗎?”桑渡遠險些一腳踹在他臉上。
奚挽君傻眼了,連忙攔住要打起來的二人,“這位李公子,我的確不認識你,何況咱們不是隻在我嫁進桑家那一日見過麵嗎?”
桑渡遠咬後槽牙。
【難道他倆是在那一日勾搭上的?可那一日我不是與他一起走的嗎?】
【懂了,難怪那夜這狗玩意比我先走,難道是……】
“不是!”奚挽君怒視著他,又緩過神來,耐心解釋道:“我的確沒見過你這位朋友。”
李逢生歎了口氣,“我的確與挽君不相識。”
“不許挽君。”桑某人滿臉黑沉。
“不過,挽君的舅舅便是雲麾將軍,十年前,他曾在我危難之際救過我一命。”
李逢生陷了回憶,“我當時許下以命相酬的諾言,雲麾將軍卻說不要我的命,他瞧我年輕有為,便承諾將挽君嫁與我,日後待挽君好,也算是報答他了。”
桑某人強調:“不許挽君!”
奚挽君皺眉,“我舅舅還幹過這麽不靠譜的事兒?”
“挽君,雖然你如今嫁給了桑渡遠,但是我絕不嫌棄,你若是願意,我隨時帶你走。”李逢生滿臉凝重。
Advertisement
“十年前我才六歲,你說我舅舅許諾將我嫁給你,你多大?”估計這事兒是莊采黠喝多了才應下來的。
“你是在擔心我倆生辰八字不合嗎?”李逢生冷俊的麵孔浮現出幾分喜悅,“你放心,我不過二十有四,正是好年紀。”
“我去你大爺的!”
桑渡遠又要撲上去揍人,奚挽君連忙攔住道:“李公子,我舅舅這個人素來不太靠譜,他許諾你的時候,估計也喝了不。
如今我是桑家婦,不會嫁給你的,李公子與郎君是好友,日後咱們亦可以朋友相。”
李逢生滿臉都是不敢置信,“你真的願意嫁給桑渡遠?”
“大焱,去後廚將那把殺豬的砍刀取過來。”桑渡遠活了幾下手腕子,眸子裏快迸發出寒。
大焱抖了下,提醒道:“小侯爺,這可是驍騎校尉,不是別人。”
李逢生充耳不聞,繼續道:“他有什麽好?
論才學,他是地我是天;論脾,我比他靠譜多了,論武功,或許他還能與我平分秋。
這樣的人,是給不了你幸福的。”
奚挽君是怎麽也想不到,看了這麽多年話本子,這驚人的臺詞和劇還能發生在上。
“呃……”
猶豫了下,桑渡遠便一臉要砍人的模樣盯過來。
“我…喜歡好看的。”巍巍指了下桑渡遠的臉,信口胡謅道:“雖然你也不錯,但是桑渡遠好像更不錯。”
【哼。】
【這土匪也算是說了一回真話。】
“……”
李逢生一臉複雜,惋惜道:“原來你喜歡這種小白臉,果然,我還是太過男子氣概了。”
桑渡遠覺自己要背過氣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多做糾纏了。”李逢生麵上的黯然神傷一瞬即逝,又恢複到往日的冷,“太子歸京,以免四,傷之事不宜傳出來,他想要你幫忙打掩護。”
Advertisement
桑渡遠皺眉,對奚挽君道:“你先回去。”
奚挽君聽到太子傷四個字時心裏咯噔了一下,叮囑道:“那你注意安全,我等你回來商量回門的事。”
桑渡遠嗯了聲,隨即又猶豫道:“若是今夜我沒回,你明日便讓大焱陪你,自己回去吧。”
聞言愣了下,瞧了眼李逢生,始終沒說什麽。
……
翌日晨。
汪媽媽端來洗臉水推門而,隻瞧奚挽君坐在床頭愣神。
“夫人,姑爺還是沒回來嗎?”汪媽媽擔憂地瞧著子,對方似乎坐在榻上很久了,一直沒有換過作。
奚挽君回過神,一臉擔憂,“我做了個夢。”
汪媽媽不解,“夫人是做噩夢了?”
“我昨夜夢見……”奚挽君話說到一半,又戛然而止。
昨夜睡下後,一直輾轉反側,等不到桑渡遠回來,迷迷糊糊間意識好像飄到了一個很遠的地方。
夢中,家嚴聲責罵太子和桑家,罵太子不知檢點,居然在語樓強暴了一個良家子,良家子自知丟了清白,竟咬舌自盡。
此事傳了出去,鬧得沸沸揚揚,百姓們都指責太子行為不端。
而桑渡遠不知勸告,將太子帶去了語樓,行齷齪之事。
太子被奪走兵權,足東宮。
而桑渡遠失去了繼承爵位的資格,家並嚴令他未來不得參加科考。
侯爺桑護疆和侯夫人卿扶教子不嚴,也重責五十大板,桑護疆再也握不刀,而卿扶險些命喪黃泉。
整個桑家了京城中最大的笑話……
“夫人,昨日姑爺說讓您自個回門,如今他也不知去哪了,要不咱們便自己回去罷?”汪媽媽一臉心疼地瞧著子。
“可憐夫人您剛過門,侯爺便將你一個人丟下,此番回門,隻怕奚家人和外頭的人都會看咱們熱鬧。”
奚挽君深吸一口氣,“不、不能回門,我得去確認一下。”
汪媽媽愣住了,“夫人您沒事吧?確認什麽?”
奚挽君洗漱好換完,剛出院門,便撞上了桑種。
“二叔?您怎麽瞧上去……”
桑種滿酒漬狼藉,眼皮下一片烏黑,不停往後瞥,神閃爍,“沒、沒什麽。”
奚挽君有一種直覺,問道:“二叔是不是知道郎君在哪兒?”
桑種愣了下,反應過來連忙擺手,“我不清楚。”
這個反應…那便是清楚了。
“二叔若是不說清楚,您在語樓做的那些事兒,挽君可就瞞不住了。”隻能問。
桑種瞪大了眼,“你、你怎麽知……”
“您別管我怎麽知道的,隻要告訴我,郎君現在是不是在語樓?”奚挽君看著他,心急如焚。
桑種無可奈何,解釋道:“是,但是挽君你別誤會,渡遠這次是陪太子去的,是公事,可不是他沾花惹草。”
奚挽君心底一沉,猶如一顆巨石從天而降,得難以息。
桑種見這反應,以為是傷心過度,著急道:“挽君你真別誤會,我昨夜去語樓著他了,真沒來。
不過今早我剛剛回來的時候,正好見燕王帶人去了語樓,也不知是不是找太子的,
你也知道你二嬸脾氣不好,我這才趁著時辰尚早溜回來。”
“燕王…是他。”奚挽君心如麻,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大焱在哪?”
汪媽媽連忙指道:“剛準備出去套馬車,送咱們回莊家。”
“他回來,將昨日桑渡遠說過的殺豬刀提過來。”奚挽君深吸一口氣。
桑種捂住,驚慌失措道:“侄媳婦兒!你別衝,你聽我說,這個世上哪個男人不腥。
你才嫁進門多久,若是將那混小子傷著了,名聲傳出去可不好聽了!”
“對。”奚挽君閡著眼,“這一次,不能再顧及名聲了。”
桑種來不及阻攔,就見大焱將二尺長的大砍刀從老遠扛了過來,“夫人,咱們去哪?”
凝聲:“語樓。”
……
包房氣息旖旎,桑渡遠從桌案上清醒過來後,瞧著滿屋狼藉,心頭隻餘凝重。
他們上套了。
趙亦寒用被褥捂住口,死死盯著一旁口吐鮮的子,著聲:“死了。”
“燕王將咱們包圍了。”李逢生盯樓外況。
桑渡遠寒聲:“這個子不簡單,隻怕是燕王安排的。”
“昨夜,咱們分明沒有點行首進來,這個子不知是從哪兒進來的,放了迷煙後,咱們全暈了,再醒來,便睡在了本宮旁。”趙亦寒清醒後,瞧見旁人猶如五雷轟頂。
猜你喜歡
-
完結527 章

空間小農女:帶著全家去逃荒
壹場意外,該死的豆腐渣工程,全家穿越到古代。 家徒四壁,破破爛爛,窮到裝餓換吃的。葉秦秦歎息,還要她有個隨身商場,帶著老爹老娘壹起發家致富。 還沒開始致富,戰亂來襲,壹家人匆忙走上遷移之路。 當個軍戶種田,壹不小心將葉家名揚四海。 從此,高産黃豆的種植技術,神秘的東方料理……,成爲大夏朝子民瘋狂探究的謎題。 這家人了不得,個個知識淵博,拿出來的東西聞所未聞。 葉秦秦帶領全家走上致富之路,順便撿個小崽子。啊咧,到了後來小狼崽掉馬甲,原來……
95.8萬字8 58545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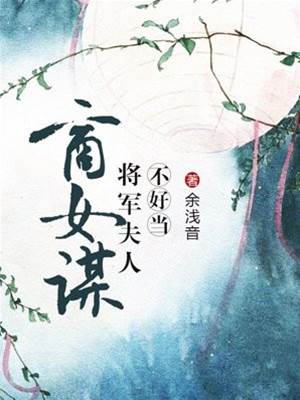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完結121 章

短命白月光只想鹹魚
HE! HE! 日更,入V後日六。 既然有人強烈提了,那就避雷:血型文,女主攻分化後會有丁丁。 江軼長到十六歲,忽然覺醒自己是個穿書的,還是穿進了一本不可描述的小說里。 這本書的女主受,就是她便宜媽媽現女友的女兒——江似霰。 而她就是江似霰的短命白月光。 她要是被江似霰看上,按照劇情,妥妥早日歸西。 為了茍命,江軼決定:我! 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拒絕早戀,成就輝煌! 我是絕對不會為了談戀愛搭上小命的! 珍愛生命,遠離江似霰從此成了江軼的人生教條。 但我們知道,人類的本質是真香,所以之後——江軼:我太傻了,真的。 早知道會有那麼一天,我絕對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在隱藏自己心意的事情上面。 我應該每一天都很認真的對你說「我愛你」 ,陪伴你渡過每一個難熬的發情期,永遠不會離開你。 ——大概是:行事囂張街頭小霸王x端莊典雅豪門繼承人。 江軼路子很野,會打爆別人狗頭的那種。 立意:有情人終成眷屬
36.2萬字8.18 4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