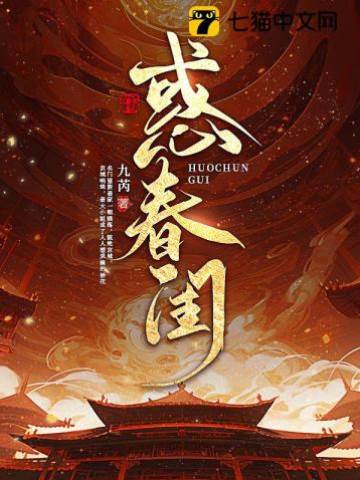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有匪(有翡)》 第38章
第38章 枯榮
周翡愕然道:“前輩,你這是做什麼?”
段九娘天真無邪地眨眨眼:“我教你啊!”
沒聽說學功夫還得被定木頭人,周翡頓時有種不祥的預,饒是懶得跟瘋子計較,也不想睜眼看著瘋子把玩死,忙岔開話題道:“前輩不是說有專門克破雪刀的本事嗎?我漲漲見識好不好?”
段九娘煞有介事地說道:“那都是招式,我枯榮手功為基,鍛為輔,招式為次,剛門的時候都得從基礎打起。”
周翡一聽,真是頭皮都炸起來了——有道是東西吃下去就不好吐,經脈岔了氣就不好順,倘若任由這瘋子在上瞎指點,以後鬧不好在院裡耍把式的還得再多一人。
眼下真是寧可段瘋婆子繼續的拆房大業,也不想領教的一本正經。
周翡急之下,無端多了幾分胡說八道的急智,飛快地拍了個馬屁道:“那個不急,我原來一直以為我家的破雪刀是世上最厲害的刀法,從來沒聽說過還有什麼能跟它相克,差點就坐井觀天了……呃……前輩還是快給我見識一下吧。”
段九娘的心智時大時小、時老時,這會有點像小孩,聽說周翡要見識自己的得意之作,三言兩語就被哄得眉開眼笑,一甩袖子解開周翡的道:“那你跟我來。”
段九娘十分沒輕沒重,周翡好不容易將一聲嗆咳忍了回去,氣都沒來得及順過來,那段九娘又嫌磨蹭,一把攥住的手腕,將連拉帶拽地拎了出去,然後把長刀塞進手裡,又不知從哪撿來一樹枝,笑嘻嘻地對周翡說道:“來,來。”
周翡將長刀在自己手中掂了兩下,雖然不怎麼仇恨段九娘了,但眼下制於手,到底還有些不甘心,便說道:“前輩,九式的破雪刀,我有一大半都使得畫虎類犬,倘若丟人現眼,是怪我自己學藝不,可不是刀不好的緣故。”
Advertisement
段九娘不耐煩道:“你這小孩子,一點年紀,也和李徵一樣囉嗦!”
周翡長到這麼大,被人嫌棄過脾氣臭、毒手黑,還從來沒人說過“囉嗦”,實在啼笑皆非。想不到外公在世時惹的這朵爛桃花,好好地爛了這麼多年都與世相安,倒是自己機緣巧合,非得送上門來給人糊一臉。
嘖,也是命。
“前輩請了。”周翡將手中長刀一抖,摒除了心頭雜念,長刀在手中卷起了一道旋風。
破雪刀前三式大開大合,乃是“劈山”“分海”“斬不周”。
周翡直接將“山海”兩部分略過,使出了在木小喬山谷裡方才領悟的“不周風”一式,這是九式破雪刀中最快、最紛繁無常的一式,那刀所到之,能斷鳴音、裂飛影。
同時,又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山谷一戰中,沖霄子提點的“蜉蝣陣”,靈機一,便在走轉騰挪中帶了出來。
周翡這一點天賦仿佛是與生俱來的,凡事不講究路數、特別會抓大放小,看見別人功夫中有什麼讓人眼前一亮之,有時候不知起了什麼古怪的靈,便能張冠李戴地用在別出。
“蜉蝣陣”相傳能以一當萬,“不周風”又最適合對抗群毆,兩廂結合,便如虎添翼,周翡活生生地把“不周風”變了“東南西北風”。
段九娘一時間只覺得自己周圍好像圍了七八個人,不由得有些訝異,輕輕“咦”了一聲,沒料到周翡這麼一個看起來中規中矩的人,居然有十分不規矩的一面。
像枯榮手那樣的家功夫,對上小輩是不必拿真刀真槍的,一破敗的樹枝到了手中,也能如神兵利,兩人電石火間走了七八招,段九娘基本沒有還手。
Advertisement
直到看明白了周翡這別出心裁的路數,方才輕笑了一聲道:“你瞧我的。”
話音未落,周翡便覺得掌中刀好像給什麼黏住了一樣,對方似乎只是拿著那小樹杈在長刀上隨意點幾下,周翡那原本來勢洶洶的刀風頓時中斷,再也找不到方才行雲流水似的暢快覺。
周翡急忙要撤手,然而那刀鋒一被迫減速,驟然被段九娘捉到形跡,一把抓在了手裡。只出了三手指,便牢牢地夾住了周翡的刀面,虎口懸空,與森冷的鐵刃之間有約莫一指寬,卻是遊刃有餘,連油皮都沒有破一層。
周翡倏地一驚,對上了段九娘的目。
段九娘看著,惡作劇似的悄悄笑,小聲說道:“這個啊,就做‘捕風’。”
周翡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可能比旁人要遲鈍一些,相較而言,領會刀劍的話比領會人話來得更清晰直白——先前聽老僕婦唾沫橫飛地講那些個恨仇,周翡基本都沒什麼,站著聽故事裡的人來回作妖,一點也不腰疼。
直到親眼見了這一招,親耳聽了“捕風”二字。
周翡突然沒來由地一陣難,一瞬間就設地地明白了何為“去者不可留、而往事不可追”。
愣了片刻,眼圈毫無預兆地紅了。
段九娘吃了一驚,手足無措地收斂了得意洋洋的笑容,想了想,又蓋彌彰地將手中的小木條背在後,說道:“哎……你怎麼這樣,輸了就哭啊?”
周翡深吸一口氣,將眼淚憋了回去,皺著眉一低頭道:“誰哭了?”
段九娘頗為孩子氣地一彎腰,從下往上覷著的神,小心翼翼地說道:“我有一次被四條惡犬追了好幾十裡地,給他們打得滿地打滾,都還沒哭呢。”
Advertisement
周翡哭笑不得,了眼,將長刀掛回刀鞘,反走到屋前,隔著窗戶看了吳楚楚一眼,見連日顛沛,頭一次挨著枕頭,睡得死死的,一點也沒被驚,便給帶上門,自己坐在了門口,段九娘也湊過去,坐在旁邊。
段九娘道:“我看你骨一般,練破雪刀太吃力了。”
周翡心說,那也比李晟強,李晟都沒撈著大當家傳刀呢。
便毫不當回事地說道:“吃力就慢慢練唄。”
段九娘正經八百地點點頭,嚴肅地說道:“是這個道理,往後要好好用功才行。”
周翡自覺已經十分用功,便將自己在四十八寨洗墨江中練刀的事講給聽。段九娘一聽見“四十八寨”幾個字,就十分專注,恨不能將周翡每個唾沫星子都拓印下來,暗自珍藏。
然而聽完了這一段,卻又笑道:“你這什麼用功?你爹那人婆婆媽媽,肯定最會縱著你們啦。”
的記憶顛三倒四,這會好像又記串了輩分,拿周翡當了李徵的兒,周翡只好給糾正回來。
段九娘“哦”了一聲,也不知聽沒聽進去,又說道:“我小時候剛開始練功的時候,有師兄弟好幾十人,頭一年就死了一半,第二年又死了剩下的一多半,及至門三年,連我在,就剩下五個人啦,你知道為什麼嗎?”
周翡從來沒聽說過這麼能死人的門派,忙震驚地搖搖頭。
段九娘平平淡淡地說道:“因為我師父每個月過來傳一次功,將一道真氣打我們,那個滋味你肯定不曉得,渾的皮要跟骨頭炸開一樣,這種時候,你可萬萬不能暈過去,暈過去就會而亡,得忍著刮骨之痛,一點一點將那竄的真氣強行收服,倘若不能收服,就得走火魔、七竅流而亡。等三年基礎打完,後面就是鍛,鍛就更容易死啦。我師父常說,沒斷過的骨頭都不結實,又過了兩年,就只剩下我和師兄兩人了!”
Advertisement
周翡骨悚然,覺這門派不像教徒弟,像養蠱。
段九娘便怒其不爭地看著歎道:“你爹……”
“外公。”周翡又糾正了一遍。
段九娘吃力地琢磨了半晌,本弄不清自己是在哪一段年月,愕然道:“什麼?李瑾容那個小丫頭何時有你這麼大的閨了?”
周翡聽這樣糊塗,也就不怎麼信方才那一堆鬼話了,頗有耐心地重新將自己的家譜講給聽……不過講也沒用,過了一會,又變“重孫”了。
兩人說的話,時而對得上,時而本是同鴨講,然而說來也怪,白日裡,周翡還恨不能將這瘋婆子千刀萬剮,這會大半夜不睡覺,跟段九娘坐在一起,聽七八糟地講陳年舊事,卻又覺得又新鮮又親切,一點也不嫌腦子裡是一鍋熬了十多年的糊粥,一聊聊到了天亮。
周翡便對段九娘說道:“前輩,你不要在這鬼地方他們的氣了,跟我們回寨中吧。”
的前半句話,段九娘有點沒聽懂,大概的神魂顛倒在過去,也並沒有覺出自己現在了什麼氣。
後半句卻懂了,段九娘面上先一喜,隨即又一呆,這一呆就大有天長地久的意思,周翡等了半晌,不知自己哪個字說錯了,便手拍了拍的膝蓋:“前輩?”
段九娘就跟詐似的,“騰”一下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道:“去四十八寨做什麼?守寡?”
這一瞬間,好似終於掰扯清了自己在哪一時哪一刻,枯瘦的手一把抓住周翡的肩頭。
周翡只覺得周一麻,隨即一難以形容的古怪真氣自上而下地流奇經八脈之間。
尋常息都如水流,有的寧靜些、有的暴些,可是這息卻仿佛一柄剔骨鋼刀,不由分說地從骨中穿,橫衝直撞,所到之,便似乎給人剝皮筋似的。
段九娘就跟讓鬼附了一樣,一掃方才的“天真活潑”,雙手抱在前,居高臨下地看著周翡疼得吭不出聲來,面無表道:“枯榮手‘外有別’,我練的是‘枯’,真氣注你,便會翻轉‘榮’,生生流轉不息,你只要是能過去,就能練我師兄的功夫。‘枯榮手’中,枯手雖然更狠毒,但歸到底,榮手更厲害,只不過克化的時候吃的苦也更多些,當年所有練榮手的同門,一年之就死得只剩我師兄一個人了……可惜我師父那混帳一個人只肯傳一門功夫,枯榮手相生相斥,我跟我師兄一枯一榮,沒法互相傳功。”
周翡耳畔“嗡嗡”作響,本聽不清叨叨了些什麼。
老僕婦聽見靜,連忙從廂房中跑出來,見周翡臉上已經沒了人。
的道只被段九娘封住了一瞬間,很快便被打進來的枯榮真氣衝開了,周翡再也坐不住,從門檻上滾了下來,手腳輕輕地著,不知是微弱的掙扎,還是無法抑制的哆嗦。
老廚娘目瞪口呆道:“夫人,您做什麼?”
好不容易睡了一宿好覺的吳楚楚才剛剛方才從夢裡醒來,未想又生變故,簡直要崩潰,一個平素笑不齒的大小姐冠不整地跑到了院裡,忙要手將周翡扶起來。
可是周翡上的骨仿佛變質了石頭,又又冷又沉重,徒勞地了兩次手,竟不知該落在哪裡,急得團團轉。
段九娘神冷漠,兀自在一邊的樹下盤膝坐下,一會像老妖怪,一會像小孩,可是這一坐,卻又約有了些許宗師一般的淵嶽之氣……只是約莫不是太溫和正派的“宗師”。
段九娘正道:“自古以來,宗門林立,有些門派縱能因幾個風流人顯赫一時,也終於有衰,後代傳承便如那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你們可知為什麼?”
在場三人,一個歇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一個隻會繡花詩,還有一個畢生專注於掃帚與鍋鏟大業,並不關心其他俗事——沒有一個能領會段宗師這番看遍今古英雄的高論。
苦無知己的段九娘只好寂寞地自說自話。
說道:“你因何習武?學的什麼刀槍劍戟?走的什麼天地乾坤道?你們那些個迂腐的名門正派,只會教弟子‘習武是強健’,說什麼‘將來要鋤強扶弱’的廢話,教出來的弟子也多半是給人‘鋤’的廢!武學一道,就是掙你的小命,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你要我死我偏不死’!沒有這一層氣神,你和打把勢賣藝的有什麼區別?你翻的跟頭還不見得有猴翻得爽利呢。”
周翡的指甲本來修得很短,這一陣子天天逃命,卻是顧不上了,長出了一小截,狠狠地摳進院中青石的地面上,很快模糊。
吳楚楚哭著懇求道:“夫人,既然是李大俠的外孫,不也相當於您的晚輩?倘若有什麼三長兩短,的父母兄弟,豈不是要傷心死了?夫人您心裡就不難過嗎?李大俠要是泉下有知,又怎麼忍心?”
段九娘被這幾句話說得愣了半晌。
吳楚楚見神鬆,忙機靈地再接再厲道:“求您快救救阿翡呀!”
段九娘聽了,搖頭道:“那我救不了,枯榮真氣已,拔是拔不出的,只能看自己的。”
吳楚楚差點給跪下,這不是管殺不管埋麼?
段九娘說著說著,面又不近人了起來:“要是真李家脈,就不該連這一點苦頭都吃不了,倘若真是這麼廢,死在我手裡,也比出門在外死在人家手裡強!”
猜你喜歡
-
完結413 章

這太子妃不當也罷
楚姣梨重生了,上輩子含恨而死的她,對於求而不得的太子妃之位,此刻不屑一顧地道:「這太子妃不當也罷!」 在決定親手為他與原太子妃牽橋搭線的時候,她聽到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什麼!太子妃不娶了?! 我上輩子為了太子妃之位都熬成病嬌了啊喂! 罷了罷了,咱再幫您物色新人選,但您可不可以不要總往我身上瞧?! 她逃,他追,他們都插翅難飛! 楚姣梨抬頭望著越疊越高的圍牆,不禁悵然道:「我的太子殿下啊,您快成婚吧!別再吊著我了!」 (PS:姐妹文《寵杏》已完結)
69.1萬字8 6536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2104 -
完結650 章
暖妻之誤惹首富王爺
某女臉上漸漸浮上一抹不明的笑容,“居然讓我睡地鋪,也不知道憐香惜玉,現在我要懲罰你,今晚你打地鋪! “ 某男終於意識到他自己挖了個坑把自己給埋了,趕緊湊上去,在女人紅唇上輕啄了一口,”夫人恕罪啊,你忍心讓相公打地鋪嗎? “ ”我很忍心!” 某女笑得眉眼彎彎,雙手環過男人的脖頸摟著,“從今晚開始,我以前睡了多少晚地鋪,你就睡夠多少晚,不許有異議!” “夫人確定?” “確定,從今晚開始,你睡地鋪!” “好! 本王今晚睡地鋪。 “ 某男墨黑的鳳眸裡蘊藏著點點精光,俊臉更是深沉莫測。 “本王這麼爽快答應夫人,夫人是不是該給點獎勵,嗯?”
121.6萬字8 16418 -
完結280 章

嬌養 慕如初
嬌軟笨美人×外表溫潤如玉,實際上腹黑狠厲的太子殿下。小時候阿圓逛廟會,不慎與家人走散,是個好心的大哥哥送她回家。那個大哥哥長得真好看吶,俊朗清雋,皎皎如天上月。大哥哥說他寄人籬下命運悲慘,甚至連飯都快吃不上了,但他人窮志不短,立誓要成為人上人。阿圓心疼又感動,鼓起勇氣安慰他:“大哥哥別難過,阿圓存銀錢養你。”也就養了兩三年吧,結果大哥哥搖身一變,成了傳說中心狠手辣的太子殿下。阿圓:QAQ 我感覺我養不起了。仆從們驚訝地發現,自從他們殿下遇見褚姑娘后,就變了個人,不再是那個陰郁狠厲的少年。他喜歡逗弄小姑娘,還親手給她喂糕點;教小姑娘讀書寫字,送許多精美華服讓她穿得可可愛愛;甚至,小姑娘受委屈,他耐心幫著擦眼淚后,暗暗地收拾了人。有一天,小姑娘兇巴巴道:“沈哥哥說自己寄人籬下還欠了許多債,怎麼總是揮金如土不知儉省?往后可莫要如此了。”仆從們冷汗:“不得了!居然有人敢管他家殿下!”可悄悄抬眼看去, 他家殿下竟是眸子含笑,無奈應了聲“好。”后來,誰人都知道東宮太子蕭韞有顆眼珠子,寶貝得緊。然而一朝身份掉馬,眼珠子生氣,他愣是哄人哄了好幾個月。 小劇場:太子恢復儲君身份的第二年,宮宴上,皇帝有意為太子擇妃。候府家的小姐明艷,公爵家的姑娘端方,個個貌美如花,含羞帶怯。可太子殿下卻突然起身,走到個五品小官之女跟前。 他神色寵溺:“阿圓,過來。”
37.9萬字8 30140 -
完結200 章

媚寵
齊春錦在周家宴上鬧了一場笑話,之后就隨父母遷到了苦寒的定州,自那日后,她卻開始日日做夢,夢里男人孤傲狠戾,像個活閻王,到了后來更每每掐著她的腰,像是要將她整個掐碎了一般;五年后,齊家大房敗落,齊春錦一房得以回京,周家又舉大宴,宴上人人討好攝政王,齊春錦小心翼翼地縮了縮身子:……這不是那個日日入她夢的男人嗎?-攝政王宋珩權傾朝野,俊美無雙,年近三十卻仍未娶妻,無人知曉日日神女入他夢,只是宋珩遍尋不得其人。周家宴上,眾人紛紛向他薦上自家女,宋珩一眼就瞥見了那張熟悉的面容,嬌軟動人,承三分媚意,還不等高興,面容的主人撞上他的目光,驚慌失措地往后躲了躲。宋珩:……他有這樣可怕?女主嬌媚柔軟貪吃好睡小慫包,男主表里不一每天都在被女主可愛哭的大壞蛋。 一個小甜甜日常文,炮灰死得快,配角都可愛,看女主怎麼變成團寵。免費章杠我我會杠回去哦寶貝~
28.7萬字8 4455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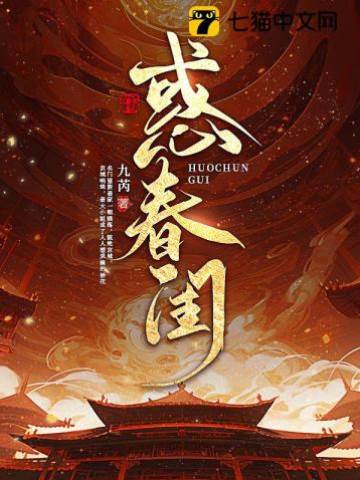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