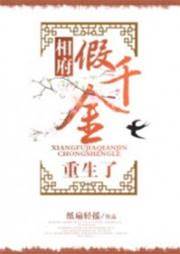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118章 探病
余的確傷了,傷的原因既不狗也不意外,就是上大名鼎鼎的"東北虎"火車劫匪了。
從國庫券離開證券公司營業部開始,大家就于高度張狀態。一開始他們用的是運鈔車,安全相對還有保證。等上了火車之后,國庫券的安全就全靠他們自己了。
余作為這次押運行的實行人,不僅要和同袍三人一組,兩小時一換,流看守裝了國庫券的行李車廂,他還得負責統籌工作。
因為擔心出事,那43個小時,他一直守在行李車間。
這時代的車子可不比二三十年后的高鐵車,行李車廂沒暖氣。大冬天的東北呀, 室外溫度能降到零下20度以下。家里也凍得要命。
他們弄了一堆軍大,所有看守的人基本上都埋在大堆里。饒是這樣,也凍得夠嗆。
車子快開出東北境時,大家正要松口氣,結果就出事了。
這年頭的槍.支管制跟幾十年后完全沒辦法比,火車上的劫匪不僅有刀,還了槍。
余他們反應過來, 雙方陷激戰,當場就打死了三位劫匪,剩下的匪徒倉皇而逃,余和另一位負責押送的戰士都了傷。
兩人在火車上做了急救之后,等到車子開到海城,完了和海城證券公司的接工作。他倆才轉來軍區醫院。
周秋萍不知道這事兒也就算了,知道了當然不能當什麼都沒發生。
原本打算去軍人俱樂部看看門面的,這回直接轉道去醫院。
周高氏原本一直暗地以婿的眼打量余,這回聽說他被槍打傷了,頓時嚇得魂飛魄散,堅決不敢讓兒找這樣的人。
秋萍還年輕呢,總不能這麼早就守寡。
Advertisement
周秋萍已經沒辦法跟阿媽的腦回路做通,無語至極∶"我跟他本來就啥都沒有。"
周高氏還在絮絮叨叨∶"我說他一個棒小伙子長得也不差,怎麼到現在也沒討到媳婦呢。看來大家都不蠢,不想當寡婦呢。"
周秋萍趕喊停∶"行了吧?哪有你這麼咒人的?我不跟你說了,我先過去看人了。你別慣著你孫,到時候該睡覺睡覺。"
哪知道兩個小丫頭看到媽媽出門,居然一左一右跑過來,要抱大。
周秋萍聽到外面呼呼的風聲,只得狠狠心∶"行了行了,不能帶你們出去,當心凍冒。"
怕死了小孩子生病,尤其是咳嗽,一咳就是幾個月,能把人瘋。
去看病人當然不好空著手。
周秋萍從家里拿了一罐子,又去買了點水果。考慮到大冬天的吃水果會冷,還額外帶了柿餅。
余神好的,按照他的標準,他的傷本不重,不過是跳彈傷而已。
看到周秋萍,他還能笑瞇瞇的調侃的禮∶"你這柿餅該不會是東鄉鎮拖拉機配件廠送的吧?
周秋萍哭笑不得∶ "你怎麼都知道了?鄭軍跟你說的吧。"
"不止呢。我這兩天沒事做,天天看報紙,報紙上好大一塊都是這次的報道。"
周秋萍好奇地拿起床頭柜上的報紙,果然,拖拉機的事被拎出來說了。
記者不僅采訪了洪等人,還去東鄉鎮拖拉機配件廠做了實地采訪。一篇報道洋洋灑灑,將事始末代得一干二凈。
就連高進明提供的那份調查報告也刊登了出來。
寧安縣機械廠這回算是全省揚名了,臭名遠揚。以次充好,掛羊頭賣狗,與其稱他們為機械廠,不如他們機械組裝廠。
Advertisement
上百萬的合同,給采購科科長的回扣就超過了20萬。
這還不算其他打點。
呵,問題鬧得這麼大,倒是要看看那位神通廣大的趙書記要怎麼保住他的寶貝兒。
估計他現在也顧不上吧,畢竟他私生活敗壞搞大小保姆肚子的舉報材料已經上到省里了。
說來這重要證還是趙書記自己提供的呢。時代在發展,科學在進步,病房里沒其他人不代表沒錄音機啊。
他那些深款款的保證,可是一字不落地錄得清清楚楚。
就是不知道紀檢干部聽了會不會覺耳朵很辣。
嗯,如果他們相護的話也沒關系,記者不介意幫忙刊登出來,廣播臺也不介意以觀眾留言的方式幫他傳播出去。
看到時候是誰的天下。
周秋萍心愉悅,繼續讀報紙,看到后面,驚訝不已∶"他們廠長也有問題呀?"
按照報紙上的說法,有職工實名舉報王廠長勾結其他領導,肆意將廠里的產品定為報廢品,然后低價賣出,從中收取回扣。
這種事在國營廠里不見。從報表上看,他們的產品質量低下,產品報廢率高居不下。然而真正用過這個時代產品的人基本都知道,東西真扎實,用幾十年都不壞。
這數據與現實的差距,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有人從中撈錢。
余嘆氣,頗為傷∶"好好的一個廠,就這樣被蛀蟲給蛀空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火車全靠火車頭。廠長都貪污腐敗了,底下的人還不上行下效。可憐的還是那些把廠子當自己家的工人啊。
周秋萍想了半天,跟著嘆氣∶"主要是領導搞垮一個廠,還能再去另一個廠繼續當領導。他們才不怕呢。就是當不也無所謂,反正他們撈的錢不僅自己一輩子,孫輩都夠花了。"
Advertisement
不過死道友不死盆道。
經過這事,鄭州柴油機廠已經徹底不考慮將機械廠作為自己在江省的定點供貨商了。兵工廠正在和他們談判,雙方流的好,估計能拿下訂單。
這一單,差不多要上千萬呢。
周秋萍看浸泡在開水里的蘋果泡的差不多了,拿出來削皮,然后切小塊,裝在飯盒里,又上牙簽,招呼余吃。
現在人很有這麼講究的,飯盒都送到余面前了,他還于震驚中。
旋即,他的臉慢慢紅了,支支吾吾道∶"你這是把我當青青和星星了。"
周秋萍搖頭∶"我可不敢讓們這樣吃,牙簽到就危險了。們都是拿勺子自己舀。吃吧,這蘋果是陜西過來的,甜的。"
余這才一小塊一小塊送進里。
周秋萍自己剝橘子吃,有一搭沒一搭的跟他說打口磁帶的事。
"安排差不多了,等門面到位再裝修一下,最早元旦就能擺出來賣。"
余幫出主意∶"你說的那個補修磁帶的方法,我覺得嫂子們也能做。說不定們的手還更巧5."
周秋萍笑了∶"我也是這麼想的。"
主要是這活只要訓練得當,即便是文盲也能干好。需要安排工作的軍嫂人不,如果將這部分分給們做,起碼能創造好幾倍工作崗位。
隨軍家屬管理起來也方便,能省不事。
余笑著調侃∶"你現在真是部隊的人,急部隊之所急,想部隊之所想。起碼得給你申請個三等功。"
現在如何養活部隊已經了領導最頭疼的事。
周秋萍笑了∶"我也沒做白工呀,我不掙到錢了嗎?"
看他蘋果吃得差不多了,拿起飯盒去衛生間沖洗干凈,然后蓋上蓋子,跟他道別∶"好了,看你生龍活虎的,我就放心了。時候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Advertisement
余掙扎著要起床送,被一把摁住∶"行了行了,你別折騰,好好休養吧。別仗著年輕不當回事,不養好了傷,以后吃虧的還是你自己。"
余不甘心就這麼走了,又沒話找話∶ "我干兒怎麼樣啊?"
"的冒鼻涕泡了,又開始到爸爸。上次在食堂還喊盧部長爸爸,然后又給自己認了個干爹,騙了不糖。我現在都不敢帶出去晃了。一轉,就能帶一兜糖回來。"
余聽著吃味。他本來還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爸爸呢,合著是分母呀。
周秋萍覺這樣說的好像兒很沒良心的樣子,就趕替小丫頭找補∶"我出門時倆還想跟著,就是天太冷了。等禮拜天,要是天好的話我再帶們過來看你。"
說著,站起,,將床頭柜上的東西收拾整齊,叮囑余注意,就轉離開了病房。
盧振軍從樓上下來,他來探邊的老領導。瞧見周秋萍的背影,他原本想喊住對方,想想又覺得大晚上的高門大嗓不合適。
算了,反正醫院距離家屬區也不遠。這邊三步一亭五步一崗,倒不用擔心安全問題。
既然來了,他也去病房看看余吧,順便和他分個好消息。請功報告送上去了,不出意外的話,一個三等功跑不了。
其實讓余跟自己到后勤來搞三產,實在是屈才了。但沒辦法,眼下的況就這樣,他們必須得想辦法掙錢。
當年新四軍在江南,不照樣得做生意養活自己嗎?他們這也算繼承了優良傳統。
盧振軍進了病房,瞧見余,吃驚不小∶"你于嘛呢?大冷的天,你可別仗著自己年輕就不當回事。"
余站在窗戶邊上,眼睛還盯著外面看,隨口回道∶"沒什麼,我躺著難。"
盧振軍好歹也是上過戰場,見過生死的人,一雙眼睛敏銳的很。
他很快就發現余到底在看什麼了,窗外,周秋萍正朝醫院大門口走。
他瞬間震驚,難以置信地瞪著自己的下屬∶"你小子,該不會?"
余口而出∶ "離婚了,是單,我沒搞破鞋。"
盧振軍倒吸一口涼氣,手指頭都料了∶"你小子來真的?你可要考慮清楚,還有兩個孩子呢。"
"青青和星星都很可,們我爸爸呢。
說話的時候,他驕傲地起了膛。
盧振軍還是接不了∶"你等等讓我緩緩,你那是放衛星,你這是放炸.彈。"
簡直把他炸得差點兒就灰飛煙滅。
他還以為這小子是個正經人呢,所以才敢派過去跟同志一道進進出出。他本想著秋萍好歹已經是當媽的人,忌諱相對一些。
結果沒想到,兔子還是盯上的窩邊草。
這臭小子,有賊心還有賊膽。
搞得他都被了,不知道該怎麼收場。
猜你喜歡
-
完結628 章

攜空間穿七零:她帶全家賺物資
【空間靈泉丹藥兵器男女雙潔爽文】 21世紀全能女戰士蘇若瑾,上得廳堂,下得廚房。 萬萬沒想到,在一次做飯中因不小心割破手指穿到70年代,還好隨身空間跟著來了…… 上輩子已經活得這麼拘束了,這輩子就好好生活,做個溫柔的美女子! 且看她如何帶著家人賺錢! 如何撩到硬漢! 作者有話說:文中開始極品多,後面幾乎沒有了,女主也是有仇慢慢報的人,各位集美們放心哈,極品會處理的,有仇也會報的喲!
109萬字8.18 130283 -
連載1364 章

重回1982小漁村
【這是一個海邊人的日常小說!沒有裝逼打臉,只有上山下海的快樂!年代文,日常,趕海,上山,養娃,家長里短,不喜勿入,勿噴!】葉耀東只是睡不著覺,想著去甲板上吹吹風,尿個尿,沒想到掉海里回到了1982年。還是那個熟悉的小漁村,只是他已經不是年輕…
476.7萬字8 28616 -
連載1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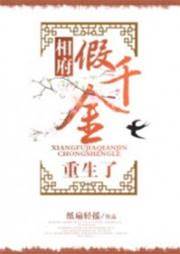
相府假千金重生了
蘇靜雲本是農家女,卻陰差陽錯成了相府千金,身世大白之後,她本欲離開,卻被留在相府當了養女。 奈何,真千金容不下她。 原本寵愛她的長輩們不知不覺疏遠了她,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婿也上門退了親。 到最後,她還被設計送給以殘暴聞名的七皇子,落得個悲慘下場。 重來一世,蘇靜雲在真千金回相府之後果斷辭行,回到那山清水秀之地,安心侍養嫡親的家人,過安穩的小日子。 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傳聞六皇子生而不足,體弱多病,冷情冷性,最終惹惱了皇帝,失了寵愛,被打發出了京城。 正在青山綠水中養病的六皇子:這小丫頭略眼熟? 內容標簽: 種田文 重生 甜文 爽文 搜尋關鍵字:主角:蘇靜雲 ┃ 配角: ┃ 其它: 一句話簡介: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立意:
38.3萬字8 9087 -
完結344 章
絕世仙婿
渡劫期大修士重生為豪門贅婿! 他潛心修仙,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止,各方勢力來勢洶洶,草莽權貴虎視眈眈,他該如何應對? “動我親友者,天涯海角取項上首級!” ——劉青。
71.3萬字8 29020 -
完結48 章

史上最強腹黑夫妻
牧白慈徐徐地撐起沉甸甸的眼皮,面前目今的所有卻讓她沒忍住驚呼出聲。 這里不是她昏倒前所屬的公園,乃至不是她家或病院。 房間小的除卻她身下這個只容一個人的小土炕,就僅有個臉盆和黑不溜秋的小木桌,木桌上還燃著一小半截的黃蠟。 牧白慈用力地閉上眼睛,又徐徐地張開,可面前目今的風物沒有一點變遷。她再也顧不得軀體上的痛苦悲傷,伸出雙手用力地揉了揉揉眼睛,還是一樣,土房土炕小木桌••••••
14.5萬字8 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