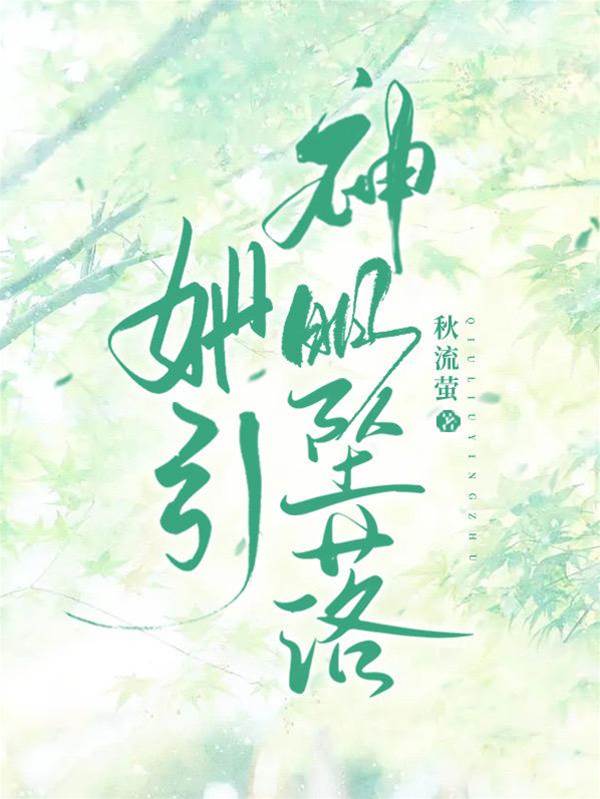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穿成女兒奴大佬的前妻》 第17章 第十七章
江做了這麼多菜, 原本還擔心吃不完,想著要不要把周建也過來一起吃。
黎宵懶得去跑一趟,“我一個人能吃完。”
行吧, 那就他們兩個吃, 反正現在天不熱,吃不完留到明早繼續吃。
最后,兩個人確實是吃完了, 不過也撐得不行,江在院子里整整走了二十多分鐘才消食了些。
在院子里散步的時候,黎宵就將買來的鎖裝到門上去,然后把晾干清漆的新門安裝上,開門關門試試,剛剛好。
門用的木板厚實,上面被他刻了花紋,瞧著還好看的,他還用剩下的木料做了兩個掛蚊帳的鉤子。
雖然現在天氣涼爽了些,但江也沒有將蚊帳收起來, 總擔心半夜有蟲子爬到床上來,前幾天就聽王嬸說住在后面的林大叔半夜被蜈蚣咬了。
不說別的, 就是江也不了一到半夜家里就有蟋蟀, 吵得人腦殼子疼,關鍵是白天怎麼找都找不到。
很擔心哪天鉆床上來了。
黎宵裝完門也沒歇著, 把院子里的工搬到堂屋燈下, 開始給孩子做搖床。
他旁還放著一張凳子,上面是紙和筆, 江怕他做的不好看, 給他畫了樣式, 但只畫出了大致的樣子,的還需要他自己來研究。
所以他是一邊做一邊自己畫,神沉靜認真。
都說燈前玉、月下人,江走近的一剎那,就覺得燈下的他似乎也更好看了。
長長的睫在俊的臉上投下一片影,鼻梁拔,薄輕抿,致的臉龐在燈的照映下忽明忽暗,有時讓人看得不夠真切。
他微微弓起長軀,上半,襯衫被進子里,顯得腰削瘦,襯衫長袖被他擼了起來,小臂線條優,下面長一只彎曲踩在長條板凳上,一只隨意展著落地,過分修長。
Advertisement
江抱著肚子都不忍心打擾他,便繞過他去廚房了。
忙到十點,兩人躺在床上。
江中午一覺睡的有點長,這會兒沒什麼瞌睡,就問起黎宵白天吃飯的事。
其實對他那幾個兄弟還好奇的,據當初來過他老家的警局大哥說,黎宵在鄰居中的口碑不是很好,但在他朋友眼中,都說他是個很仗義的人,靠得住。
年紀比他大的,都愿意給他當小弟。
黎宵不是個話多的人,哪怕跟幾個朋友在一起,他說的話也不是很多。
但現在的江不是很怕他了,見他不出聲,就沒忍住多問幾遍。
最后他簡短說了幾句,“朱強被他馬子在半路上走了,沒來,然后我們點了幾道菜,喝了幾瓶啤酒。”
“哦,對了,他們說你做的爪很好吃。”
干的語氣,說的一點都沒有。
黑暗中,江沒忍住翻了個白眼。
黎宵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補充了一句,“金大友家里還有一些筆記和試卷,你要的話,我讓他拿過來。”
沒提是自己主開口要的。
江也沒多想,聽了心舒坦很多,覺得他這個金大友的朋友比他多了。
便道:“當然要,對了,你這個朋友他考的是哪個學校?”
“省會的醫科大學。”
“那好厲害。”在江眼中,學醫的都是神人。
“你們是從小就一起玩嗎?”
“也不是,金大友比我們小四歲。”
江奇怪,“那他念書早的。”
“嗯,他家里窮,跳過幾次級。”
大概是嫌江問來問去的煩,干脆就把金大友家的事說了,“他上面原本還有個哥哥,比他聰明些,跟我是同歲的,不過后來丟了,他父母因這事互相埋怨分開,之前一直找,前兩年他爸放棄了,在外面重新娶了老婆,他媽不清楚,不過都沒回來過。”
Advertisement
那時候林如還在工廠上班,廠里建了一所小學,黎宵就是在那里認識的金大友哥哥,金大友父母當初是廠里的臨時工。
那時候,黎宵和金大鵬年齡都不到,但績卻是最好的。
怎麼被拐的黎宵不太清楚,好像是夫妻倆從岳父岳母家回來路上吵架,一時沒顧得上孩子丟了,那天早上金大友吃壞了肚子沒跟著去,不然很可能都丟了。
江聽了心里難,知道,八、九十年代是人販子最猖狂的時候。
還記得當初剛去實習時,和隊里的同事一起吃飯,聽到他們聊就在一周前,他們抓到的一個犯人是小時候被拐賣的,他的親生父母后來發家了億萬富翁,可惜幾年前出車禍意外去世了,死在了尋找他的路上,家產全都留給了名牌大學畢業的養子。
而他的養父母,在買了他兩年后生了一個兒子,從此就不疼他了,家里又很窮,念完小學就讓他出去打工,吸他的,供完弟弟的學費后父親又生病了,最后他誤歧途當街搶劫,不小心把人捅了。
一直到進了局子里都不知道自己不是親生的。
還是隊里的一個大哥發現他長得和幾十年前一個被拐兒的照片很像,才注意到了。
聽說那個犯人知道真相后,三十多歲的他痛哭的像個孩子,一邊哭一邊說“他們毀了他”“他的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
而這只是無數個被拐兒的影,甚至更慘的都有。
也是在那一刻,江清楚意識到,社會比學校殘酷多了,很幸運的安全長大,邊也一派祥和。
江了自己的肚子,心里暗暗發誓,只要沒穿回去一天,就會好好照顧這個孩子,不僅要預防以后上學被霸凌,還要警惕來自別的意外。
Advertisement
見側的人不說話,黎宵以為是被自己嚇到了,清了清嗓子,然后翻過也手去肚子。
大手不小心搭在了江的手背上,溫度有些熱,還有些糙,江不自在的想要出來。
但黎宵沒讓,還收握住了,“這幾天孩子乖不乖?”
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像是在耳邊說的一樣,讓江更加別扭了,了子,試圖離他遠一點,里敷衍道:“還行吧。”
男人沒覺得哪里不對,里輕輕嗯了一聲,“睡吧。”
接下來的幾天,黎宵就在家里做搖床和推車,做完也沒歇著,而是拿著把尺子量對面的房間,那房間原本是黎宵爺爺住的,他爺爺不在后房間就一直空著。
江平時在家,幾乎沒進去過。
他量完后又出去了幾趟,從外面推回來一些水泥、鋼筋和一些瓷磚。
江一問,才知道他準備把這個房間改造浴室。
聽后還有些擔心,“你一個人行嗎?要不要請幾個人。”
他沒搭理,口中銜著一只筆,一手拿著本子,一邊用尺子在規劃著什麼。
于是江就不打擾他了,隨他折騰去。
金大友回學校前過來了一趟,江看到了人,長得很瘦,個子高高的,似乎很笑,從進門到離開,臉上笑容就沒落下來過,眼睛彎彎,雖然長得不是很帥,但讓人看了很舒服。
難怪黎宵說他到哪兒都吃得開。
他送給江幾本筆記本和一些試卷,還給說了一些學習方法。
江為了謝他,將家里新做的辣椒醬給他裝上兩瓶,看得黎宵老大不樂意了。
這是他吃的,平時吃面就要拌上兩勺。
金大友笑嘻嘻接了,一點都沒客氣。
Advertisement
黎宵干活的速度驚艷到了江,印象中搞裝修那些都需要技工,就像以前家里浴室燈壞了,他爸信口雌黃說自己來換,省錢,然后換了一個禮拜都沒換好,最后沒法子只得花錢請人。
而這次,江就看著他給房間屋頂裝上了天花板,牽了幾電線,又將四周墻壁用鋼筋水泥加固,地面和墻壁刷上水泥上瓷磚。
就是審不大行,瓷磚又是又是藍。
但確實被他弄得像模像樣,這房間原本看著不大,等把里面的床和家搬空后就覺得寬敞的。
改造后進門是洗漱臺,然后是水蹲廁,再往里去,上面有個臺階,那是淋浴的地方。
江最滿意的就是家里多了個廁所,這周圍的房子建造的時間有點久了,用的是街后面那個公共廁所,江每次進去前都要深深吸一口氣,然后憋著那口氣上完。
黎宵又買了一面鏡子放在洗漱臺前,旁邊按照江的意思,打了一個置架柜子。
趁著這個機會,他又買了一個大理石水槽洗池,靠著院子墻安裝。
這個很便宜,他是路過一家賣墓碑的看到了,想著平時洗服蹲著難就買了。
廚房里也裝了一個水槽,不用的臟水可以隨手倒掉。
裝浴室剩下的水泥,他用來把水井給封上,變了水井。
擔心孩子出生后不小心掉了進去,這事發生的概率還高的,連江都聽大嫂說過,說同事婆婆在鄉下帶孩子,跟人打麻將忘神了,等發現孩子不見了時,小孩子已經掉進井里沒氣了。
這事讓記了好久。
江很喜歡他弄的這些,以前沒覺得穿越前的生活有多方便,還是來了這里后才覺老一輩的人生活真的很麻煩,沒有自來水,沒有電飯煲,沒有洗機,沒有電瓶車……
就拿通來說吧,雖然縣城里已經通了公車,但來往并不頻繁,出門一趟很不方便,還特別人,江遠遠看過一次就心里發怵,怕把肚子疼了。
以前出門都是騎媽的小電驢,又快又輕松。
二十年的時間其實并不長,但他們國家的發展確實太快了,這個時候手機都沒有普及,但就在二十多年后,5g都出來了。
江懷念的同時又有些慨,然后跟著黎宵興致的參觀家里新添的東西,順便補充道:“浴室里得添一把拖把,還得買一雙拖鞋,方便洗澡的時候穿,你再打個小架子放在這里,用來掛服和巾……”
黎宵一邊聽一邊用手按墻壁,看有沒有干。
弄完這些,已經到十月中旬了,距離江生產沒幾天了,江也不好跟黎宵說知道自己哪一天生,所以這幾天讓黎宵盡量在家呆著。
好在他也不是天天有事出去,浴室弄完后,他就自己找了點木工活兒,天天在院子里打家。
剩下的木頭料子他也沒扔,做了好幾個帶著趣的小板凳小桌子和一些玩。
其中有個玩是陀螺,江還自己先玩了起來,覺得有意思的,小時候沒玩過這個,不過小學時期有一段時間流行溜溜球。
還拿了哥哥的溜溜球送給同學。
十五號早上,江將給寶寶準備的服被子拿出來曬曬,之前洗過三回,大嫂曾經生小侄子的時候,媽就是這麼做的,說多洗洗能讓服變,不傷害寶寶皮,也防止甲醛那些。
前幾天晚上下了幾場雨,就想著拿出來曬曬,去去氣。
沒想到剛將服攤出來曬,就有人來了。
因為黎宵在家,白天里江就不關院子門,所以人一來就看到了。
婦人中等個子,容貌普通,小鼻子小眼,沒什麼特,不過皮好的,臉上沒有斑,也不黑。
齊耳短發梳得順溜,上穿著黑的舊外套和舊子,腳上一雙老式扣帶布鞋,鞋子似乎穿的有點久,鞋底看著有些薄了,但收拾的很干凈。
跟那個累的有些彎腰駝背、臉暗黃的婆婆相比,這人看著要年輕很多。
婦面容瞧著和氣,看到江的時候還出淺笑,然后挎著籃子走進來親熱道:“想著你要生了,就過來看看。”
江這才后知后覺想起,這是原那個親媽。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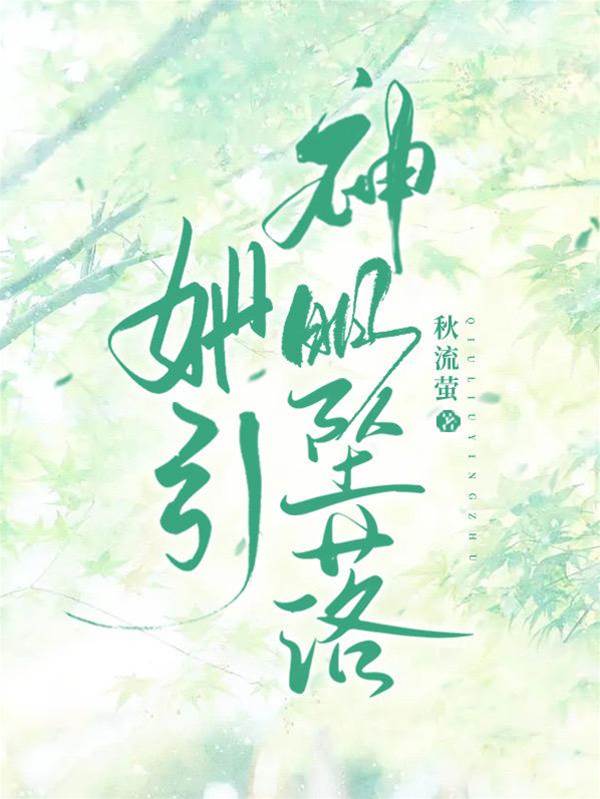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