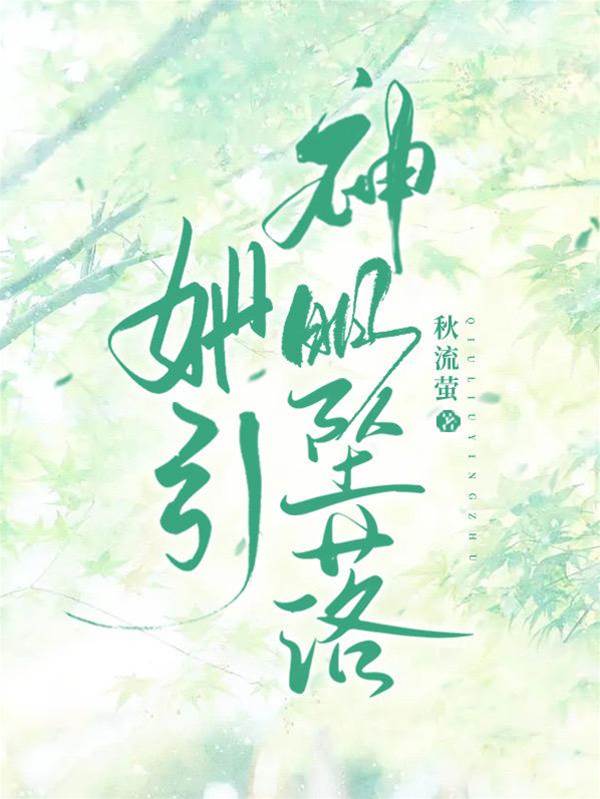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離婚后財閥前夫日夜糾纏》 第9章 甲方乙方
陸恩熙拎著塑料袋,輕輕的,“既然這樣,司請便。你不待見我,我離你遠點。”
司薄年面無表,“陸恩熙,你長了不本事。”
聽得出他在諷刺,陸恩熙回以微笑,“是麼?司倒是收斂不,以你當初的做派,王永春的小舅子恐怕斷得不止一手指。”
那笑容是冷的,眼尾沒,只是將角微微挑開,瓷白的牙齒剛好的弧度。
客觀來說,陸恩熙當然很,皮也好,凡是可以看到的部位都泛著淡淡的白,沿著脖子往下的一路蜿蜒,更是白紅。
司薄年和相親的次數固然不多,仍記得渾令人目眩的凝脂。
只可惜,這人心如蛇蝎,還舉止不端!
拳頭在袖口下一攥,司薄年臉上也籠了厚厚的戾氣,“心疼他?”
陸恩熙也不是什麼圣母心腸,做錯事付出代價,理所當然,只是作為律師,更希施刑者是法律,司薄年替出一口氣,出于面子也好,單純嚇唬也罷,橫豎讓壞人得到報應,但也給他的履歷又加上一筆。
算了,他早就虱子多了皮不。
“他差點燒死我,我還沒善良到那個份兒上。”
司薄年從鼻息里哼出冷意,“善良?”
陸恩熙若是個善良的,他司薄年的名字可以倒著寫。
鬧不清司薄年大晚上跟耗在樓下所為哪般,但小腹墜痛的陸恩熙著實不想再廢話下去,于是潦草道,“司日理萬機,我就不耽誤你時間了,上了年紀早點睡覺,保命。”
Advertisement
再次逐客。
這是陸恩熙第二次明目張膽的趕他走。
手比腦子作快,司薄年一把拽住人纖細的手臂,“罵我老?”
陸恩熙手臂痛,擰眉甩了甩,沒甩掉,“我說我自己不行?”
司薄年目測的臉,沒什麼表彩的評價,“是不年輕。”
陸恩熙只覺得一火蹭竄到腦門,掛著淡似若無的禮貌微笑,聲音明顯是譏諷,“既然司嫌棄,咱們還是減見面比較好,司上的事項你找個助理跟我洽談,省得司看到我影響心,我擔不起罪名。”
司薄年目驟然一涼,沾了冰水似的,“你就這麼回報我?”
回報?
又不是讓他多此一舉找王景春的麻煩。
想想算了,何必跟他繼續拌,“謝謝你。”
司薄年道,“怎麼謝?”
這一問,倒是把陸恩熙給問的不會了,想了想,“好好替你打司。”
司薄年鼻息一哼,“我了你訴訟費還是占了你多大便宜?”
合同條款清楚明白,作為代理律師的,將獲得高于業平均水平的報酬,單是奔著錢就得好好干活兒。
行吧。
以對司薄年的了解,跟廢這麼多話,肯定有大招,挑明得了,“說吧,想讓我做什麼?除了跟你家里糾葛之外,其他的我都會考慮。”
司家人多事雜,一個個眼睛長在頭頂上,陸恩熙吃了數不清的虧,了一籮筐的委屈,如果可以,一輩子都不想見到司家任何人!
Advertisement
“陸律師沒搞清楚甲方乙方?現在是我握著主權,你有資格跟我談條件?明天上午十點,雍景別苑,遲到一分鐘扣一萬。”
陸恩熙以前怎麼沒發現司薄年這麼,他人品是不太過關,至在花錢方面出手極為大方,現在跟一萬一萬的摳,什麼東西?
“好一招公報私仇,算我再次認識你了司先生。”
司薄年松開細到一擰就能斷的手臂,“咱們來日方長吧,陸律師。”
——
雍景別苑不是別的地方,陸恩熙也輕車路,和司薄年婚后來過幾次,看他爺爺。
老爺子膝下三個兒子兩個兒,他誰也不蹭,自己住一棟依山傍水的老宅,晚清時一位貴族的府邸,奢華氣派,絕對的文化保護單位。
下車,陸恩熙踩著高跟鞋往里走,得繞過一條狹長的林蔭道,走著走著停下腳步,目被路邊的秋千架吸引。
“老公,你幫我晃晃啊,讓我一會兒。”
那時,滿臉膠原蛋白青春活力的陸恩熙,坐在秋千架上,仰頭張司薄年,后者雙手袋,一副不認識的樣子。
“你多大了?”
陸恩熙撇撇,聲氣的撒,“就一下嘛,小時候都是我爸陪我玩,今天你陪我嘛。”
司薄年冷著臉,“這麼想玩,回家找你爸。”
陸恩熙還想撒,司冠林背著手走來,“薄年沒別的事可做,一天到晚哄你玩?”
Advertisement
老爺子矍鑠的目深不見底,落在哪里都像下冰雹。
陸恩熙跳下秋千,乖乖的挨近司薄年,輕聲細氣道,“爺爺……”
司冠林蹙蹙眉,十分不滿的稱呼,“薄年跟我來。”
陸恩熙絞著手跟司薄年,還沒走到別墅正門,又聽到老爺子說,“你來干什麼?”
一句話把陸恩熙說的進退兩難,尷尬的杵在那里,向司薄年求助。
司薄年上了一級臺階,俯視臉漲紅的小人,“不是想玩?去玩個夠。”
說罷轉就走。
陸恩熙眼眶一熱,管不了傭人是否看到的狼狽,淚水忍也忍不住的流滿小臉。
此刻,無聲笑笑。
都說年無知腦,真恨不得回到六年前狠狠扇自己一掌,司薄年那張冰山臉,到底哪兒值得你這麼作踐自己得死去活來?
——
“陸小姐?”
傭人認出陸恩熙,遠遠的打招呼。
陸恩熙換了個自然松快的表,“陳姐,好久不見。”
這位陳姐陳娟,五十來歲,是司冠林的保姆,負責他的飲食起居,人收拾的干凈利落,歲月在臉上留下痕跡,算不上多好看,但勝在溫。
是雍景別苑唯一對陸恩熙笑臉相迎的。
陳娟環視四周,這才走近幾步,“這幾年你過的好不好?怎麼瘦這麼多啊?”
陸恩熙和司薄年離婚的事外界不知,傭人也是幾個月后不經意從主人的對話里得知的,什麼凈出戶、名聲掃地,陸續到他們耳中。
Advertisement
其他人私下里都議論說陸恩熙婚出/軌才被踹的,也有人說陸家破產想拖累司家,司家不當冤大頭,還有人說陸恩熙的大哥得罪了司薄年,總而言之,陸恩熙是個禍。
陳娟不那麼認為,所認識的陸恩熙善良可,是個好姑娘。
陸恩熙揚起角,“最近在減,效果這麼好嗎?”
陳娟心里一酸,“這麼瘦了還減?胖點不是更有福氣啊?小臉兒掌大,再減就沒了。”
陸恩熙沒接話,陳娟接著低聲音說,“你今天來,時機不太對,老爺子發脾氣呢,從昨天晚上就鬧緒,把所有人罵一遍,沒看到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嗎?”
陸恩熙心說,要不然司薄年也不會讓我來。
猜你喜歡
-
完結3328 章

先婚後愛:BOSS輕點寵
她以為離婚成功,收拾包袱瀟灑拜拜,誰知轉眼他就來敲門。第一次,他一臉淡定:“老婆,寶寶餓了!”第二次,他死皮賴臉:“老婆,我也餓了!”第三次,他直接撲倒:“老婆,好冷,來動一動!”前夫的奪情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驚情。“我們已經離婚了!”她終於忍無可忍。他決然的把小包子塞過來:“喏,一個不夠,再添兩個拖油瓶!”
591.3萬字8.46 320926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3019 -
連載1815 章

枕上歡:老公請輕點
唐慕橙在結婚前夜迎來了破產、劈腿的大“驚喜”。正走投無路時,男人從天而降,她成了他的契約妻。唐慕橙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無聊遊戲,卻冇想到,婚後男人每天變著花樣的攻占著她的心,讓她沉淪在他的溫柔中無法自拔……
318.3萬字8 35129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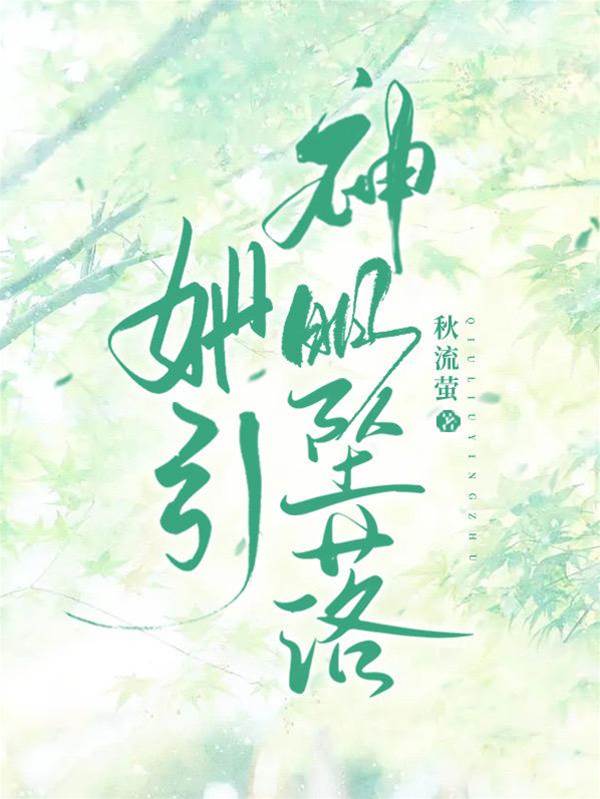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91 章

你有男閨蜜,就不要纏著我了
結婚前夕。女友:“我閨蜜結婚時住的酒店多高檔,吃的婚宴多貴,你再看看你,因為七八萬跟我討價還價,你還是個男人嗎?!”“雖然是你出的錢,但婚房是我們倆的,我爸媽可
33.3萬字8.18 2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