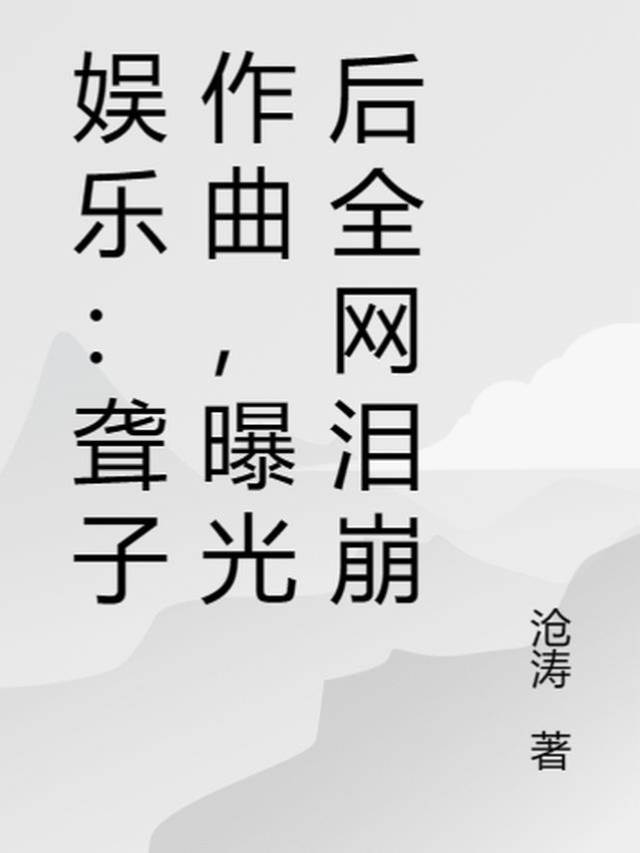《黃雀雨》 第16章 #16
#16
校區很大,校車和自行車是最普遍的通工。
夏郁青不會騎車。
老家水泥路只從縣里通到鎮上,山路崎嶇,自行車自然派不上用場,寥寥幾戶有托車,大部分人家還是得靠步行。
南城大學的校車分兩種。
一種是校際大,通新老校區,單程一小時。班次不多,因為師生更傾向坐地鐵。
一種是校校車,走大環線,串起教學樓、圖書館、食堂和宿舍等,上下課的高峰期趟趟滿載,本不上去。
現在是中午午休時間,夏郁青功在育場這站搭上前往校門口的校車。
在靠窗位置坐下,打開了車窗,從包里出耳機-手機,點開音樂件。
后背被人輕拍一下。
夏郁青摘下耳機回頭,坐后排的生說有點冷,麻煩將窗戶關小一點。
夏郁青趕說“抱歉”,正要回頭關窗,目略過過道另一端倒數第二排靠窗位置。
意識到什麼,愣了一下,又立即轉回去。
那里坐著一個男生,白上,外搭一件油白燈芯絨的外套。
此刻,他正向這邊。
兩人目相會,夏郁青笑著沖他點了一下頭,當做打招呼。
蘇懷渠也笑了一下。
夏郁青轉關上了車窗。
校車上偶遇,這麼小概率的事,心多有些激。
要是平時,一定會過去跟蘇懷渠多聊兩句,但此刻醞釀了一下,似乎難以提起心。
算了,下次吧。
夏郁青將耳機塞回耳朵。
下一瞬,余瞥見,旁邊座椅靠背,一只手借以支撐地抓了一把。
隨即,那影往前一步,在旁邊的空位上坐了下來。
“你好啊。”蘇懷渠笑說。用的是上次的句式。
Advertisement
夏郁青摘下耳機拿在手里,笑起來,“你去哪兒?”
“去校門口買幾本雜志。你呢?”
“我去坐地鐵……進城吧。”
新校區學生不約而同地把去市中心這件事稱之為“進城”。
“下午沒課?”
“翹了。”
“你看起來不太像是會翹課的人。”蘇懷渠說。
“好學生也不是人人都不翹課的。”
兩人都笑了。
夏郁青說:“你‘進城’次數多麼?”
“不算多。怎麼?”
“嗯……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一個人逛一逛打發時間,放松心?除了商場、公園和書店。”
蘇懷渠認真地想了想,“老校區去過嗎?可以去逛逛,很安靜。”
夏郁青去過一次,但是是過去辦事,便說:“謝謝推薦,我去逛一逛。”
“校西門有家蔦蘿咖啡館,環境還不錯。”
夏郁青點頭記下。
他們沒能展開聊得太多,校車很快到了校門口。
夏郁青去換乘校際士,蘇懷渠要出校,便就在站點告別。
校際士十分鐘后發車,車上統共五個人。
夏郁青坐在后排靠窗位置,聽著音樂,在晃晃悠悠中睡著了。
*
陳叔陳佑平“自愿”退居閑職,只在公司掛個虛名。
年后陳佑平派系的人,有的仍舊留在公司,有的選擇出走,又一人事關系更迭震,漸漸平息之后,SEMedical總算初步達陸西陵所要求的上下一心。
研發部門走了三個人,亟需補充新鮮。
生、化學和醫學叉領域的相關研究學者舉辦學論壇,陸西陵和研發部負責人汪老師同去,一為聽取前沿報告,二為開拓人脈。
論壇在南城大學老校區生科院的報告廳舉行,持續一天半,今日中午結束。
Advertisement
結束之后,汪老師請過去的幾位同儕吃頓便飯,聯絡之余,也傳達了求賢若的期許,和SEMedical資助科研項目的意愿。
這頓飯陸西陵沒出席,他知道學者們多有傲骨,見不得商人的一銅臭。
他自己去了地質學院,順道拜會父親陸頡生的恩師。
新校區建以后,所有專業都遷了過去,老校區只保留著幾個老牌專業的院辦。
這些辦公樓并不做教學與辦公使用,大多只為了還原民國建校時期的原始而貌,此外再發揮一些資料檔案館的作用。
南城大學的老牌專業主要為理、數學、文史等,地質學是其中之一。
陸頡生的恩師退休以后,不再授課,只做些考證和資料整理的工作。
陸西陵請老教授在學校附近的一家老飯店吃了頓便飯,將人送回院辦,隨即坐車離開。
車從西門出去。
陸西陵坐在后座,里銜煙,手掌半攏著打火機,低頭湊攏點燃。
窗外一景一閃而過。
他頓了一下,司機停車,往回倒幾步。
隔窗去,一家XX手作茶店前,站了兩個生。
高個的那個手里端著碗章魚丸子,正低頭揪著自己牛角扣大里的下擺;矮個的那個生,拿著紙巾手忙腳地給高個生拭。
芝士蓋茶迎而潑了一的慘烈事故。
片刻,高個生擺手做了個“算了”的作,矮個生退后,連連鞠躬道歉,而帶歉意地轉走了。
高個生揪住又看了一眼,肩膀微塌,神頹然。
片刻,往垃圾桶的方向走了幾步,但又停下了下來,表似在“扔了吧”和“不能浪費糧食”之間來回糾結。
最終拿起竹簽一叉,以就義姿態,把紙盒里剩余的兩粒丸子接連塞進里。
Advertisement
陸西陵看到這兒,才將車窗落下。
生目看過來,表僵在臉上,像是徹底噎住了。
這一陣陸西陵沒主聯系夏郁青——既然已經適應了學校,一切按部就班,也似乎如所言,正積極青春。
他這名義上的“長輩”,也沒什麼再過度關注的必要。
說穿了,兩人只是過去時態的資助者與被資助者的關系。
但此刻見這麼狼狽,又好像不能坐視不理。
陸西陵招了一下手,“上車。”
夏郁青艱難咽下了章魚丸子,怔怔地說,“……陸叔叔你怎麼在這兒。”
“上車再說。”
“我服臟了,怕弄臟……”
“臟了就臟了——趕過來。
夏郁青將紙盒和竹簽扔進垃圾桶里,走過來拉開車門。
甜膩的芝士和霜的香味充斥空間,白上一團黏稠污跡,七八糟的,跟的神目一樣狼狽。
“怎麼了?”
夏郁青搖了搖頭。
陸西陵盯看了片刻,先將煙熄了,稍稍側坐朝向,垂眸打量。
從抿微微下垂的角,到不知是否凍紅的鼻尖,再到黯淡的眼睛。
早立春了,今天也沒那麼冷,顯然就不是凍的。
他剛準備細問,車到了路口,司機打斷一句,問他是不是仍舊去公司。
陸西陵問夏郁青,“要不要回學校?”
夏郁青搖頭,“我就從學校跑出來的。”
陸西陵沉片刻,吩咐司機回公寓,隨即拿出手機,發了幾條消息。
鎖屏之后,再看向,“就你一個人?”
“嗯。下午有課,我翹課出來的。”
陸西陵有兩分意外,“不錯。越來越有出息了。”
夏郁青被逗得終于笑了一下。
陸西陵這才問,“又跟室友鬧矛盾了?”
Advertisement
夏郁青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我好像太沒用了。”
“這話讓陸笙聽見,會以為你在反諷。”
夏郁青一下就笑出來,“……可我好羨慕笙笙姐。”“羨慕做什麼?羨慕是個真正沒用的廢?”
“……不要這麼說。”
“那你說,怎麼了?”陸西陵意識到,自己竟然出奇的有耐心。
夏郁青嘆口氣,煩躁地撓撓額頭,“我今天好倒霉。在學校被室友舉報了貧困生補助資格;坐校際士半路上拋錨,司機把我們趕下車讓我們自己去坐地鐵;然后,同學推薦的咖啡館今天關門;隨便買的章魚丸子難吃死了;哦……還被人潑了一的茶!”
陸西陵聽得好笑,怎麼的麻煩事都是串來的?而且,后而那幾件能跟第一件相提并論嗎?
“誰舉報的?學校什麼反應?”陸西陵準抓住重點。
夏郁青簡單復述事經過。
“放棄就放棄了。”陸西陵聽完,肯定了的做法,“這種機械的舉報反饋機制,不值得你浪費時間妥協和說謊。”
“……但總覺得好像就是向惡意屈服了。”夏郁青低聲說,“我難過這個。”
“沒聽過一句話嗎?流水不爭先。”
夏郁青點頭。
流水不爭先,爭的是滔滔不絕。
“你往后前程萬丈,別被一時勝負心絆住。”
陸西陵做的是跟人打道的工作,管理、統、合作、競爭……不同對象,不同方式,不同態度。
見得人越多,越知道夏郁青這樣的品有多珍貴。
就像自己說的,干干凈凈、郁郁蔥蔥的一株青稻苗。
即便有什麼會使彎腰,那也該是結穗后沉甸甸的謙虛。
夏郁青彎眼而笑,看著他,“我什麼時候才能有這樣的能力?”
“嗯?”
“隨便兩句話就可以說到人心里去。我好像一下子就不難過了。”
“是嗎?”陸西陵挑挑眉。
他無端覺得幾分憾。
是緒太穩定,所以顯得太好哄。
他的耐心其實還夠他多哄兩句。
南城市中心而積不大,陸西陵住的公寓在核心地段,離老校區不遠,開了沒一會兒就到了。
夏郁青方才沉浸于自己的思緒,沒去分辨,乍聽耳,自把陸西陵說的“公寓”理解為了要送回清湄苑那邊。
等自識別的攔桿抬起,車駛小區,映眼簾的是幾乎高聳云的公寓大樓,才反應過來。
眼睜睜看著車開進地下車庫里,還是沒敢開口問,這是去哪兒。
車倒停車位,陸西陵拉開了他那一側的車門,說了句,“到了。”
夏郁青了兩下才扣住拉手。
只覺得張,卻不知道自己在張什麼。
下了車,提著帆布包,跟在陸西陵后,朝電梯走去。
他今天穿著一正裝,風搭在臂間。
三件套的黑西服,并不是全然的黑,更近于深灰深到了極致,越簡單的反而越襯他,一種毫不費力的清峻與貴氣。
夏郁青抬眼著他孤松茂立的拔背影,一瞬間趕把自己的思緒拽回來。
這似乎不該是關注的東西!
電梯里銀廂轎可鑒人。
陸西陵往前瞥一眼,映照出的影離他遠遠的,遠到了另一端,低垂著腦袋。
他微微蹙眉。
夏郁青沒注意樓層,“叮”的一聲之后,門打開,陸西陵出去了,也就跟著出去。
走廊安靜得如同真空,燈明亮,大理石地而顯出一種不敢落腳的干凈。
陸西陵停了下來,大拇指在鎖上指紋識別區,“嘀”聲之后,推開了門。
玄關落塵區放著一雙布袋裝著的拖鞋。
陸西陵拆了之后,扔到腳邊。
換鞋走進去,一眼只覺得空間異常空曠,如寂靜廣闊的,黑白灰三的沙漠。
來不及細看,陸西陵拿起置柜上整齊疊放的,一把塞到手里,“洗個澡,把臟服換了。”
他抬手指了指浴室方向。
夏郁青趕照做。
浴室空間極大,外間是換間。
把外套和都了下來,在打底衫之前,又頓了頓,再去了門把手,確認自己是鎖上了。
陸西陵坐在客廳里煙。
水聲響起時,他起去了臺。
今天沒太,灰蒙蒙的天,這一側落地窗能看見江景,但看多了也乏善可陳。
他盯著江上的船只,好長時間,似乎一不。
煙不知不覺完了。
水聲也停了。
停了很久,人沒有出來。
又等了十分鐘。
擔心是不是浴室地摔倒了,或是什麼設施不會用,陸西陵還是走了過去。
他敲了敲門。
里頭傳出聲音,“……馬上出來!”
很近,就在門后。
片刻,門打開了。
一室水汽撲而而來,穿著干凈衛和衛的夏郁青,肩上搭著一塊干巾,頭發尚在滴水,臉似是被熱氣熏得通紅。
“陸叔叔……”聲音小得幾不可聞。
“怎麼了?”
“……附近有便利店麼?”
“有。要買什麼?”
“我自己去……”耳朵紅熱,像要滴。
“你把頭發吹干,我去一趟。”
“我自己去就可以……”
“你不知道路——到底要買什麼?”
陸西陵站在門口,完全擋住了路。
夏郁青又熱又窘迫,只想趕離這個似乎進退不得的境地,“你讓我自己去,拜托……”
陸西陵不理解怎麼這麼執著,但也不勉強了。
去門口拿了門卡給,“出門左轉,兩百米。”
夏郁青點頭,接過卡便要轉。
“等等。”
夏郁青停下腳步,立即意識到自己肩上還搭著巾,就拿了下來。
陸西陵手,替接了過去。
“……謝謝。”
約莫十五分鐘,響起門鈴聲。
陸西陵走過去把門打開了。
夏郁青一只手藏在背后,走進來蹬了鞋,靸上拖鞋。
看了他一眼,手又往后背了背,像是避著他似的。
陸西陵瞧見了一角黑的塑料袋。
頃刻間明白了。
他不聲地別過了目,自己朝著臺方向走去,不再看,只說,“趕去吹頭發。”
其實這沒什麼。
陸笙一貫大大咧咧的,單獨包裝的棉條和口紅放在一起,從包里取用本不避諱。
正常生理現象,也不必避諱。
他聽見腳步聲噠噠噠地往浴室去了。
門關上的時候,他都跟著松了口氣,好像生怕不自在,從而害得他也得跟著不自在。
猜你喜歡
-
完結2195 章
首席的獨寵新娘
一場別有用心的陰謀,讓她誤入他的禁地,一夜之後卻被他抓回去生孩子!父親隻為一筆生意將她推入地獄,絕望之際他救她於水火。他是邪魅冷情的豪門總裁,傳聞他麵冷心冷卻獨獨對她寵愛有佳,可一切卻在他為了保護另一個女人而將她推向槍口時灰飛煙滅,她選擇帶著秘密毅然離開。三年後,他指著某個萌到爆的小姑娘對她說,“帶著女兒跟我回家!”小姑娘傲嬌了,“媽咪,我們不理他!”
431.7萬字8.33 195062 -
連載2605 章

閃婚夫妻寵娃日常
顧時暮是顧家俊美無儔、驚才絕艷的太子爺兒,人稱“行走荷爾蒙”“人形印鈔機”,令無數名門千金趨之若鶩。唐夜溪是唐家不受寵的大小姐,天生練武奇才,武力值爆表。唐夜溪原以為,不管遇到誰,她都能女王在上,打遍天下無敵手,哪知,遇到顧時暮她慘遭滑鐵盧…
445.4萬字8.18 139421 -
完結1277 章

偏執小舅,不許掐我桃花!
整個海城的人都以為,姜家二爺不近女色。只有姜酒知道,夜里的他有多野,有多壞。人前他們是互不相熟的塑料親戚。人后他們是抵死纏綿的地下情人。直至姜澤言的白月光回國,姜酒幡然醒悟,“我們分手吧。”“理由?”“舅舅,外甥女,有悖人倫。”男人冷笑,將人禁錮在懷里,“姜酒,四年前你可不是這麼說的。”一夜是他的女人,一輩子都是。
173.8萬字8.46 39115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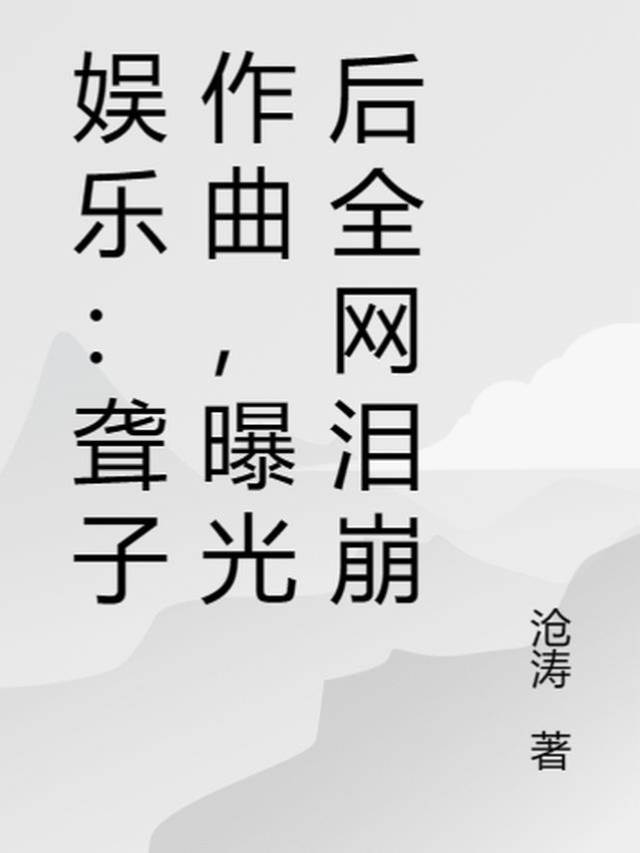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