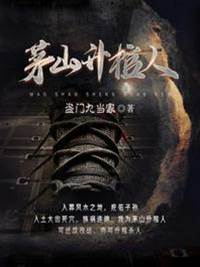《我是千年大棕子》 第二十七章粽子的來曆
張玄是什麼樣的人?
面癱,語言障礙,自理能力傷殘十級,選擇智力障礙,無趣冷漠可能還中二的扶不起青年。
任守是什麼人?
會賣萌,會犯二,會文藝,會吐槽。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得起針線,扛得起沙包。勤勤懇懇熱生活,幽默風趣五好青年一枚(毆)。
一個這麼討厭的人和一個這麼完的人,怎麼會一樣嘛啊哈哈!
“槍哥啊,你這是在罵我還是在誇他呢?”我搖頭,“我們怎麼可能一樣。他要是有我一半的熱生活和積極向上,你們天門早就倒鬥界武林至尊了。”
槍哥有一會兒沒有說話。他看著手裡點燃的香煙,白煙氣嫋嫋上升徐徐消散。過了很久,他才彈了一下手指。
“我來天門比張玄早一年。”槍哥說,“那時候只有我、九叔、舒道和紅搖四個人。我們去甘肅倒一個鬥。過程驚險的,返程途中大家都疲憊不堪。結果就迷了路。”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周圍的景很相似,好像遇到鬼打牆一樣,無論走到哪裡都在兜圈子。無奈之下,只有野外紮營。想到第二天再想辦法出去。可是在當夜,我好像聽到遠有一聲炸聲,那聲音不遠,聽起來就像炸藥開山一樣。好奇之下,九叔和我就去查看況。”
“我們點著火把走了大概兩公裡。因為不清方向,只有順著聲音傳來的方向去。沒留神我一腳踩到了什麼東西,仔細一看,發現是個人。那人大半個子都被碎石塊埋著,不知道遇到了什麼事,渾是,昏迷不醒。他手裡抓著一把刀,昏迷的時候也沒放松過。九叔和我把那家夥抬了回去,發現雖然看上去慘了些,可事實上這家夥都是外傷。簡單包紮之後,傷口的就止住了。”
Advertisement
“第二天帶著這倒黴鬼上路,很奇怪,這次沒花多工夫就走了出去。那家夥愈合能力簡直好得驚人,帶下山後甚至沒送他去醫院,他就醒了過來。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其他的問題,不論我們問他什麼,他都回答不出來。他是誰,從哪裡來,遇到了什麼事,全都不知道。九叔慢慢發現這家夥在對付鬼怪上面很有一套,就把他留了下來。”
我一直聽槍哥講著,問道:“那人……就是張玄對嗎?”
槍哥點了點頭。
原來是這樣。
為什麼對我有些特別,為什麼說我們是一樣的。原來,我們真的是經曆過相同的事。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遇到過什麼事,醒來時遇到的就是完全嶄新的世界。驚人的愈合能力,神的力量,這些都沒辦法彌補心裡那份虛。人都是缺乏安全的,與這個世界的聯系越,越能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可是他沒有父母,沒有親人,沒有記憶。他和別人不同,就像怪一樣。有的只是一個名字,還有那把他從開始就抓著的刀。
我想起張玄無論走到哪裡,手中都一定牢牢抱著那把黑刀。他可能並不是覺得這件東西有多麼寶貝,只是,那是他和自己的過去唯一的牽絆。
三年前,他在墓裡看到我的時候,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哪怕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個怪,依然堅信著自己是人類。所以他才把我帶了出來,然後有了之後的一切故事。
我沉著:“槍哥……從你的故事裡,我猜……哎,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張玄可能是山神的兒子,山神即將分娩,才把你們困到山裡,然後把生出來的兒子給你們帶下山養人,所以你們第二天才那麼容易走了出來的?”
Advertisement
“不錯的想法,”槍哥面無表說,“所以你其實是山神的兒對吧?他只要帶著你兄妹倆回到那座山上祭拜一下,你們兩個的記憶就都能恢複了是不是?”
我哈哈大笑起來。
“你們兩個廢話說夠了嗎?”
這個聲音讓我和槍哥同時打了個寒戰,戰戰兢兢抬起頭來,紅搖一只手叉著腰,一只手拿著皮鞭,瞇起眼睛看著我們,形狀好的櫻掛著一抹冷的微笑。
“……啊,槍哥,你剛才不是和我說到舒道實在是太辛苦了我們要去幫忙來著嗎?”
槍哥心領神會,迅速站起來:“是啊,說的沒錯,我們剛才還在反省作為天門的一員太不稱職來著。”
我跟在槍哥後面,同手同腳走到了離忠犬狀態紅搖最遠的一個角落。
舒道已經坐了下來,他剛才一直沒有停止忙碌,現在額上沁著一層薄薄的汗。看見我,微微一笑。
要知道,我現在可是沒扣帽子的僵臉狀態,對著這張臉還能如沐春風地微笑,舒道的涵養簡直讓我驚歎得五投地。
“舒道,有頭緒了嗎?”槍哥問。
“嗯……雖然並不太確切,但是你們從這裡挖一下試試吧。”舒道指了指一面牆壁,“從下面開始,不用太深,我只是想試一下……”
因為舒道的工作指示聽起來需要細致的人選,所以幹活的人變了槍哥和張玄。為什麼唯一的居然在“細致”這一點被刷了下去……
他們向前掘進的速度並不快,但是還好,並沒有出現土壤掩埋的現象。
“任守,你離遠一點。”九叔對我做出了特別吩咐。
我有些鬱悶的看了他一眼,還是乖乖走了過去。頗為不解地問道:“九叔,為什麼你總不讓我參與很多事……就像之前和那個大粽子搏鬥的時候,為什麼只讓我看著腦袋不讓我參戰?”
Advertisement
“你上有死氣。”九叔說,“張玄告訴過你,那粽子是死,看況能‘複活’的,大半是在那顆腦袋上,用你的死氣著,才不會再過來。”
“哦,這樣啊。”我瞬間覺得自己也是有作用的,“它為什麼會重生?”
九叔無所謂的說:“無論為什麼都沒有關系。有問題的是……那個粽子存在的本。”
“……什麼?”
九叔的表有些深思:“那位元朝將軍,該是這個墓的第一個進者。但是在這個息壤墓中,後來多都變了白骨,卻只有他……依然保持著可行的僵,這簡直就像是……特意留下的一樣。”
特意留下?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起了我們沖這裡之前,那個滾落在墓道裡的粽子腦袋,面對我的臉上出的詭異笑容。
“……像狗一樣。”
“嗯?你說什麼?”
我抖著說:“它……很像一條狗,息壤留下它的骨,把我們驅趕到這個食人坑中。它……它還在笑……九叔,你不覺得簡直就像是息壤留下的一條惡狗嗎?舒道說這裡的土壤是因為食菌才這樣的,它們……有這麼高的智商嗎?”
九叔沒有回答我的話,他的樣子好像陷了深思。
沉默的功夫,槍哥和張玄已經從中走了出來。出乎意料,槍哥的臉沉沉的,看到我們的視線,他搖了搖頭。
“不行,沒挖多遠,旁邊的土又開始……雖然沒有剛才那麼快,但是已經超過了我們挖的速度。九叔,真的不能炸開嗎?”
九叔沒說話,他指了指頭頂,眼尖的我看到,那上面著一點點須子。
“槍哥,你死心吧……看樣子這上面全都是大槐樹,炸一下,一片樹林塌下來。我是沒事啦,至於你……呃,我會好心替你收的。”我好心提醒。
Advertisement
“果然是……不行嗎?”舒道的樣子,好像又陷了思考。
這下子又回到原點了。我不敢去打擾舒道,於是覺得幹脆還是幹點有意義的事——清點戰利品。
即使是這個窮到可憐的墓,按照盜墓一定不會走空鐵律,我們還是撈到了一點東西。大概是:棺材一——這東西大概是給雇主躺驗氣氛用的,跟我沒關系。白骨無數——這跟我也沒關系,紅搖大概會很樂意帶點回去當紀念。還有……哦!傳國玉璽!雖然這依然和我沒多大關系可這是最值錢的!
……不過,玉璽哪去了?
雖然按照常理來看,最應該把這東西視若珍寶的舒道同學應該把它抱在懷裡,可人家表示只有研究的時候才會覺得它是個寶,研究完哪去哪去。這種視金錢如糞土的神大家千萬要好好學習。
我準備把玉璽撿回來,當做任守私人小金庫的第一桶金。
我左右張了一下。發現我們剛才挖時移出的土堆在墓室的一個角落,那裡原本停著的是棺材裡發現的男白骨,已經被吞沒一半了。而玉璽……居然正在他手裡握著。
由此可見,舒道那種寶貴神實在是碩果僅存的,這世道就連死人也會和我們搶東西了。
“你說你都死了還拿它幹嘛?”我一邊咕噥著一邊拼命掰著白骨的手,“下面是沒有當鋪的,拿著也不能當錢……打個商量,我回去幫你燒點行嗎?”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變粽子的原因,我用力的時候有點不控制,一個不小心,把白骨的腕子和玉璽一起卡一聲掰了下來。
“呃……”我黑線地看著手裡的骨手,很猶豫要不要把它重新粘回去,我記得帶的萬能包裹裡好像有瓶502來著……
“任守,你在那邊幹什麼?”槍哥著我的名字。
“哎……就來!”來不及想什麼,手骨的好幾個地方還卡在玉璽隙裡,我直接拿著手和璽一起跑過去。
槍哥一個栗敲到我腦門上,他怔了一下,似乎覺得粽子腦袋手還不錯,接著又彈了一下。
“嘿你還上癮了是吧?”我捂著腦門後退,“你也不嫌這模樣恐怖……我幹嘛?”
“沒什麼,單純看你閑著不爽。”槍哥還真是越來越直白了,他斜眼看了一下我藏在背後的手:“你又拿了什麼?”
我吭哧了半天,還是悻悻地把藏匿的贓拿了出來,小聲嘟囔:“我不是看你們都不要麼……這東西扔了怪可惜的……”
槍哥黑線:“你可真會自己腦補,誰會不要?送上門的寶貝……就算不是寶貝,舒道也會拿回去研究的。”
哎,唯一視金錢如糞土的舒道原來也淪陷了。
槍哥把手骨和玉璽一起搶了過去,轉手給了舒道。還回頭看了我一眼,表充滿了鄙視。
我悲哀地看著被搶走的玉璽,決定回去以後繼續申請漲工資……反正九叔說過只要我能抓住重點就不扣的!
“阿守。”
我鬱悶的扭過頭,發現舒道手中拿著玉璽正向我走來,他的眼睛在鏡片後爍爍發。
“這個……你從哪裡找到的?”
“幹嘛啊……這不就是剛才那個玉璽嗎?”我說,“我真的沒拿其他的了!”
“不……你誤會了,我只是覺得……我有些明白這些泥土生長的了。”
猜你喜歡
-
連載1534 章

東北出馬筆記
一塊紅布三尺三,老堂人馬老堂仙,有朝一日出深山,名揚四海萬家傳! 八十年代,我出生在東北農村,七歲那年大仙說我命犯三災八難,將來會出馬頂香,我不信,卻屢遭磨難。 為了謀生,我當過服務員,跑過業務,開過出租……但命運就像施加了詛咒,我身邊不斷發生各種邪乎事,無奈之下,我成了一個出馬仙。
311萬字8.33 15197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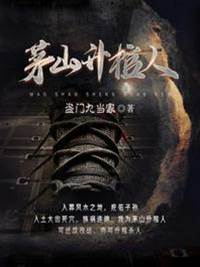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5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