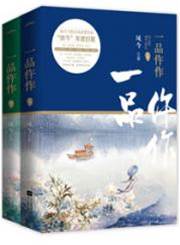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秘密(東野圭吾)》 第七章
與平介在圖書館相遇兩天之後,橋本多惠子帶著五個孩子來醫院了,三個孩,兩個男孩。他們應該是和藻奈關係很好的同班同學吧。
「在電視里看到你的名字,別提有多吃驚了!開始我想是重名吧,但是藻奈的名字很見啊,年齡也和你一樣,看來那肯定是你了。這樣一想,我馬上不知如何是好了,只有哇哇大哭起來。」一看就很好勝的川上邦子說道。臉上的表雖然在笑,不過眼睛已經開始發紅了,這一點平介也看在跟里。可能是獲知事故時的震驚又復燃了吧。
聽了的話,藻奈,也就是直子,眼角也開始潤了。
「是啊……是啊,讓你驚了吧。川上和藻奈以前總是在一起的,對吧?聖誕節那天藻奈還厚著臉皮去你家打擾,回來時你們還送給那麼大的蛋糕……」一面著鼻涕,一面著眼角繼續說道。
「在車上時,藻奈還說要給邦子和其他夥伴買信州的禮帶回去呢。結果沒想到發生了這種事……」
說話的口氣是一個失去了兒的母親的口氣。聽了的話,平介先是覺得眼角一熱,但他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孩子們和橋本多惠子正用奇怪的眼神看著藻奈。
Advertisement
「啊……對,是啊,藻奈。你臨出發前就說要買禮,對吧,藻奈,這一點爸爸也記得呢,是吧,藻奈?」
經平介這麼提醒,假借藻條外表的直子先是一愣,之後馬上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捂了一下。
「啊,對,對。讓你們擔心了,真是對不起。」面向同學,深深地低下了頭。
「已經完全沒問題了嗎?」
「嗯。託大家的福,沒有覺得特別不舒服的地方了。」
「頭痛癥狀什麼的也沒有嗎?我聽說遇到通事故之後經常會有那樣的反應。」
「嗯,從目前來看還沒什麼問題。不過現在還不敢斷定。我也聽說有很多人在通事故后留有後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我以後再也不敢坐雪游大了。」
雖然率人可能覺得說話時已經夠小心了,可是從藻奈口中說出的所有話都與其小學生的份不太相符。橋本多惠子聽了之後也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不過很快又恢復了笑臉。
「聽說你從新學期起,就能來學校了,大家都高興壞了。不過你可不要太勉強啊,覺得不舒服時可以不來。」
Advertisement
「好,謝謝了。您這麼說太讓我了。」
藻奈再次低頭致謝時,旁邊的一個男生捧著花邁前一步:「這是我們送給你的。」
「啊!」直子的臉馬上綻放出了彩。但是接下來的瞬間,的眼神不是投向了鮮花,而是投向了抱著花的年:喲,這不是今岡君嗎?」
年點了點頭,有點迷的樣子。
「哎呀!」藻奈髮出了驚嘆聲,「都長這麼大了!上次見到你還是二年級……」
「好大的花束呀!」平介趕忙一邊去接鮮花,一邊了句話進去,因為又說走了,「這花出院之後帶回家裏擺著吧。哈啥,這花真是太漂亮了,是吧,藻奈?」
「啊?啊,是啊。不過還得買個花瓶。」
對話又持續了一陣,不過藻奈古怪的語氣依舊沒有多大改觀。
看來本人也在努力地用孩子的口吻說話,但越是這樣,反倒顯得越不自然。
很多人給我帶來了問品和鼓勵信,那個……我覺得真的有必要好好謝謝他們,甚至我還直在想,要不要給他們買什麼東西……真的,謝之真的難以言傳……」
Advertisement
小學生會說「難以言傳」這樣的詞嗎,平介一邊想,一邊提心弔膽地聽著。
終於熬到橋本多惠子和孩子們起了。他們走出病房有小一會兒后,平介也悄悄地跟了出去。他們正在等電梯。
「藻奈今天好怪啊。」是邦子的聲音。
「是呀,今天說話就像我媽媽似的。」另一個孩也表示同意。
「那是因為好久沒見面,有些張的緣故。」橋本多惠子說,「再加上之前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所以有些話說不好了。一定是這樣的。」
「哦,是這樣啊。郡真可憐呀。」
聽邦子這麼一說,其他孩子也紛紛點頭同意。
看來他們總算以他們的方式想通了,平介懸在心上的石頭終於落了地,於是又回到了病房。他心裏還是決定跟藻奈,不,跟直子說,要按孩子的方式說話。
平介回到病房前,抓住門把手正要開門,忽然聽見屋傳來了藻奈的啜泣聲。他心中揪了一下,靜悄悄地開了門。
藻奈將臉埋在枕頭裏,正搭搭地哭著。那瘦小的肩膀在微微地抖。平介走近,將手放在了的背上。
Advertisement
「直子。」他呼喊著妻子的名字。
「對不起!」用含混不清的聲音說,「我一見到那群孩子忽然覺得非常傷心。孩子們都不知道藻奈已經不在人世了。一想到這裏,我就覺得那些孩子和藻奈都很可憐……」
平介一言不發地著的後背,因為他實在想不出任何該說的話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