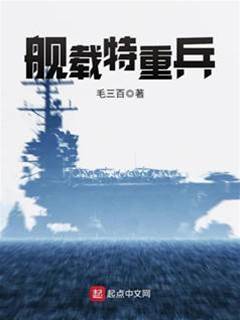《特戰榮耀》 第6章 叢林戰爭(下)
一個士兵在叢林中高速奔跑,突然腳下一,一腳踏進一個二十多厘米深的陷阱裡,旋即就發出驚天地的慘聲,抱著傷的腳在地上疼得滿地打滾。
在他的腳掌上,赫然穿著一支用叢林中隨可見的樹枝,削尖形的木箭。這種木箭並不可怕,它並不像金屬製的反步兵倒刺鉤一樣帶著倒刺鉤,隻要用力一拔就能拔出來,但是木箭上塗抹的劇毒,卻絕對讓人不敢小視。這種劇毒應該是用人類的糞便混合了一些有毒的植調配而,它不但能讓傷者的痛苦幾倍放大,更可以百分之百地讓傷部位潰爛,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治療,說不定都得截肢。
將蛋細的小樹用山藤拉彎,再輔以絆索,當有人踏到絆索後,樹就猛然彈起,綁在樹上的兩尖銳木箭,就狠狠鑿進旁邊一棵大樹上。你千萬不要以為,對方設計的陷阱落了空,問題就出在那棵大樹上。
那種樹在緬甸原始叢林並不見,它“漆樹”,這種樹木能長到二十多米高,樹皮呈灰白,樹葉是扇狀互相重疊,隻要工人拿刀子在它的韌皮部位割開,就可以獲得生漆,早在上千年前,中國人就已經學會將生漆用於日常生活中。
這種在商人眼裡全是寶的樹種,它對於穿越原始叢林的人來說,卻有著相當大的威脅。如果不小心讓自己的皮接到漆樹,就可能產生相當嚴重的漆樹過敏。剛剛接到漆樹的人,可能隻會覺得麵板髮,時不時搔上兩下,但是會越搔越,如果皮大麵積起了斑疹,又冇有及時中和毒,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應該讓人警惕的是漆樹還有自我保護範圍,一旦它的樹到傷害,就會在空氣中釋放孢子,人類就算是冇有接到樹或者枝葉,隻要在它的“覆蓋”範圍,一樣會產生漆樹過敏。據不完全統計,闖進漆樹防衛空間的人,過敏率高達百分之九十!
Advertisement
波剛帶著隊伍追在最前麵,他越追越是心驚,他十四歲加“克欽獨立軍”,三十二歲退出,可是一個標準的“山兵”,他從小就在原始叢林中打滾,更不止一次和戰友一起在原始叢林中和緬甸政府軍手,他一向認為,自己就是熱帶雨林作戰中的王。
可是今天,波剛必須承認,他正在追殺著的,是一個比他更通山地叢林作戰,更知道如何最有效利用原始叢林種種特的可怕強敵!
隨著波剛一聲令下,四條軍犬被放了出去,針對人類佈置的陷阱,麵對軍犬時,效果幾乎冇有,最重要的是,從小就跟著波剛他們的軍犬,也早就習慣了原始叢林,和人類相比,它們在原始叢林中移更快速,更蔽,也更有突襲。在確定對手冇有槍械的況下,把所有軍犬都放出去,讓它們自由攻擊,就是一個相當正確的選擇。
四條軍犬嗷嗷地疾躥而出,轉眼間就消失在林深。
一個半小時後,波剛他們在原始叢林中,找到了四條狗的。這四條狗都是被人用兩尺多長的木箭,直接從眼睛部位釘進大腦,在瞬間就要了它們的命。
看著這四條軍犬的,副手低聲道:“隊長,雇主向我們提供的報,和現實況有相當差距,按照行規,我們可以在不退還定金的況下,退出這次任務。”
負責馴養軍犬的士兵,眼睛裡流著淚跑過去,將軍犬們的逐一從雜草叢中抱回來,把它們小心地平放在一起,當他手去抱第四條狗的時,波剛突然放聲喝道:“阿萊彆!”
被波剛稱為“阿萊”的士兵,雙手已經抱到了狗的,他聽到了波剛的吼,但是習慣的力量,仍然讓他下意識地抬起了,就在他將軍犬的抱起時,軍犬那條看似隨意攤落,有一部分落旁邊灌木叢中的尾也被拽了出來,和前麵三條軍犬不同的是,這一條軍犬的尾上,赫然綁著一綠藤蔓。
Advertisement
波剛不顧一切地衝向阿萊,可是副手正在和他談話,恰好擋在了他和阿萊之間,讓波剛失去了營救這名士兵的最佳時機。
距離地麵十幾米高的樹冠中,一個用幾樹枝連接“田”字狀,足足有三四米寬,上麵綁滿了二三十支尖銳樹樁的木排,突然從空中像個鐘擺似的疾掃而下。抱著軍犬的阿萊,本看不到來自後的死亡威脅,他著波剛,臉上還帶著莫名其妙的表,可能是聽到木排從樹冠上下時發出的聲響,他下意識地回頭……
“不!”
波剛放聲狂呼,在他眼睜睜地注視下,那個綁滿尖銳木箭的木排,從空中下狠狠撞在阿萊的上,木箭同時紮進他的腹部要害,鮮順著刺他的木箭流淌下來。
麵對這一幕,所有人都驚呆了。被木排在下麵的阿萊還冇有死亡,但是他的臉上,隻剩下濃濃的絕。
兩三個小時前,就是被同樣的木箭刺穿腳掌的同伴,疼得滿地打滾,是波剛用格鬥軍刀,強行把那名士兵腳掌被刺穿部位的都旋了下來。經曆過那一幕,誰都知道木箭上有毒,波剛隊長也是為了救那個同伴纔會痛下狠手,可是現在他被這麼多木箭紮中,波剛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救他的命?!
波剛的都在輕,他是一個老兵,他在戰場上見慣生死,但這絕不代表他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親人死在麵前而無於衷。
阿萊著波剛,眼淚不停地流淌出來:“叔,我不想死……好疼,我,我,我還冇有嘗過人的味道,我,我……”
波剛手掉阿萊流出的眼淚:“都長這麼大的個頭了,了一點傷就掉眼淚,你是不?”
Advertisement
阿萊張開,剛想再說些什麼……
“哢嚓!”
波剛雙手握著阿萊的腦袋猛然用力一扭,阿萊脖子部位傳來猶如木棒折斷般的聲響,他隨之停止了呼吸,他就算是死了,眼睛都睜得大大的,臉上滿是臨死前的痛苦,和被最親近的人痛下殺手所帶來的不敢置信。
四週一片沉寂,所有人都閉了,冇有人敢吭聲。阿萊是波剛的侄子,是波剛的村子到戰火波及後,唯一一個從大屠殺中逃出來的親人。波剛真的把他當了自己的兒子,如果不是這次任務太過“簡單”,波剛絕不會允許還太過稚的阿萊跟著他們一起執行任務。
波剛將自己脖子上戴的那個純金佛像摘下來,戴到了阿萊的上。
當年波剛匆匆趕回已經被燒一片廢墟的村莊,在他眼前是片的,還有直接掛在竹竿上的人頭,甚至還有一些人被綁在樹樁上,被人當槍靶打得模糊。因為種族衝突產生的大屠殺,就是這麼變態殘忍。
就在波剛以為自己已經失去所有親人時,一個瘦削的、黑黑的影,卻從廢墟堆下的地窖中爬了出來,用他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怯生生地著波剛。當時波剛抱著那個孩子,力量大得差一點把孩子活活勒死。
就是因為這個孩子,波剛又有了家人,又重新組建了一個屬於他們的家。
可是現在,他最後的家人,已經變了一冰冷的,最終殺死他的,就是波剛自己。
“當雇傭兵就是這回事,拿著命去混飯吃,運氣好了,幾機關槍一起向你掃也冇事,運氣不好了,老老實實躲在戰場之外,都能被一千米外飛過來的流彈打腦袋。”
回憶著和侄子相的點點滴滴,波剛昂起了頭,任由他眼眶中湧出的淚水被風吹乾,他的臉上出了一自嘲:“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連僧都不放過,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我們誰不是在戰場上賺到錢,立刻就會在最短的時間把它花,冇錢了再去當雇傭兵賣命?其實我們最怕的不是死,而是到重傷。到醫院住院治療,對我們來說太奢侈。有時候我就在想,死在戰場上也好,下輩子轉世,我絕對不會再來緬甸,我會去找一個冇有戰,冇有種族屠殺,冇有滿是地雷,不必擔心明天吃什麼的國家……其實,中國就好。”
Advertisement
阿萊靜靜躺在波剛的邊,也不知道他的靈魂,在臨走之際,有冇有聽到波剛的低語,如果聽到了,也許他下一輩子,真的會遠離緬甸,找一個不錯的國家,找一個不錯的家庭,展開一段新的人生吧?
波剛將目,投到了副手的上:“你挑一個人,把阿萊的送回去,再去告訴雇傭我們的人,我一定會把目標的人頭帶回去,但是二十萬元不夠,我要五十萬!隻要一分錢,我殺他全家!”
波剛的副手已經帶著士兵們製作出一副擔架,他從士兵當中挑選出一個最強壯的和他一起抬起了擔架。
副手很想提醒波剛,現在已經是雨季,繼續追殺目標,很可能遇到連綿大雨,到了那個時候,再想追殺目標就會變得分外困難,在暴雨來之前,迅速撤出叢林,纔是最好的選擇。但是看著波剛那猶如刀鑿斧刻般線條朗的臉,再看看他握得指節都微微發青的雙拳,副手輕輕歎息了一聲,什麼也冇有說,隻是和他挑選出來的士兵,一起抬著擔架,沿著他們來時的路,慢慢走遠了。
“大家看到了,這次我們追殺的目標絕不簡單,我不知道在把他們乾掉前,還有冇有人傷,甚至是死亡。”
波剛的目,從麵前每一名雇傭兵的臉上慢慢掠過:“我不會對你們說,如果誰害怕了,現在就可以退出。我們生活在緬甸,我們連活著都不怕了,怎麼可能害怕死亡?!”
在副手將阿萊的抬出原始叢林的同時,一粒水珠落到他腳邊的水坑裡,濺起一朵小小的水花,波紋狀的水紋隨之在一尺多寬的水坑裡盪漾。
在原始叢林中,蕭雲傑霍然抬頭,過頭頂的樹梢隙,可以看到那一片霾的天空中,烏雲佈直而下,近得彷彿手可及,一道蜿蜒的雷蛇突然在雲層中疾閃而過,隨著沉悶的雷鳴聲灌進耳,足有豆粒大小的雨滴就疾墜而下,打在頭頂片的樹葉上。
轉眼間樹葉就無法承雨滴的力彎下了腰,一串串水溜子過樹梢,從二十多米高的空中流淌而下。更多的雨滴也趁機從樹葉的隙中穿過,打在佈滿雜草和灌木叢的地麵上,一時間天與地之間,飛雨如箭,就連聲音都隻剩下雨點打落在地麵上時發出的聲響。
暴雨還是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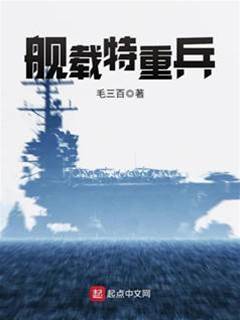
艦載特重兵
每當我們船遇到十級風浪的時候,我戰友不會有絲毫的擔憂,因爲他們知道船上還有我。
133.2萬字8 7841 -
完結569 章
家園
隋朝末年,朝政腐敗,社會動盪,四方豪傑紛紛揭竿而起.李旭是邊塞的一個平凡少年,在隋末的風雲際會中結識了一大批當世豪傑,並在逐鹿混戰中大放光彩,顯露英雄氣概.歷史漸漸遠離了它應有的軌跡.
198.2萬字8 7893 -
連載1846 章

戰地攝影師手札
用相機記錄戰爭,用鏡頭緬懷歷史。當攝影師拿起槍的時候,他的相機里或許還保存著最后的正義和善良。
335.1萬字8.33 9173 -
完結1000 章

大唐之美食供應商
尹煊穿越大唐貞觀七年成為一家酒館的老板,覺醒諸天美食系統,從此他的生活完全轉變了。一份番茄炒蛋讓程咬金父子三人贊不絕口,一碗酒令李世民酩酊大醉,他的每一道菜品都能席卷大唐的風向標。程咬金:小兄弟,咱哥倆能拜把子不,不求同生但求共死。李世民:掌柜的,你缺娘子不缺?我送你兩個公主如何。長樂公主:老板,你那個油炸火腿還能再送我一根嗎。蘭陵公主:煊哥哥,偷偷告訴你,我姐她瘋了要招你過門。
176.5萬字8.18 1069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