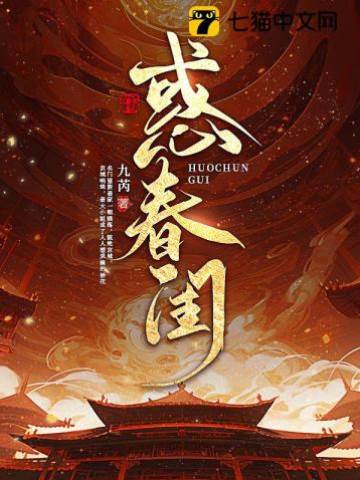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第15章 池邊霧
泠瑯想過很多可能,關于鑄師留下的那三個字。
春秋潭,或許是某湖泊;春秋檀,便是某種沒聽說過的香料;更或許是春秋壇,一只裝了勞什子事的壇子。
那個傍晚暴雨如注,烏云沉沉在天邊,上的蓑已經,連刀鋒都變得淋漓。
在一荒郊破廟中,尋到了鑄師。他躺在地上,就在倒塌的佛像背后。
地上有深痕跡,泠瑯不知道那是雨水還是。走近,聞到土腥中摻雜的腥氣息,看清了地上的人已經很難再稱之為人,便知曉了那是跡,已幾近干涸。
這個曾經親手鍛造出無數神兵利的工匠,在此時已經沒什麼尊嚴可言,那雙手微微著,再也拿不起錘或鉗。
他看著,破碎的嚨發出氣聲,連話語也無法說出。
泠瑯垂目注視他,知道眼前這個人已經很難活到雨停。
說:“我知道你不認識我,但你應該認識這個——”
出云水刀,刀如鏡。一粒雨水順著刀沿出,砸落到鑄師的眼邊,像一滴淚。
那雙渾濁瀕死的眼陡然有了彩,甚至帶著懷念與自滿。泠瑯靜靜地看著,知道他認出了這把刀。
沒有誰會忘記自己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尤其當這件作品歸屬于一個充滿傳奇的人,從此那個人的傳奇便是刀的傳奇,那個人的名聲便也是刀的名聲。
這不能不稱作為一種驕傲。
他凝視著流暢的、完到讓人心碎的刀面。屋外驟雨未歇,來人神莫測,生命正在消散,但他只看著他的刀,像在看一位再也無法得見的人。
Advertisement
泠瑯蹲下來,用刀背上鑄師的臉,想他應該不會拒絕這種親近。
“刀的主人死了,”在雨聲中平靜地說,“因為一把會消失的匕首。”
“有人告訴我,它太過奇異詭譎,很有可能是出自于你之手,我應該來見你……我找了你很久,但或許還是晚了一步。”
“那把匕首大約四寸,柄上嵌著白玉,雕了連綿花紋,像云朵或是水波……我分不清。總之,我推開門看到它,不出兩息的時間……它憑空消失了。”
“你現在看起來很不妙,如果能告訴我那是什麼,我會助你解。”
鑄師沒有第一時間回答,他閉上眼,用沾染了的臉龐冰涼刀面。因為失,他的面有一種奇異的灰白。
良久,他終于開口:“這是一把只能在夜里使用的匕首,它在鑄造之初,便不能見到。”
“不是出自于我,但我認得它……”他費力而嘶啞地說著,聲音像灌滿了風。
“它什麼?”
“春秋談……”
“它是誰的?在哪里?”
鑄師開始止不住地搐,他用一種類似于懇求的眼神看向,只回答了后一個問題:“涇川侯府。”
泠瑯沒有追問,意識到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再去刨問底,未免太過殘忍。
起,重新用刀尖指向他。
鑄師一生中最鐘的作品,終究還是沾上了他的。
而帶著刀的人,離開那個雨夜后踏上了尋找謎底的路途,兜兜轉轉,答案終于顯現在手里。
春秋談三個字被隨隨便便地書寫在陶罐背后,看上去可稱潦草。它被隨意放置在廚房角落,好像也完全不設防。
Advertisement
泠瑯好像看到,一扇沉默的門立在眼前,而的手正扣著門鎖,只需要輕輕一推——
“要放紅豆。”聽見自己說,語氣十分輕快。
將陶罐放回原,沒有表現出任何異樣。
將甜羹送去房間,若無其事地關切攀談,臨走時還心地安了小廝銀錢,鎮定自若一如往常,不會有任何異樣。
只是從那天起,泠瑯便多了一項賢妻之舉——煮甜羹。
用著這個借口,日日出小廚房,很快便同小廚房忙活的下人們絡起來。自然隨意地閑聊,貌似關心地問詢,一點一點試探關于陶罐的事。
將寫著字的紙條摘下收好,只留下罐,假裝疑地問這是哪兒來的。
竟是無人知曉。
好像它就是憑空出現在那里,沒有誰能道出它是做什麼的,又為何被忘在此。
只有灑掃的老仆看了看,又聞了聞,肯定道:“這定是盛酒的。”
阿嬤不信:“我怎聞不到酒味?”
老仆自信道:“因為它早已被喝完。”
“為何你能聞出?”
“倘若你也同我一樣有幾十年的飲酒功力,便也能聞出了。”
眼看著二人要拌起,泠瑯適時打斷道:“那你可能辨認出這是何酒?”
老仆瞇著眼,嗅了又嗅,面上竟浮現出沉醉迷的意味。
“是我從未見過的酒,從未見過的那種……極好的酒。”
泠瑯默然。
謎題更加撲朔了,真相被掩于層層迷霧之后,站在山下,像個等不來青鳥的探者。
直到回了屋,診完脈,大夫笑著恭喜:“夫人已經好轉,無需再日日服藥了。”
Advertisement
也沒有馬上開心起來。
大夫走了,泠瑯撐著下,窗外來去的云。四月初,天氣愈發明亮了。
喃喃:“小廚房曾有誰離開過嗎?”
綠袖說:“有呀,從前有個姓周的廚子,專門負責侯爺飲食。”
泠瑯立即轉頭看。
綠袖一頓,覺得夫人那一瞬間的眼神很可怕。
泠瑯溫一笑,道:“接著說。”
綠袖立即放下異樣,脆聲道:“后來他不在府上了。”
“為何?”
“嗯……好幾年前,侯府辦宴會,是他主廚……二公主嘗了道鹿很喜歡,便將他討走了。”
“他現在在公主府?”
“或許吧,我也不曉得,夫人為何突然關心這個?”
“……就是好奇,”泠瑯依然微笑,“為何先前廚房那幾人沒想到他?”
“因為周伯很難以親近,古怪,并不人歡迎……我那時候很小,他倒經常逗我玩,給我糖吃,現在府上記著他的人沒幾個了吧。”綠袖思索著回答。
泠瑯陷沉思。
又是北坡林,又是二公主府邸……
算是曉得了白鷺樓蒼耳子的難,他說查來查去繞不開那堆難以打探之人,原來一點也不假。
夜又臨。
因為大夫拍案好轉,晚照和晴空重新住到別間去了,泠瑯再次穿上夜行,奔波在林之中。
心里放不下,還是去了北坡一趟,那個高深的不管如何,也要親自確認才放心。
依舊是重重深林,道道哨卡,已經來過一次,輕車路地繞過守衛,往第二道墻深。
Advertisement
一路順利,越往里,心中卻越疑,這也太平靜了些,也不見加強警戒,難道上次鬧出的靜還不夠大?
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高深死了。
那個見都沒機會見的人,費盡心思從白鷺樓換的線索,就這麼死了,在第一次潛此地的后一天。
訃告明明白白地在布告板上,姓名日期,樣樣都有。途徑那里,想看不到都難。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泠瑯在回去的路上反復琢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縱推著一切,而已經深陷于網中。
更奇怪的是,換好服溜回熹園的時候,又上了江琮。
他坐在池邊石凳上,一袍子隨意披著,仍是沒有點燈。形消瘦孤寂,靜靜地著泛著薄霧的池面,不知在想什麼。
泠瑯的腳步很輕,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自己靠近,只知道,原來他在四下無人的時候,出的表一點也不像白天那般溫和煦。
猜你喜歡
-
完結1349 章

逆天廢柴:邪君的第一寵妃
「禽獸……」她扶著腰,咬牙切齒。「你怎知本君真身?」他擦擦嘴,笑的邪惡如魔。一朝重生,她以為可以踏上一條虐渣殺敵的光明大道,豈料,拜師不利,落入狼口,任她腹黑的出神入化,也逃不過他的手掌心中。終有一日,她忍不可忍:「說好的師徒關係呢?說好的不強娶呢?說好的高冷禁慾呢?你到底是不是那個大陸威震八方不近女色的第一邪君?」他挑眉盯著她看了半響,深沉莫測的道:「你被騙了!」「……」
154.2萬字8.18 48848 -
完結478 章

狂傲世子妃
一、特工穿越,一夢醒來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絕境之中,各種記憶跌撞而至,雖然危機重重,但步步爲營,看一代特工如何在宮廷中勇鬥百官滅強敵,譜寫自己的傳奇。我狂、我傲,但有人寵著,有人愛,我靠我自己,爲什麼不能。
84.4萬字8 16632 -
完結264 章

權貴休妻后迎來火葬場
還是公主時眾人眼裡的沈夢綺 皇上、太后:我家小夢綺柔弱不能自理,嫁給攝政王少不得要被欺負了,不行必須派個能打的跟著她。 閨蜜洛九卿:公主她心性單純,孤身一人在攝政王府指不定要受多少委屈,要給她多備點錢財打發下人,那幫人拿了錢,就不好意思在暗地裡給她使絆子了。 通房程星辰:公主明明武力值爆表能夠倒拔垂楊柳,為何偏愛繡花針?難道是在繡沙包,偷偷鍛煉?不行我得盯死她! 攝政王:我家夫人只是表面冷冰冰,私下還是個愛偷吃甜點糖糕的小朋友呢 沈夢綺本人:在越雷池一步,本公主殺了你
53.5萬字8 7964 -
完結77 章

首輔的早死小嬌妻
永安侯離世后,侯府日漸衰敗,紀夫人準備給自己的兩個女兒挑一個貴婿,來扶持侯府。沈暮朝年少有為,極有可能金榜題名,成為朝中新貴,精挑細選,沈暮朝就成了紀家“魚塘”里最適合的一尾。紀夫人打算把小女兒許配給沈暮朝,可陰差陽錯,這門親事落在了紀家大…
29.4萬字8 6105 -
完結227 章

重生盛世醫女
顧重陽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回到十歲那年。母親還活著,繼母尚未進門。她不是喪婦長女,更不曾被繼母養歪。有幸重來一次,上一世的悲劇自然是要避免的。既然靠山山倒,靠水..
89.8萬字8 1051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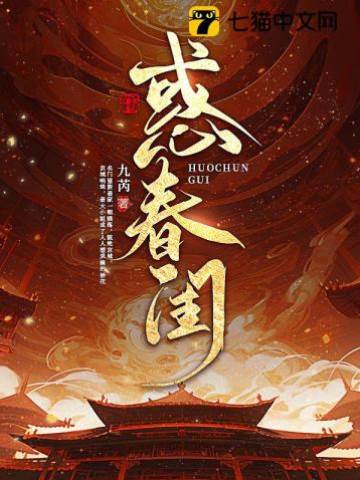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