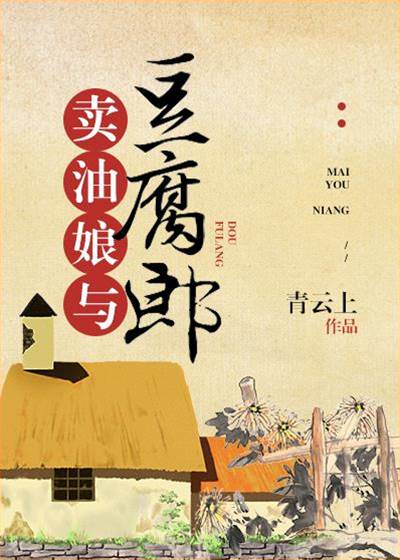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諸事皆宜百無禁忌》 第35章 宜許諾 秋欣然想了一會兒,搖搖頭:……
等觀音堂重新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時, 夏修言靠在佛像背后長長地松了口氣,像是全上下幾百塊骨頭又一塊塊拆開來重新有了能彈的隙。秋欣然眉眼耷拉著,神消沉又沮喪, 全然沒了往日的機靈樣子。夏修言看一眼, 拉起來:“走吧, 先離開這兒。”
二人從佛像的坐臺上跳下來,悄悄翻窗出去, 四周靜悄悄的, 屋也沒有一點痕跡,恍如方才發生的一切都只是他們的一個夢罷了。
山間傳來寒的鳴聲, 在這種夜里格外滲人。二人離開觀音堂,繞到一枝葉繁茂的灌木后,確保四周無人, 終于坐下了口氣。他們盤對坐著, 夏修言在心中盤算了一陣,開口道:“我們得想想接著要干什麼。”這麼一點時間,他好像已經迅速調整好緒,開始有條不紊地據事態變化進行布局了。
秋欣然坐在對面看著他的在月下張合, 他大概說了什麼, 但一句都沒聽進去。只茫然地看著他用石子在地上劃線,想一會兒又涂抹掉,接著重新畫給看。等他說完, 抬眼看過來問:“懂了嗎?”
秋欣然突然覺得很喪氣, 想起一年前在行宮的山上發生的事, 一年過去了似乎毫無長進。低著頭,冷不丁地開口道:“我離宮前九公主給過我一個白玉指環,說是在花園里撿到的。”
夏修言一愣, 但很快反應過來:“李晗臺的?”
秋欣然默認道:“當時不愿告訴我指環的主人是誰。”
“那指環現在在哪兒?”
“在我這兒。”
夏修言神嚴肅起來:“這件事你還告訴過誰?”
秋欣然搖搖頭:“沒有了。”
Advertisement
他松了口氣,告誡道:“別告訴任何人,也不要想著拿指環做文章。”他看一眼,又重復道,“起碼現在還不行。”
“什麼時候可以哪?”秋欣然喃喃道,“等我有一天為老師那樣的人嗎?”
“你想做司天監的監正嗎?”夏修言問。
秋欣然想了一會兒,搖搖頭:“我只想做個算命先生。”
夏修言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說:“我會為領兵的將領。”那是他第一次對人訴說自己的野心,盡管那時候,他的野心也不過是為軍中一個能夠領兵的將領。
“像你父親那樣嗎?”秋欣然小心翼翼地問。
這一回夏修言沉默許久才回答道:“我或許不能像他那樣。不過——”他停頓一下,朝秋欣然看過來,出一點笑:“總要有人能替我們討回公道。”
秋欣然他目中那點浮掠影似的笑意晃得心中微微一,夜風一吹,提了一晚上的心好似就放下來了那麼一點。
這麼一會兒工夫,夏修言又低下頭,將方才的話重新和說了一遍:“我一會兒回廂房去裝作很早就在屋里歇下了。你要自己下山從大殿后面繞到廣場上去,你坐到殿外的誦經的僧人后,夜里四周昏暗,沒人會注意到你。等天亮的時候,你要鬧出點靜來,這樣才會有人記得你昨晚一直都在廣場沒有離開過,明白嗎?”
“明白……”
“好。”月下年出個贊許的微笑,他拉著起來將帶到長廊上。“去吧。”他看了眼面蒼白的,用一種難得輕的語氣同說,“別怕。”
秋欣然看了眼一團漆黑不見盡頭的長廊,抿著往前走了幾步。廊上沒有燈籠,四野一片寂靜,空的只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走了十幾米,忍不住回頭朝后又看一眼,發現黑的年還站在原地目送。
Advertisement
秋欣然攥了手心,扭頭朝著山下小跑起來,夜中周遭的一切景都在快速地后退。不久前還冰冷的手心忽然冒起熱汗,風一吹又消失了。直到一口氣跑到了大殿后的放生池,才敢扶著柱子急促地息起來。
前面就是大殿,僧人的誦經聲回在廣場上,勉力平定了呼吸,小心翼翼地貓著腰溜到了誦經的僧人背后。其他人早已離開了,隨意找了個團坐下,奔跑后劇烈跳的心臟像要隨時跳出腔,沒人注意到什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注意到在這兒坐了多久。
天蒙蒙亮時,廣場上的僧人們疲憊起,法會結束了,鐘樓撞響晨會的鐘聲,回在整個寺院之。
殿中捻了一夜佛珠的婦人睜開眼,平春姑姑忙上前攙扶起:“娘娘一天一夜沒有休息了。”
皇后的臉上出難以掩飾的倦容,靠著旁宮的攙扶起,忽然聽得外頭傳來一陣喧鬧,不由皺眉。平春忙沖一旁的宮婢使了個眼,不一會兒那宮婢回來稟報:“是秋司辰昨晚在殿外守了一夜,方才起時暈過去了。”
皇后微微一愣,出些許容之:“找太醫去看看,難為這孩子有心。”
***
迷迷糊糊之中,秋欣然醒過來一次,躺在的床鋪上,外面傳來談話聲,其中一個是原舟,像在問什麼人:“我師姐……為何還不醒?”
另一個聲音則較為陌生,像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耐心道:“司辰驚懼……憂思……染上風寒……好好休息……”
“多謝包太醫……我送你出去……”
過一會兒外頭又安靜下來,只聽見屋爐火中燒炭的“噼啪”響聲,便在這樣的安靜中再度昏睡過去。
Advertisement
秋欣然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夢里始終在一條不見盡頭的漆黑長廊上奔跑,試圖擺后追上來的腳步聲。不敢回頭,卻能聽見后傳來的聲音,一會兒是李晗園焦急地問:“欣然,你看見我的白玉指環了嗎?”一會兒又變了小松絕地問:“秋司辰,你為什麼不救我?”
捂著耳朵,還是能聽見指甲劃在地板上的聲音,一下一下的,糲又尖銳,每一聲都像劃在的心口上,不上氣來。
“別怕。”
忽然有個聲音在耳邊輕聲說,抬起頭時有人站在長廊的盡頭,月落在他上,看不清面容。
秋欣然的心“砰砰”跳起來,朝著月跑去,一頭撞進白晝里——
睜開眼時,床邊是一張憔悴又疲倦的年臉孔。秋欣然晃了晃神,一時竟分不清自己是否還在夢里。
原舟見醒了,霎時間紅了眼眶:“師姐——”他哽咽了一下,轉過半晌沒有回過臉。
外面的鋪天蓋地落進屋里,人恍惚間有種重回人間的錯覺。
等秋欣然能坐起來吃藥的時候,距離清和公主的法會已經過了小半個月。也是等醒來才知道,在法會上暈倒之后,被人送回舍便一直在昏迷中。太醫來看過,只說驚懼加,憂思過度又吹了風這才引發高熱。這并非什麼重病,但遲遲不醒,原舟差點以為熬不過去。
“辛苦你了。”秋欣然靠坐在床榻上,真心誠意地謝他。原舟卻不好意思地別扭道:“這有什麼好謝的?你若當真出了什麼事,我怎麼跟師父師叔代。”
“那也要謝的,”秋欣然笑一笑,“明明我是師姐,卻總給你添。”
Advertisement
“胡說什麼哪。”原舟不高興地皺眉。他總覺得秋欣然這段時日仿佛消沉許多,也不知是因為清和公主的死,還是因為這場來勢洶洶的病。
“宮里最近……有出什麼事嗎?”坐在床上的人冷不丁地問。
原舟一愣:“師姐指的什麼?”
秋欣然沉默一會兒,才低聲道:“婚喪……嫁娶這一些的。”
原舟不疑有他,立即便想起不久前的一樁事來:“哦——說起來,倒是有一件。”
“什麼?”
“清和公主法會后,徐嬪被發現死在了自己的屋里,經太醫查驗是中毒而死,的宮也在房里上吊自殺了。似乎是那宮平日里拿了徐嬪的首飾賄賂小太監出宮去賣,徐嬪發現,心虛之下才毒殺了徐嬪。不過大約自己也知道事敗,便也跟著懸梁自盡了。”
秋欣然覺嚨里像是梗著一團棉花,半晌才問:“憑什麼斷定是殺的?”
“你知道這后宮的事本是皇后在管的,可近來因為清和公主的死,皇后已許久沒有在后宮面了。好在這案子手段雖兇殘,但調查起來倒還容易,他們找到了那宮賄賂過的小太監,也在屋里搜出了徐嬪所服用的毒藥,人證證俱在,很快就結案了。”
“那宮的尸如何理的?”
原舟有些奇怪他對這件事所表現出的好奇心,但聽語氣又像只是隨口一問,于是到底沒有往心里去:“按常理來說或許就該通知家里人,不過家人好像都沒了,大約最后便是人將尸扔到葬崗去。”
秋欣然沉默一會兒,忽然說:“你能替我打聽一下家人的下落嗎?”
這回原舟當真警惕起來:“你和是有什麼淵源?”
淵源?夢境中的求救聲和呼喊聲好像又在耳邊響了起來,秋欣然不易察覺地輕輕了下被褥,才蒼白著臉隨口糊弄道:“這個宮……我之前好心借過一筆銀子。”
“你借銀子?你為什麼會……”原舟的神迅速從驚訝轉為同,最后問:“你借了多?”
“一大筆。”秋欣然神低落道,“總之你幫我打聽打聽吧,實在討不回來也就算了。”
這九是討不回來了。原舟大約想這麼說,不過瞄了眼的神,到底忍住了沒說,還好心安道:“無妨,你若急著用錢可以問我要。”
秋欣然因為他的話快速地翹了下角,但很快又落下去,走神地瞧著窗外心事重重的模樣。
原舟忽然想起剛宮的時候,臉頰圓潤,明眸皓齒,像是哪座仙山上下來別未分的小仙。在宮中不過一年多的時間,眼里卻已有了幾分憂愁。
“師姐,你想回山上去嗎?”見秋欣然愣愣地看過來,他又有些不好意思,“還是你想留在這兒?”
“我總要回去的……”秋欣然笑了笑,著窗外落了滿地的枯葉,輕飄飄道,“但人不能得隴蜀,在山上的時候想下山,到了山下又想回去。”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鳳花錦
仵作女兒花蕎,身世成謎,為何屢屢付出人命代價? 養父穿越而來,因知歷史,如何逃過重重追捕回歸? 生父尊貴無比,一朝暴斃,緣何長兄堂兄皆有嫌疑? 從共同斷案到謀逆造反,因身份反目; 從親如朋友到互撕敵人,為立場成仇。 富貴既如草芥, 何不快意江湖?
90萬字8 10800 -
完結536 章

傾城醫妃不好惹
一朝穿越,成了不受寵的秦王妃,人人可以欺辱,以為本王妃是吃素的嗎?“竟敢對本王下藥,休想讓本王碰你....”“不是,這一切都是陰謀....”
97.2萬字8 115579 -
完結492 章
穿越醫妃不好惹
穿越前,她是又颯又爽的女軍醫,穿越后,她竟成了沒人疼的小白菜,從棺材里爬出來,斗后媽,氣渣爹。夫婿要悔婚?太好了!說她是妖孽?你再說一個試試?說她不配為后?那我做妃總可以了吧。只是到了晚上,某皇帝眨巴著眼睛跪在搓衣板上,一字一頓地說天下無后是怎麼回事?
88.1萬字8 19934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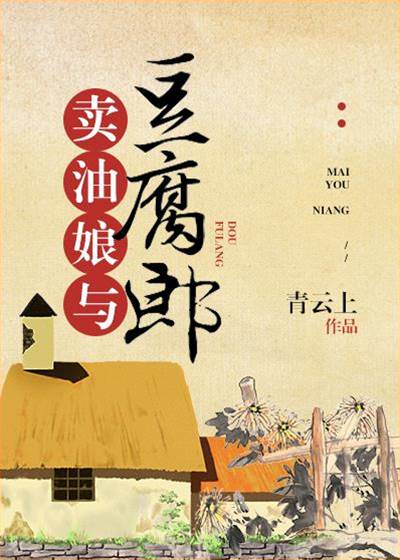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344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46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