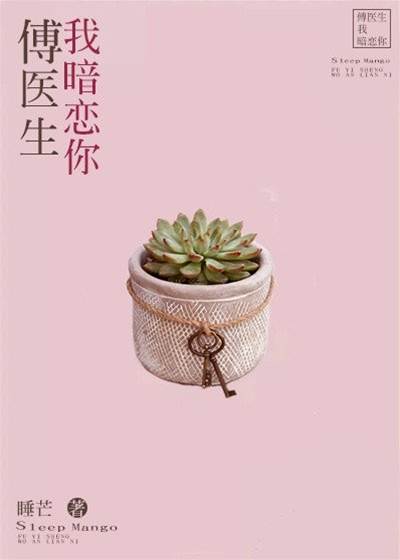《何以笙簫默》 第五章 回首
接下來幾天默笙連續出外景,沒再過問采訪的事,已經和老白說好換個CASE,應該不關的事了。
這天拍攝完的比較順利,默笙早早地回到雜志社。在洗手間洗手的時候被阿梅和幾個同事拉住八卦。
“阿笙,你那個英男人的專訪可能不要做了。”
“怎麼?”
“陶憶靜連人家的面都沒見到,就被拒絕了。真是笑死人了,當初說得多滿,現在丟臉了。”阿梅的語氣聽起來有點幸災樂禍。
“是啊,聽說打電話到事務所,都是助手接的,借口說何律師病了。”
“病了?”默笙本來要出去了,聞言停下腳步,“是真的嗎?”
“肯定是假的啦,昨天我還看到人家上節目了。”
這類節目一般都是提前錄制的,以琛,他會不會真的病了?
坐在辦公室還是不安,一會又自己嘲笑自己,趙默笙,你現在憑什麼去關心他?已經不到你了。
“阿笙,電話!”老白把電話轉給,“好像早上已經打過兩個來了。”
“嗯,我接了。”默笙拿起電話:“喂,你好。”
“趙默笙嗎?”電話彼端傳來男子溫和的聲音,“我是向恒。”
和向恒約的地方是城東一家寂靜人間的咖啡館。
略略寒暄后,向恒說:“找你可真不容易,幸好以琛提過一次你在雜志社當攝影師。”
看見默笙愕然地看著他,向恒一笑:“你這是什麼表,以琛提到你很奇怪嗎?”以琛的確什麼都不會說,但有老袁這個中年八卦婦男在,還是可以挖到點邊角料。
侍者上前遞上餐單。
點了飲料,向恒進正題:“你大概很奇怪我找你出來。”
的確很奇怪,眼前俊雅斯文的男子默笙雖然認識,卻并無深。很長一段時間對他的印象都只是“以琛的一個舍友”,連名字都弄不太清楚。直到有一次跟著他們宿舍的人去吃火鍋,那次是規定要攜伴參加的,結果只有向恒一個人落單,有一個人調侃他說:“向恒,連何以琛都被人搞定了,你這個單貴族還要當到什麼時候?”
Advertisement
向恒嘆氣說:“你說的輕松,我去哪里找一個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趙默笙來搞定我?”話語中戲謔味十足。
偏偏以琛還湊一腳,很頭痛地說:“你要的話送給你好了,正好讓我清靜清靜。”
當時在一旁真是無辜極了,什麼話都沒說都會禍從天降,這幫法學院的人啊,說話一個比一個損。
不過從此記住向恒。
見默笙有點恍惚,向恒突兀地開口:“其實我一直想不通,大學的時候為什麼你會為以琛的朋友。你應該知道,那時候喜歡以琛的生很多,比你漂亮聰明優秀的大有人在。”
默笙不知道他這時為什麼突然提起從前,只是閉口不言,聽他說下去。
他一副追憶的神態。“那時候我們宿舍的娛樂之一就是賭哪個生最后能搞定以琛,有天晚上熄燈后又吵吵鬧鬧賭起來,有人賭的是我們系的系花,有人賭和以琛一起參加辯論賽的才,我賭的好像是外語系的一個生。”
他笑笑,想起年輕狂。“以琛對我們這種活向來持‘三不’政策,不贊不理會不參與,看他的書睡他的覺隨我們鬧,可是那次他卻在我們紛紛下注后突然說——‘我賭趙默笙’。”向恒看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
所以后來才會有人傳是他的朋友吧,這些以琛從來沒提起過。
“你可以想象我們對你有多好奇,后來見到你就更驚訝了。以琛一直有一種超乎年齡的沉穩和冷靜,在我們的印象里他的朋友也應該是懂事的,而你,”向恒含蓄地說,“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
“老實說,我開始并不看好你們,可是以琛卻漸漸像個正常的二十歲大男生,他時常會被你氣得跳腳,也會一時高興就任我們差遣把一個宿舍的服都洗掉。唔,就是他生日那次……”
Advertisement
這種事會發生在以琛上?多不可思議。
他生日那天,跑遍了全城都沒有買到滿意的生日禮,結果只能晚上十點多鐘累得慘兮兮地出現在他宿舍樓下,兩手空空地對他說生日快樂。
以琛板著臉問:“你今天跑到哪里去了?禮呢?”
自然拿不出來,以琛兇兇地瞪了半天,最后挫敗地說:“算了!你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然后他低頭吻了,那是他們的初吻。
還記得當時睜開眼睛后傻乎乎對他說:“以琛,今天又不是我過生日。”
咖啡在杯子里微微晃,“叮”的一聲回到桌上。
這個人為什麼要提那麼多以前的事呢?不要說了行嗎?
“你說的我要知道的事就是這些?”打斷他。
向恒打住,臉上說不出是什麼神,半晌他看著緩緩搖頭說:“趙默笙,你真的心狠。”
是啊,對誰都心狠。
向恒不再多話,掏出紙筆寫了兩行字遞給。默笙接過,上面寫著一家醫院的名字和病房號。
這是什麼?
“以他那種工作方式,英年早逝都不奇怪,何況是‘小小’的胃出。”向恒向來溫和的聲音冷凝,“我把醫院的地址給你,去不去是你的事。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趙默笙!”他的語氣飽含譴責,“人不能太自私!”
他說完結賬走人,默笙坐著,被這個消息鎮住了。紙片在手里地一團,不長的指甲掐進里也是極疼,卻完全沒意識到要松開。胃出,醫院,以琛……因為嗎?竟是因為?
咖啡已經是冰涼,默笙推開咖啡館的門,外面不知何時開始飄起雨。這個時候怎麼可以下雨呢?尤其這雨竟淅淅瀝瀝的沒個斷絕。
Advertisement
居然輕易地就打到車,司機是個熱過頭的人,聽了的目的地以后就開始不斷地發問。
“小姐,是不是你朋友病了?”
“小姐,你在念書還是在工作了?”
“小姐……”
“小姐……”
默笙“嗯”“哦”的回答,眼睛看著窗外。司機的每句話都從耳邊過,卻沒有一句聽個明白。外面的景一樣樣的從眼前掠過,卻不知道看到了什麼。一路上居然沒有紅燈,那麼快地就到了醫院,那麼輕易地就找到了以琛的病房。只是站在門前,那手卻有千斤重,怎麼也舉不起來去敲那個門。
可是要走嗎?那腳也有千斤重,怎麼也移不開一步。
有那麼一剎那,竟覺得會這麼永遠下去,不敢靠近,又舍不得離開,于是宇宙洪荒,海枯石爛,永遠站在他的門外。
可是怎麼會有永遠呢?該來的總要來,怎麼躲也躲不掉。門從里面被拉開,來不及閃避,直直地對上那人。
以玫。
有些人似乎注定總要相遇,而且從來原因一樣,比如說以玫和。
默笙后來總在想,這個溫婉如水又清麗如詩的孩子那時是用怎樣一種心聽所的男子向別人介紹“這是我妹妹”的?當初皮厚兮兮對自我介紹說“我是你哥哥的朋友”而以琛沒有反駁時,又是怎樣的一種痛徹心肺?
如今看到,居然對溫一笑時,那笑里面又有多不為人知的酸楚?
哎!以玫以玫,好久不見。
“默笙,終于又見到你了。”
是啊,終于。
“你來看以琛嗎?”以玫問,“他剛剛睡著,如果你有空能不能陪我去趟他家?我要去幫他拿些生活用品。”
默笙猶豫了一下,點頭。“好。”
Advertisement
“他……沒事吧?”
“沒事。醫生說只要多休息,注意飲食就好。”
“那就好。”默笙低聲說。
一路上絮絮叨叨,不過是一些近況。以玫說:“我本來早就要找你的,卻被公司突然外調,忙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回來一趟,以琛卻突然病了。哎,我總算會到職業的痛苦了。”
默笙說,“我怎麼也沒想到你居然會為一個強人。”
“你不也是?那時候老不務正業拿個相機拍東西,沒想到會為一個攝影師。”
默笙笑起來。“我現在還是在拍。”
以玫失笑,“你老板要是聽到你這樣說一定會氣死……到了,就在這里。”停下腳步,拿出鑰匙開門,默笙腳步頓了一下,跟著走進去。
以琛的家位于城西高級住宅區的十二樓,房子很大,只是看起來空空的,一件多余的東西都沒有,只有茶幾上幾本未合上的雜志才讓這個房子看起來像有人居住。
“這幾年大家都忙,偶爾才聚聚。”以玫邊收拾東西邊說,打開冰箱,無奈地搖頭,“果然什麼都沒有,他大概是天底下最不會照顧自己的人,上次我來居然看到他在吃泡面,忍無可忍的拉他去超市,沒想到卻遇見你。”
以琛一直是這樣的,默笙怎麼會不知道呢。他永遠有比吃更重要的事,對這種人只有“你不吃我也不吃”的招數才能對付。
“哦,對了。”以玫突然說:“我快結婚了,你知道嗎?新郎是我的頂頭上司,很灰姑娘的故事。”
默笙愕然地著,“你要結婚?”
“對,我要結婚了。”笑著點頭,有些嘆,“以前不懂事才會對你說那種話,后來才知道,有些東西是爭不來的,對以琛我早就死心了。”
“為什麼?”
“大概因為我等不過他。他可以在幾乎沒有希的況下一年又一年地等下去,我卻不能。”以玫沉默了一下說:“大約三四年前,以琛贏了個大案子,我和他們所里的幾個人一起去慶祝,他被灌醉了,我送他回來。他吐得一塌糊涂,我幫他清理的時候他突然把我抱住,不停地問,你為什麼不回來?我都準備好背棄一切了,為什麼你還不肯回來?”
以玫頓了頓,苦笑,“如果這些還不夠讓我死心的話……你跟我來。”
拉著默笙來到書房,隨手出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遞給。“這是我無意中發現的,不止這一本書上……”
默笙怔怔地看著書頁上寫得很凌的詩句,從那潦草的字跡可以想象出下筆的人當時的心是多麼的煩躁苦悶。
“啪”地合上書,以玫還在說什麼,已經聽不到了。
腦海中一個清脆帶笑的聲音仿佛從遙遠的時空傳來。“何以琛,你還不知道我的名字吧!我趙默笙,趙就是那個趙,默是沉默的默,笙是一種樂,我的名字有典故的哦,出自徐志的詩……”
悄悄,是離別的笙簫,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小時候,以琛的媽媽經常抱著我說要是有個兒就好了,而我媽媽就在旁邊說要不我們兩家的孩子換換。以琛從小就聰明懂事,我媽媽喜歡他大概比我還多。”回醫院的路上,以玫說起一些往事,“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阿姨的樣子,可惜……”
“……他父母是怎麼死的?”
以玫搖頭說:“我也不太清楚,那時候我才九歲。好象是意外吧,叔叔從四樓失足摔下來,阿姨本來就不好,傷心過度沒多久也去了。”以玫像是想起什麼,頓了頓又說:“我聽我媽有一次無意提起,阿姨死后,發現屜里該吃的藥都沒吃,說起來,也算是自殺。”
“自殺?!”默笙呆住。那時候以琛也才十歲吧,何其忍心!
以玫點頭,“阿姨大概很叔叔吧。”若有所思,幽幽地說,“其實以琛很像阿姨……”
猜你喜歡
-
完結178 章

重生之香妻怡人
紫菱在失去意識的那一刻,聽到小三問渣男老公:“親愛的,她死了,姚家所有財產是不是都成我們的了?”原來,渣男老公不願意離婚,只是爲了外公留給自己的龐大財產!悲憤欲絕,滔天的恨意下,她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再次醒來,鼻翼間充斥著消毒藥水的味道。一張放大了熟悉的俊臉面色焦急看著她問:“紫菱,你感覺還好嗎?”好個屁!她被
43.2萬字8 35618 -
完結448 章
豪門隱婚,傲嬌總裁霸道寵
慕錦愛厲沭司的時候,他傲嬌不屑還嫌棄。她不愛他的時候,他也從不阻攔,但轉眼她就被人設計,被送到了他的床上。慕錦:我不是故意的。她對天發誓絕對冇有禍害彆人的心思,甚至還把設計她的人給找了出來,男人卻對她步步緊逼,最終把她逼到了婚姻的墓地。慕錦一萬個不願意,我不嫁!不嫁?男人涼涼的睨著她,你難道想未婚先孕?
91.2萬字8 38277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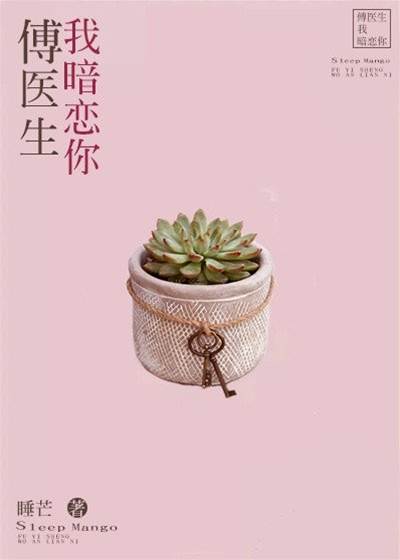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83 章

小情竇
身為北川大投資方長子,祁岸俊朗多金,一身浪蕩痞氣堪稱行走的荷爾蒙,被譽為本校歷屆校草中的顏值山脈。與他齊名的宋枝蒽氣質清冷,成績優異,剛入校就被評為史上最仙校花。各領風騷的兩人唯一同框的場合就是學校論壇。直到一場party,宋枝蒽給男友何愷…
33.9萬字8 6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